作為社會學前史的市民社會思想
另一方面,陳紹馨這個時期的作品中,對市民社會有非常特別的著墨。就書寫脈絡而言,前述對意識形態與知識社會學的討論反映當時包括新明正道在內日本社會科學界的知識焦點。相對地,市民社會並非這個時期的討論重心:日本對市民社會思想的討論要到戰後開始反思法西斯主義興起過程,以及社會運動興起後,才有比較明確的進展。即使在英語世界對黑格爾政治哲學的討論中,國家也是主要的焦點;大約要到1970年代,才開始深刻關注他對市民社會的討論。陳紹馨對市民社會先驅性的關注,可以推測來自幾個因素。首先,從思想本身脈絡來看,黑格爾思想是這個時期日本文科高等教育的基本教養。其次,陳紹馨也注意到西方現代政治思想的關鍵轉折,也就是從十六、十七世紀以對抗王權為核心的社會契約與主權國家形成的理論,到了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商業社會發展下,轉向關注自發性社會秩序與國家間關係。這個轉折源自佛格森,集大成則是黑格爾,恰恰是陳紹馨所針對的兩個市民社會思想家。陳紹馨認為正是這個從早期模仿數學的自然狀態假說轉變到以實證觀察為基礎的思想轉折,構成社會學的歷史起源。
除了對思想脈絡的掌握外,外在脈絡方面也可推測來自他對臺灣現實的關懷。儘管文化社會學具有脫離日本社會現實脈絡的傾向,但對於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日本而言,仍然不失為曲折的「自我認識」道路,間接呼應日本現代性在這個階段的發展。對於臺灣這樣一個在殖民體制下甫進入現代的社會,市民社會誕生的議題對於臺灣社會的自我認識具有更大的啟發性。雖然探討黑格爾,陳紹馨的知識關懷恰恰相反:前者關切如何超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達成新的統一,後者所關切的反倒是與國家分離的市民社會如何可能。戰後包括日本與歐洲,特別是東歐對市民社會的討論,常常都是在面對一個壓制性的國家之下對自主性的強調。陳紹馨日後將臺灣走向市民社會的歷程作為研究首要課題,一定程度可以看出臺灣歷史脈絡與他對市民社會思想的關注之關係。
陳紹馨對佛格森的討論,聚焦在他1776年的《市民社會史論》(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英國是最早發展出布爾喬亞市民社會的國家,佛格森則是最早注重社會性的現代政治思想家,並以為基礎建構市民社會理論,因此陳紹馨將之定位為社會學的先聲。佛格森雖然從未明確定義社會,而將社會視為家族、部族、朋友、國民甚至帝國的綜合體,但明確反對當時政治思想所流行以自然狀態為基礎的社會契約論,主張對市民社會的討論必須從人類本能的社會性開始。佛格森主張上層結構的文學美術知識,雖然表面看來與現實生活脫離,但型塑了整體性的社會生活,因此學藝活動的興衰影響整體社會的狀態。在這個前提下,人類社會的發展便是從未開化社會(rude society)發展到開化社會(polished society),或是從蒙昧野蠻到文明,也就是文明社會或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必須留意的是,陳紹馨翻譯佛格森著作時,常常將文明社會和市民社會兩個概念混用而視為同義詞,如此混用並不見於對黑格爾的討論中。筆者認為這與英文civil society與德文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差異有關,佛格森將civil society這個概念直接對立於未開化社會、野蠻社會,也使他的civil 概念究竟是指日文的「文明」還是近代的「市民」產生模糊。
陳紹馨進一步整理佛格森對不同社會進化階段凝聚原理的分析:蒙昧社會的成員間內部分化小,具有強固的同質結合,擴張是透過向外戰爭,由大集團兼併小集團,因此最受尊崇的是可以向外獲取戰利品的戰士。市民社會則是在社會分工、私有財產發達以及社會從屬關係確立下,鬥爭轉向內部。社會分工發達後,個人依不同性向從事不同職業,生產與軍事組織也產生技術上的分化。佛格森批判社會分化所產生的弊病,認為導致個人被局限在自己的工作而失去觀照全局的視角。社會發達也帶來貧富差距擴大,產生內部鬥爭,過往向外鬥爭的成果就會在內部鬥爭下浪費。
〈黑格爾〉一文分成上下兩篇刊載,陳紹馨在上篇討論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基本內容,並回顧西方現代政治思想中對市民社會的討論,下篇則討論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在思想史中的位置與意涵。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主要出自於1820年〈法哲學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陳紹馨對黑格爾政治哲學的理解大抵吻合目前文獻的一般認知。黑格爾體系中的倫理生活(Sittlichkeit)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家庭,黑格爾反對以原子化個人出發的自然狀態說,而將倫理生活的起點設定為是從生育的需求所衍生的家庭。第二階段則是文中所著重的市民社會,其起點是經濟學所討論的欲望體系,從私利出發的個人,則構成市民社會。欲望的滿足帶來勞動,是價值的來源。勞動的客觀化與普遍化會帶來分工,人類因而形成更緊密的互賴以及依存關係,但也產生生產過剩、分配不均、利益對立等社會矛盾。立基於自利與欲望體系的市民社會成立,仰賴三個重要環節:司法、警察、同業公會。黑格爾承襲孟德斯鳩的看法,將法律視為人類生活內在的必然形象,法律因此成為市民社會的契機。經濟的生活關係會帶來普遍性的法律與司法,構成存在的普遍者與主觀特殊性的統一。陳紹馨指出警察(Polizei)在此並非狹義維持治安的警察,而是指稱更廣泛對權利以及共同生活安全的保護,具體內容包括對生產及消費的統制、對弱者的福利等。同業公會則是當時德國實業階級的特徵,在黑格爾脈絡中,也是獲得名譽與權力的領域。最後,倫理生活的第三個階段則是國家。黑格爾將國家視為客觀最高精神的實現,將個人特殊需求與全體普遍福祉完全有機的融合。市民社會是倫理的現象世界,國家則是倫理的實現。在這個前提下,黑格爾主張古代的統一國家是不完全國家,沒有發展出獨特性,並隨著近代分化的經濟生活而解體,形成黑格爾稱為悟性國家的特殊性市民社會。普遍性的古代國家與特殊性的近代市民社會在辯證法下,朝向「具體自由的現實態」之現代國家邁進。
如前述,陳紹馨對佛格森與黑格爾的討論中,除了闡述兩者理論內涵外,最關注的是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定位,特別是如何引出社會學的誕生。陳紹馨對佛格森的歷史定位放在時代先驅的意義,也就是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這兩個布爾喬亞市民階級躍升的關鍵事件之前,就提出市民社會的討論,同時開展對自然狀態理論的批評。另一方面,陳紹馨在黑格爾的討論中,除了市民社會理論的內涵外,也聚焦在其與馬克思主義整體觀的關係,認為他建立出物質生活關係、政治法律以及學藝宗教間關係的理論。除了介紹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討論外,陳紹馨這篇長文所關切的問題,則是為什麼市民社會早在英、法萌芽,卻沒有出現完整的市民社會理論;反倒是在市民社會較不發達的德國,由黑格爾提出市民社會理論?
陳紹馨對此提出類似〈德國風格〉的回答,也就是黑格爾成熟的市民社會理論恰恰來自德國市民社會的後發性。他回溯從布丹到霍布斯、洛克以及盧梭等西方現代政治思想家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看法,指出從概念史來看,從霍布斯開始,市民社會的概念就普遍與其他政治共同體的概念混用,甚至消融在其他政治共同體的概念中。霍布斯的用法中,國家與市民社會幾乎同義,洛克的論述中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與共同體(common wealth body)也同義,而包括佛格森、亞當斯密、重農學派與盧梭都有類似將市民社會等同於政治共同體的傾向。另一方面,黑格爾之前的理論家在使用市民社會這個概念時,所要對照的往往是國家之外包括村落、城鎮、都市等各種共同生活的型態,而普遍將開化的文明社會視為與國家的同義詞,以此區別於之前階段的社會政治型態。陳紹馨稱為「社會」與「市民社會」的區隔。
陳紹馨認為,十八世紀市民社會的概念在英法政治思想中的式微,恰恰起因於英、法布爾喬亞市民階級政治上的勝利。英、法布爾喬亞革命之下,封建主義與絕對主義被排除,國家的任務被新興掌權者設定為以法律保護財產權、自由與平等的活動。換言之,現實上英、法的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關係從初始激烈的對立,隨著布爾喬亞階級發展出市民社會逐漸掌握國家,促成國家的「市民社會化」,自然也沒有再建構獨立於國家之外市民社會理論的必要,而整合進政治共同體的討論,促成國家與市民社會兩者概念的同一化。相對地,黑格爾之所以會建立完整的市民社會理論,則是起因於德國相對後發的國家發展。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終極關懷是克服市民社會的矛盾,朝向一個絕對精神更高層次的國家,而這個終極關懷正來自他所處時代德國國家的缺陷:在神聖羅馬帝國遺緒下四分五裂,拿破崙入侵又彰顯缺少強有力統一國家的現實,從而刺激建立統一國家的企圖。普魯士的興起與經濟的發展提升德國人的愛國心,也強化黑格爾建立神聖性國家的概念基礎,因而在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上做出重大貢獻。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社會學博士。曾任教於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現任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經濟社會學、歷史社會學、日本社會、人口與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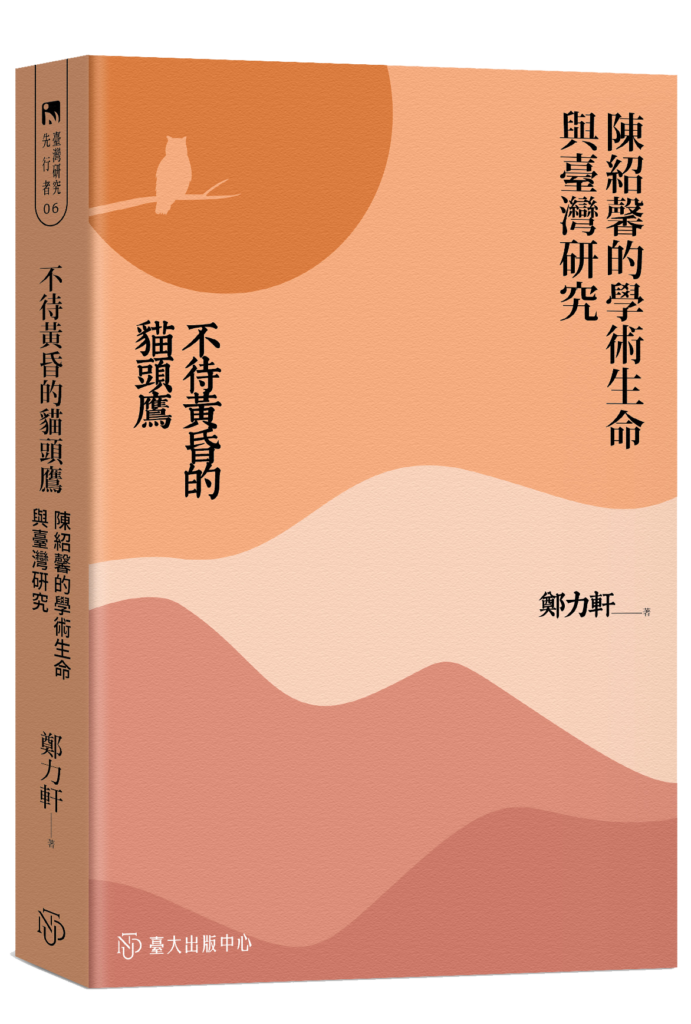
書名:《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
作者:鄭力軒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22年10月
讀冊|博客來|金石堂|誠品
- 【書摘】《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 - 2023 年 11 月 24 日
- 【書摘】《不待黃昏的貓頭鷹》 - 2022 年 10 月 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