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冷戰到高加索分崩離析
一九七九年,是充滿政治分裂和意識形態分裂的一年,從此成為當代歷史的重要分野之一;對很多人來說,一連串戰火爆發,看似是包圍了蘇聯南境。這年一開始,先是伊朗國王由於不敵那場已然無法控制的革命運動,於一月十六日出逃;年底則是莫斯科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決定出兵阿富汗,扶持一支危弱的親共勢力。這些愈燒愈烈的鄰國戰火都離蘇聯南境不遠,再加上一九八○年九月十二日土耳其發生軍人政變,以及數日後開打的兩伊戰爭:那個新成立不久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與一九六八年薩達姆.海珊於伊拉克巴格達建立的巴斯黨政權,進入長達八年的對戰。
一反高加索邊區前幾年的穩定局勢,如今愈來愈顯得像某種世仇和政治失合,情況混沌不明。一方面,蘇聯政權處於所謂的「停滯」狀態,布里茲涅夫政治上恩庇門閥、社會上妥協攏絡人民,兩者結合並用,一直掌權到他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離世。另一方面,沸沸揚揚的是宗教意味愈來愈濃厚的伊朗革命,以及土耳其對於左派反對勢力的大規模鎮壓。如果說一九八○年代初,對於那些革命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始終是參考指南,蘇聯經驗卻顯然不再吸引人,而且當下還正經歷比其所下令執行的更為嚴峻的轉型。
為了理解這些區域性的翻轉變化對高加索邊區造成的衝擊,我們便需觀察一九七九年之後那些年。那些動盪賦予邊區新的意識形態,同時自然地賦予宗教議題一個特殊的重要性。觀察家們往往炒作區域角力關係中「伊斯蘭元素」的重要性。難道是像有些人所說,蘇聯方面操縱伊斯蘭來對抗西方,以免中亞和高加索的蘇維埃共和國暴露在一種失控的宗教狂熱再起,可能遭到敵人利用?雖然這種不穩定的局勢營造出一種觀望氛圍,高加索的重大動盪則直到一九八○年代末才發生,還有蘇聯共產黨新任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自一九八五年三月起推動的「經濟改革」(perestroïka,俄語意為重建),也是在八○年代末才顯現出成效。
新的國際關係方針使得與土耳其和伊朗交流時,關係有了顯著改善,而政治上鬆綁在國內帶來的衝擊,則在外高加索內部造成一些前所未見的裂隙。民族問題,從「經濟改革」的第一時間就再度浮現,自一九八八年起導致外高加索內部情勢愈來愈緊張,在該地區三個共和國內引發了種種真正的政治衝突,且有時甚至是武裝衝突。於是一九八○年末高加索呈現國際邊界的矛盾景象:在冷戰結束的效應下,國界開放了,而原來的蘇聯領土卻從四面八方疵裂。以此意義而言,接下來被顛覆的,就將是邊境的社會、經濟和人類學經驗了。
政治緊張與新的冷戰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伊朗國王從德黑蘭出逃;巴勒維王朝對於過去幾個月的動盪,除了政治懦弱,並夾雜不分青紅皂白的鎮壓以外,毫無對策。理論上,蘇聯或許可以慶幸這個始終是美國最親近的盟友之一倒台了(不論這個盟友想不想掙脫美國)。美國人裝置在伊朗北部監視中亞核武和彈道飛彈活動的兩個電子情報偵測站(TACKSMAN)關閉了,怎能不開心慶祝?這兩個站點關閉造成的缺口,使得美國設置在土耳其的那三個基地重要性大增,並且迫使華盛頓方面不得不與中共洽談,在中國境內架設類似的設備。就在伊瑪目何梅尼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結束他的法國流亡歲月重返伊朗,旋即成為伊朗政界核心人物之際,莫斯科則不顧一切地押寶於圖德黨;該黨於革命期間再度活躍起來,走出地下活動,並嘗試動員背後的群眾。
到了一九七九年年底,由蘇聯國防部長狄米特里.烏斯季諾夫將軍鼓動出兵阿富汗的決議,很顯然比較不利於蘇聯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阿富汗一九七八年建立的共產黨政權,由於實施改革的手段粗暴且不得要領,失信於民,其國內局勢的發展,讓該政權數月以來相當艱辛。蘇聯對於阿富汗的占領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九年二月,這隨即使得蘇聯與許多穆斯林國家的關係都岌岌可危;這些國家於一九八○年一月的伊斯蘭合作組織會議中,就已對此提出抨擊。廣泛地來說,儘管某些蘇聯的盟友嘗試出面辯護,但第三世界國家都批評蘇聯的行徑違反了互不干預原則,且是一種帝國主義的表現。
第三個發展,在高加索西麓,起於一九八○年九月十二日的土耳其軍事政變。帶頭者凱南.埃夫倫將軍,以必須約束國內極左派與極右派勢力一連串對立造成國家失序混亂為由,將這場自一九七一年以來首次的軍事政變予以正當化。事實上,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間,這一連串對立衝突已造成將近六千人喪命,而政府機關也如同土耳其社會內部分歧之翻版,因意識形態與政治分歧,而千瘡百孔遭到癱瘓。然而,這場政變,不但遠不符合官方版本「軍方出手仲裁政治亂局」的說法,還帶來了一場特別暴力的鎮壓,而且主要遭到打壓的是左派勢力,這造成了一波逃往歐洲的大規模流亡潮。
所以,整個地區都在動盪中,可是前述這些發展的方向卻都不一致。阿富汗戰爭對於南高加索諸共和國的衝擊比較沒有那麼直接;直接受到衝擊的,是成為軍事行動後援基地的諸中亞共和國,或是蘇聯那些在歐陸部分的共和國,被動員提供主要軍隊兵力。不過,亞塞拜然最特別的,是提供一團義務役的波斯語譯者給蘇聯軍隊。更廣義地說,高加索諸共和國跟蘇聯其他地區以及中東歐共產陣營國家一樣,都接到指示,要透過合作關係、姊妹市和交流活動等去支援阿富汗政權。
伊朗和土耳其政治變天,對這兩國來說,有各種意義上的詮釋。一九八○年九月土耳其政變,加快了原本與華盛頓方面的修和計畫,而隆納.雷根更試圖動員美國諸盟友來制裁蘇聯。以凱南.埃夫倫將軍為中心的軍人政變,遭控訴為鎮壓迫害且有美國人撐腰,這些控訴都顯得相當正式,然而新的局勢似乎並不必然會顛覆地方上的交流。〔蘇聯駐土耳其〕大使羅迪奧諾夫於是在一九八一年五月進行一份針對黑海陸棚協議之修正換文,這份協議原是一九七八年六月所簽署,開啟了海底資源開發的途徑,同時也增加了能源領域的交流,奠定土耳其日益仰賴蘇聯供應電力和碳氫化合物的基礎。
這次換文反映出黑海這個空間作為土蘇交流區域的新角色。〔土耳其〕政變之後沒幾天,蘇聯喬治亞某位叫做山卓的人寫信給布里茲涅夫,建議發展土耳其和蘇聯之間的郵輪計畫,以促進兩國間的彼此認識,便展現出對於這片海域的深切期待。不過山卓還建議,為了更加方便行事,如此協議最好是「由喬治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經中央政府同意後,以中央的名義)直接與鄰國―土耳其共和國」簽署。在這位投書人看來,剛發生的政變非但不是一個妨礙,反而創造了一個有利於合作的機會,而且他覺得愛德華.謝瓦納澤這號人物最適合主導這些前景看好的協商。在這些斡旋的努力中,亞塞拜然的領袖人物海達.阿立耶夫也嶄露頭角,他早自一九八一年一月便建議莫斯科要利用亞塞拜然共和國的〔國際〕能見度來維繫與土耳其的良好關係。
蘇聯高加索應對伊朗問題
相較於〔土、蘇兩國〕這種妥協出來的權宜之計,蘇聯與伊朗的關係則是在一九八○年代初明顯地緊張起來。事實上,那個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動搖伊朗的革命,本來沒有引起莫斯科什麼熱情關注;莫斯科方面眼見從一九六○年代起與國王一起拉近兩國關係的那些努力都化為烏有。除了外交考量,革命造成的失序混亂在一九七八年至七九年冬天還導致瓦斯供應中斷,造成外高加索地區停電並且失去暖氣供應。直到一九七九年開年好幾個星期後,蘇聯才透過伊朗國家之聲廣播電台向革命運動示好。不過蘇聯當局明白他們對於伊朗革命的影響有限,因為面對極左派的活躍,伊朗共產黨圖德黨已經被邊緣化;極左派的激進運動千變萬化,其中更不乏莫斯科極不樂見的對毛澤東之種種效法。在國王倒台前兩天,一月十四日,圖德黨更換黨魁,由過去幾個月以來一直捍衛著一條清晰革命路線的努爾丁.齊亞努里擔任,他是曾經流亡至中東歐共產陣營國家的資深抗爭人士。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伊朗〕通過伊斯蘭憲法,加上蘇聯占領阿富汗之後,局勢愈發緊張。伊朗是最早批評這個占領行為的國家之一,此立場使伊朗得以確立其反帝國主義立場,並且拒絕任何結盟行為。何梅尼的主張,是為那些被壓迫和「被剝奪財產」的人民代言,完全在一種「不要東方、不要西方」的論述中。在蘇聯境內,這種論述由新任伊朗大使穆罕默德.默克里為代言人,這位長期流亡國外的學者,遵奉宗教典範,並且亟於和蘇聯境內的穆斯林建立直接連結。一九七九年五月,一群伊朗僑民聚集於巴庫的總領事館附近,在大庭廣眾下,焚燒退位的國王和王后法拉.帝巴的肖像。接下來好幾天伊朗媒體轉載了很多張示威者正在焚毀肖像的黑白照片,而某報更頌揚「蘇聯的穆斯林熱情歡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大使」。這位大使激昂地呼籲伊斯蘭團結,還有他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巴庫的清真寺所發表的宣教演說,都是麻煩的根源,更何況伊朗還在同一時間決定不參加一九八○年九月蘇聯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召開的穆斯林大會。
在此同時,區域局勢中又出現第二個緊張情勢的源頭,由薩達姆.海珊掌權的伊拉克,決定對伊朗發動一場血腥戰爭,這場仗持續打到一九八八年。莫斯科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起初對於要採取何種路線意見分歧:如果說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和日後的第一書記尤里.安德洛波夫希望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拉近關係,軍方卻不這麼想,軍方提醒軍售伊拉克以及與伊拉克合作的重要性。最後決定要維持一千兩百名蘇聯軍事顧問,但是暫停軍售給巴格達。這個決定,並未阻止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軍武設備給海珊;在德黑蘭方面看來,這就像是對伊拉克侵略行為的默許,導致兩國外交關係日益緊張。而當戰事有利於伊朗時,蘇聯又陸續地〔給伊拉克〕輸送武器,罔顧伊朗人性命。
蘇聯和伊朗關係惡化,高加索首當其衝。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為止,問題都還在於如何促進亞塞拜然蘇維埃共和國的伊斯蘭代表與伊朗革命菁英間直接接觸。然而,伊朗局勢快速惡化,使得巴庫變成這些合作者的家眷與蘇聯外交人員的轉運地;前述人員在〔蘇聯〕駐德黑蘭大使館首度遭人試圖恫嚇後,於一九八○年一月二日奉令撤離,裏海艦隊的多艘船隻都被緊急派往進行這場撤離,而當年春天沿著邊界又發生了數起軍事恫嚇行動。接下來的幾個月,設於伊朗北部的那些蘇聯代表處,由於遭到指控支持反政府人士,一直都處於兩國間緊張局勢的風暴核心。
一九八○年八月,伊朗外交部長薩戴.闊札德一封寫給蘇聯人的信,就揭露在伊朗庫德族地區內發現「大量的蘇聯製武器」,並指控蘇聯的態度「與惡魔般的美國並無二致」。在同一時間,裏海濱拉什特城的蘇聯領事館,則遭伊朗指控是竊聽和蒐集情報的平台,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情資。往後幾個月,暴露於雙邊關係紛擾中的高加索邊區,主要都糾結在伊朗公共領域中被揭發的那些蘇聯間諜案。一九八二年夏天,負責所有滲透進伊朗的「偷渡客」的蘇聯情報人員弗拉基米爾.庫奇金變節投誠,此事更是加劇雙邊關係的危機。庫奇金透露給西方國家情治單位的資訊,被小心翼翼地轉給伊朗,引發一九八三年二月時一波逮捕圖德黨激進人士的行動,甚至往上牽連到齊亞努里,迫使他數次在電視上羞辱地認罪,最終該黨於同年五月正式遭禁。
面對伊朗既混亂又欠協調的宣傳戰,蘇聯當局自一九八○年春天起,就在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的一個龐大共同計畫中,密切投入研究當代伊斯蘭政治潮流的發展;負責協調該計畫的研究所所長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是蘇聯與中東進行平行外交的知名人物。一九八○年七月八日,一份加強對伊朗進行反宣傳的計畫通過實施,所有媒體和所有從中亞和高加索播送的廣播電台都直接被納入參與計畫。我們也見到外高加索穆斯林精神生活管理處被賦予了一個特殊角色;在此之前,相較於塔什干的精神生活管理處,外高加索的管理處重要性不高。而領導人謝赫伊斯蘭帕查札德,由於他這個行政部門的結構特殊性,得以同時監管什葉和順尼的穆斯林(蘇聯獨有的情況),因此他的地位愈來愈受彰顯。
帕查札德頻繁出國參訪,並且接見許多代表團,向這些代表團宣講什葉和遜尼在高加索共存的善德。他還多次邀請伊朗神學士來訪,以加強與亞塞拜然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而在與伊朗宗教人士保持如此高度頻繁接觸的同時,他也致力於與伊拉克官方建立各種往來。由於伊朗與伊拉克兩國都在巴庫設有總領事館,使得這個亞塞拜然的首都成為一個互別苗頭的擂台,經常有各種儀式和活動的舉辦,兩伊的外交人員都會在這些場合中全力爭取蘇聯發表支持他們的聲明。與此同時,還可以在許多國際展覽會的場館中見到帕查札德的合作夥伴們介紹著「蘇聯的穆斯林」:先是一九八○年九月德黑蘭商展有這麼個有點無法分類的奇怪攤位,之後一九八二年八月至九月的〔土耳其〕伊茲米爾商展也出現了一個類似的場館。
高加索式的「經濟改革」
參觀者向這些攤位的合作者洽詢的那些問題,如果說通常都是有關信仰,不過卻也揭露出這些邊境關係其他意在言外的表述。其實,許多洽詢者都是對亞塞拜然蘇維埃共和國有興趣的看展觀眾,其中,很多是伊朗的亞塞拜然人,他們將造訪此攤位當作批評那個伊斯蘭共和國政治日益中央集權的一種方法。在革命最初的那幾個月,強調的是共同的伊斯蘭認同,對於亞塞拜然人區域性的訴求,還看到一種相對的容忍;然而三年後,再也不是那麼一回事。在伊朗亞塞拜然省格外有人氣的阿亞圖拉沙里亞特馬達里,可以說是外地反何梅尼勢力(包含教義層面的對立)的代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伊朗亞塞拜然省進入分裂脫離的狀態,反抗中央權力;這兩位阿亞圖拉的衝突在一九八二年四月達到高峰,何梅尼違背了所有伊朗神學士傳統,以陰謀顛覆其政權為由,逼退沙里亞特馬達里。
在官方的反宣傳框架中,巴庫菁英圈內再度浮現了一種頌揚亞塞拜然國族主義的論調,但遭到蘇聯中央制裁。於是,我們見到蘇聯一九四○年代的那套攻略,在伊朗亞塞拜然省的公眾論述中還魂,而且,那個長久以來的禁忌詞彙「南亞塞拜然」,克服萬難地重新出現在報章與各種出版品中。掀起這波浪潮的,是文壇大老亞塞拜然作家聯盟的主席米爾札.易布拉喜莫夫,他發表的文章︿南方復興﹀描述了伊朗亞塞拜然人的處境。一九八一年,巴庫的東方學研究所開闢了一個討論會期,專門討論這個「南亞塞拜然」,與此同時,那些國營出版社則大量出版伊朗亞塞拜然人的小說、詩作和回憶錄等。在文學層面,此時是「懷舊」文學的全盛期,思索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亞塞拜然共和國的失敗,也思索那條將亞塞拜然人劃分成兩邊的阿拉斯河的象徵意義,與當時代那些流亡者曾短暫出版的文學重繫紐結。
在跨境發展的過程中得到正當化的那種愈來愈強有力的國族論述,並不局限於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當局也竭誠捍衛那些在伊朗因為身為基督徒而遭到言語暴力,並受到兩伊戰爭衝擊的亞美尼亞人;喬治亞的亞美尼亞人也繼續進行一九六○年代協助菲瑞丹地區的喬治亞人返鄉的政策。自從一九七五年黎巴嫩內戰開始後,甚至連葉里溫也投入援助黎巴嫩的亞美尼亞人,更在一波夾雜民族訴求、蘇聯愛國主義和基督徒精誠團結面對伊斯蘭威脅的宣傳中,自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起,將撤離伊朗的亞美尼亞人接返亞美尼亞,作為新的核心關懷。因此,伊朗伊斯蘭政治的確立,也有助於鄰國亞美尼亞和喬治亞強化基督信仰在國族中的定義。一九八五年一支法國代表團途經葉里溫,歸結出蘇聯當局利用國家論述「完全地掌控這個共和國」,同時也注意到宗教復興的力度似乎逾越了官方的底線。
儘管前述區域形勢助長了這些民族國家的發展,但在米哈伊爾.戈巴契夫上台,並逐步推行其新政之時,高加索則遠非蘇聯時事關注焦點。阿立耶夫於一九八二年成為莫斯科中央政治局的一員,並擔任蘇聯部長議會第一副主席,不過他仍對所出身的亞塞拜然共和國的政治保有某種間接掌控,降低了繼任者卡姆蘭.巴吉洛夫的存在感。而比較親近戈巴契夫的謝瓦納澤,於一九八五年夏天榮任蘇聯外交部長;他自一九七八年起就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顯然就是得益於他在政治上活躍的形象。早在一九七○年代末,他不就已經表明立場,贊成結合學院派的社會學理論以及共產黨的掌控工具,加強運用各種措施操控輿論。在他的指揮下,由於一九七二年初的貪汙舞弊而「被釘在刑台上示眾」的喬治亞,似乎成為一個「理念實驗室」,透過一連串在市府層級、波季港、提比里斯和幾個農業區的經濟實驗,幾乎可說是提前進行了「經濟改革」。
在新政治權力的頭幾年,南高加索除了幾個主題項目還有點能見度以外,幾乎感覺不到什麼改革的影響。對於社會和政治的批評逐漸深化,特別是表現在藝術和電影方面,例如一九八六年譚吉茲.阿布拉澤的電影《懺悔》,明白批評政治專橫,或者亞美尼亞-喬治亞人導演謝爾蓋.帕拉札諾夫拍的那些電影,都大獲成功。戈巴契夫是研究農業問題出身的,對於高加索地區極度令人失望的農業狀態,毫不掩飾地表達不滿。在此同時,環境問題愈發引起注意,這個自一九七○年代末以來就日益嚴重的問題,從許多民眾投書表達他們擔憂黑海和裏海沿岸的狀態就看得出來。向主管當局投書,是蘇聯社會長久以來的習慣做法,愈發密集的信件,通常得到一種相當善意的官僚回應。早自一九八○年,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境內的梅薩莫爾核電廠擴建之時,亞美尼亞科學界和亞美尼亞當局就聯合動員,中止未來要貯存外高加索所有危險廢棄物的廢料場計畫。鄰國喬治亞,則是將一九八四年至八七年間的一個外高加索鐵道計畫,視為對喬治亞國家以及其景觀的威脅。高加索地區由於化工業、石油業和冶金業快速發展,對於生態環境議題日益關切,而戈巴契夫的透明開放政策,以及車諾比核災意外的效應,都再度在時事上強化了生態環境議題: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一位醫生兼環保運動人士佐里.巴萊陽在《文學報》中深表痛心地指出,葉里溫都要死在毒煙裡了。
作者現任巴黎政治學院里爾分校現代史講師,同時也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與里爾大學共同設立的北歐歷史研究院(IRHIS)之研究員。其研究專長為國際關係,以及東歐、俄羅斯和中東之間的交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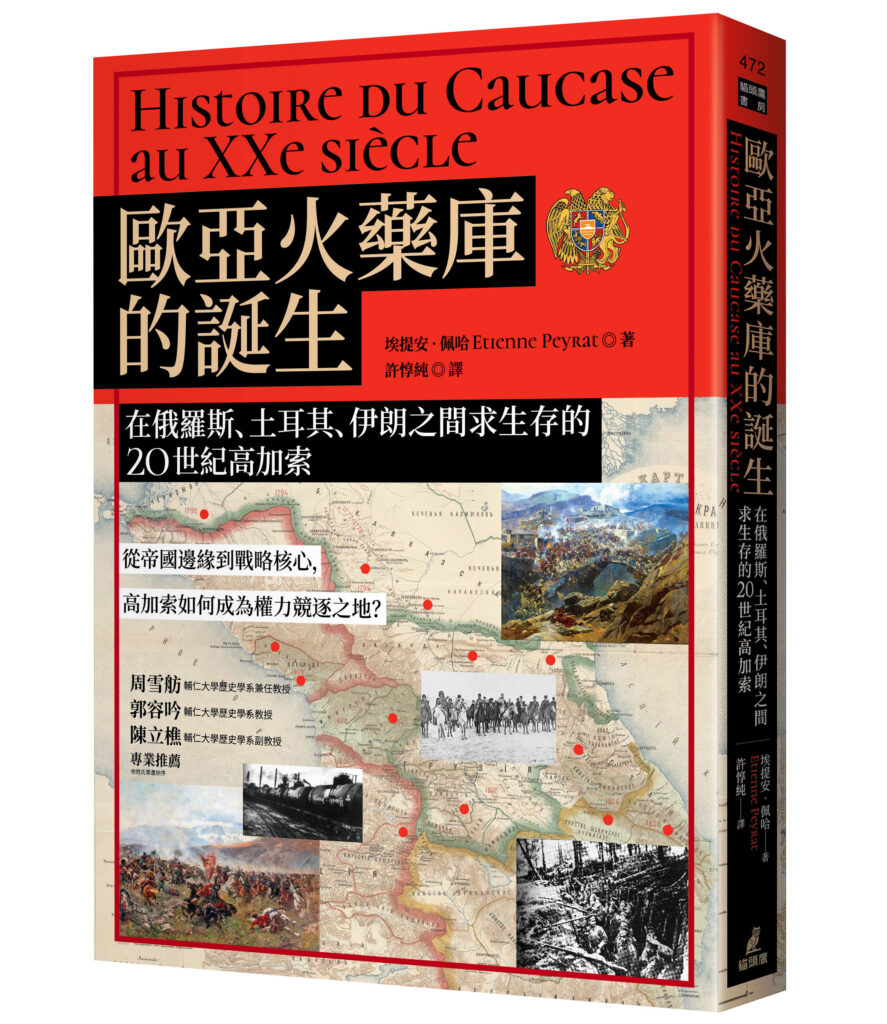
書名:《歐亞火藥庫的誕生──在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之間求生存的20世紀高加索》
作者:埃提安.佩哈(Etienne Peyrat)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時間:2023年4月
讀冊|博客來|金石堂|誠品
- 【書摘】《城市六千年史:見證人類最巨大的發明如何帶動文明的發展》 - 2023 年 11 月 9 日
- 【書摘】《經濟史的趣味》 - 2023 年 7 月 13 日
- 【書摘】《歐亞火藥庫的誕生──在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之間求生存的20世紀高加索》 - 2023 年 4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