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乘著世界歷史之風,升起船帆。思想於它是揚起風帆,詞語就是他的帆,而要成為概念,則要看如何揚帆。──班雅明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經表明,諸如人口調查、地圖與博物館等帝國殖民治術的政治效應,經常是一個除魅與復魅雙重並進的過程。起初它們希望透過有限的序列,讓一切需要治理的對象都能一個整數、無所遺漏的方式編排、分類進而控制;然而與之並行卻是召喚出另一種無限序列,其命名原則是不知名、可複製的通用事物:一個馬來人、一個維吾爾人、一個無產階級等等,舉目所及,人人皆是。
帝國現代殖民技術以文明之名在除魅殖民地野蠻的同時,同時也孕生後殖民國家的復魅:一種「會遺忘很多事情」的民族共同體想像。而《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文明與野蠻》不言而諭的質疑了這個除(復)魅的雙生,進而拆解其中彷彿必然的連結,「除昧」與「復魅」的敘事於是得以平行並進。
「除昧」的迷思暴力
薩依德曾在《東方學》中記述了Arthur Balfour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講,他宣稱英國人,作為征服者,卻比「那些野蠻人」,比其他的國家都「更瞭解埃及文明」,因此,埃及及其人民的福祉最好託付與英國人管理,而教化與撫育野蠻人等,則是文明帝國責無旁貸的重負。
「野蠻人」(barbarian)一語源自古希臘語中的擬聲詞”barbaros”,用以描述不會講希臘語的人在說出自己語言時希臘人聽到的聲音,本意是無以辨識,用法近於漢語語境中「蠻夷戎狄」所指涉的乃出九服之地寓意。然而,野蠻與文明的雙生辯證是貫穿《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文明與野蠻》的書寫理路,不是作為時間序列的先與後,而是在同屬一個符號秩序中「藉以辨識、劃分,規訓治理或排除的法則」。
在現代政治法理的語境中,「野蠻」並不是文明的遠古對照,而是文明用以證成自身精神與歷史優勢正當性的法理配置。不存在阿茲提克人與印加人發現歐洲的可能,因為野蠻人沒有基督教歐洲的理性知識能力,他們沒有能力像歐洲人那樣繪製美洲大陸的地圖,由於歐洲人精神上的優勢,新世界只能處於一種「被拿取」的狀態,「發現」的行為並不需要被發現人批准,反而,正如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所暗示,出於普世法權的約束,不文明的亞非人民對於外來者有悅納義務。若果如此,讀者會在「八瑤灣事件」的琉球漂民被戮看到悅納義務的弔詭。
文明的「國際法」自始並非平等政治實體的交往原則,邊沁在1780年以「國際法」所指涉的問題意識是歐洲人占領土地的整體正當性。
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中「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一語堪稱本作題眼。殖民暴力的弔詭在於它並非無理蠻橫,而是有其「除昧」的法理論述,也即文明與野蠻之間的門檻閾界(threshold),及其因預設之必要過渡而生產的「裸命」(bare life):1914年「太魯閣戰爭」中既作為理蕃對象又作為撫育客體的原住民、1931年霧社事件後被集中於川中島社中,既是遺族又為「保護蕃」的倖存者、1942年南洋戰事中獻身帝國戰場,既(不)是非人,也(不)是國之人類的高砂戰士。
文明與野蠻的閾界是帝國除昧空間中非裡非外的空無之地,過去的莊園與蕃地,今日的營或監獄,都是其標誌性形象。讀者將在本作中感受到因為裸命因為生命形式與生命本身之疊合與無以區別所帶來的雙重意識與精神困境。
「除魅」的神聖暴力
在其自傳小說《英雄奴隸》中,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對於殖民地經濟「園」(plantation)的描述,貼切說明了此一文明與野蠻必要過渡的法理配置,「園是一個獨立的小王國,有自己的語言、規則、規章與風俗。國家的法律與制度明顯並不適用。在這裡出現的問題,國家的文明力量無法解決」。文明的殖民使命需要設置一個懸置普遍律法,「明顯並不適用」的拓樸空間。
而道格拉斯的身而為奴,在他決心放棄宗教儀式(「祈禱」),起身掐住奴隸主喉嚨「感覺到他的血液在我的指甲間流淌」的衝突中,瞬間被解放,「我不再是奴性的懦夫,為塵埃般小人物的皺眉而顫抖,長期處於威脅下的精神被喚醒,得到了男子氣概的獨立。我來到了一個不再害怕死亡的時刻」。
道格拉斯的「暴力」是對黑格爾式主奴鬥爭的顛倒,奴隸之所以為奴隸在於畏懼死亡,而主人在精神的優越來自他對於死亡的無畏,主奴的辯證在於當奴隸為奴而不再為了自身的自然需求而勞動時,主奴的精神位階即預設了逆轉,只有不再為自身而勞動的「自由」,才能創造興趣化的人造世界,而只能耗費的主人在世界歷史的舞台終將被奴隸取代。
而道格拉斯的故事很不同,奴隸把死亡看作一個更好的選擇,更優於在園的奴隸制中的「非人」,暴力並沒有主奴關係確立的時刻終結,主奴關係的辯證環節也不在於通過勞動的教養,而是更為「野蠻」的暴力。
《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文明與野蠻》認定,文明與野蠻並非緊貼毗鄰,而是始終存在「敘事得以介入、思索的空缺」。與文明與野蠻之間的閾界同樣是非裡非外,此一空缺的空間會在突現的那一刻徹底翻轉文明與野蠻的進步歷史:總督佐久間之死的懸疑、跨種族的性關係及其帶來的身分認同混雜,以及在南洋戰場的「艱苦與恐怖」殺戮中,感受青春熱血燃燒所意識到的平等承認意識。
無向的「再復魅」風帆
《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文明與野蠻》置疑了除魅與復魅並行的「想像共同體」理路,由是班雅明的文明與野蠻論題得以貫穿全作,而其中並行並相互抗拮的兩條軸線是除昧與除魅的暴力,再借用班雅明的話來說,它們分別是迷思暴力與神聖暴力:
如果迷思暴力是打造律法,神聖暴力就是律法的毀棄;如果迷思暴力設立了疆界,神聖暴力則摧毀一切疆界,如果迷思暴力同時帶來罪愆與報復,神聖暴力則只是救贖。
確切來說,本作或許應該題為「再復魅」,書中的復魅手勢固然往往訴諸去文明化的「海洋、土地,與身體的游牧勞動」,卻並非是向著某種原初狀態,向著某種「野蠻」的復歸。在不同歷史環節中除魅的神聖暴力敘事,所動搖的是文明與野蠻的辯證,而非是訴求暴力的具體主張,一如法農對於「種族主義、仇恨、憤怨以及『報復的正當欲望』都不足以孕育解放的戰爭」的警示,解殖的「暴力」最終是為了瓦解殖民者在心理與物理上設下的暴力迴圈,而不是以暴制暴。
「再復魅」不只是對於除昧暴力的批判,或許也不僅僅是除魅暴力的救贖,更多是一種如本作結語所自述的書寫「姿態」:在大海中央對島嶼的回看,從無定的異托邦之地回望,對於共同體解脫文明與野蠻辯證的無向想像。
除昧與復魅的書寫與詞語最終都是「再復魅」的風帆,《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文明與野蠻》即是這張風帆,而如何揚起帆?如何漫遊於不知何方?將是讀者的任務。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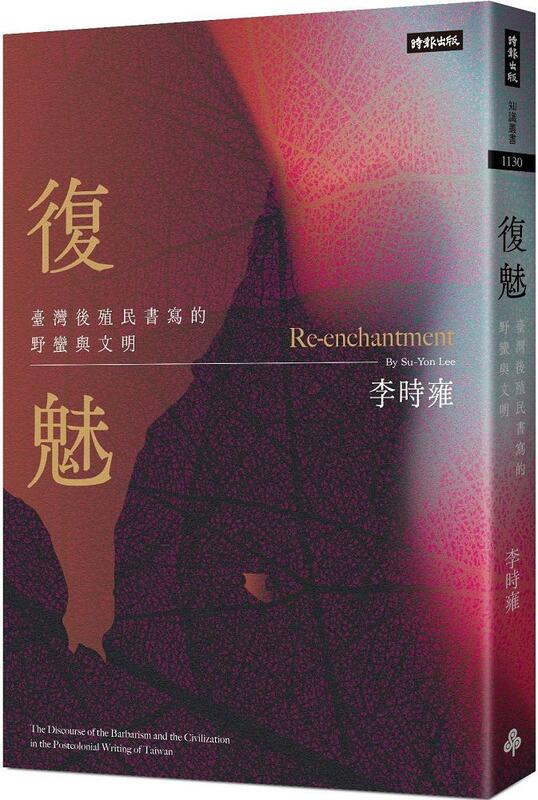
書名:《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野蠻與文明》
作者:李時雍
出版社:時報
出版時間:2023年4月
- 怎麼看《三體》才不會像小粉紅? - 2024 年 4 月 5 日
- 2014何以成為全球反中帝零年 - 2024 年 3 月 25 日
- 從未結束的冷戰 - 2024 年 3 月 1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