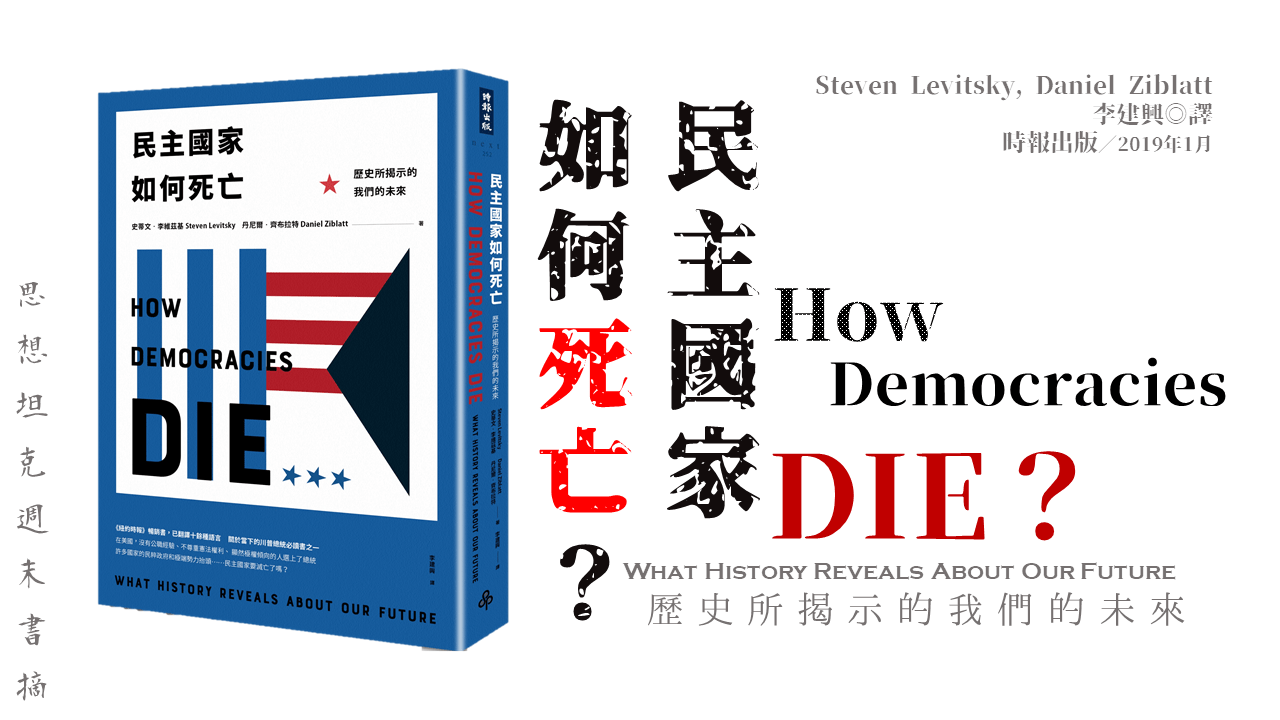
民主的護欄
世世代代以來,美國人對憲法一直有強烈的信心,以此為核心認為美國是天選的國家,有神意指引,是全世界希望與機會的燈塔。雖然這個世界觀可能褪色了,對憲法的信賴度仍然很高。一九九年的民調發現八十五%美國人相信憲法是「美國在近一百年來成功」的主要理由。確實,我們的憲法制衡體制是設計來防止領袖集權濫權的,在美國史上多數時候,真的有效。林肯總統在內戰期間的擴權在戰後被最高法院逆轉了。尼克森總統的非法竊聽在一九七二年水門案之後被揭發,引發了國會大舉調查與兩黨施壓設置特別檢察官,最後在確定面臨彈劾時迫使他辭職。在這類例子裡,我們的政治機制扮演了對抗專制傾向的重要堡壘。
但是憲法的護欄本身足以確保民主嗎?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設計良好的憲法有時也會失靈。德國的一九一九年威瑪憲法是國內最偉大的法學家設計的。它長期備受推崇的Rechtsstaat(「法治」)是公認足以防止政府濫權的。但在一九三三年面對阿道夫.希特勒奪權,憲法和法治都迅速崩潰了。
或者想想後殖民拉丁美洲的經驗。該區域許多新獨立的共和國直接以美國當模範,採用美式總統制、兩院制國會、最高法院,有的還採用選舉人團跟聯邦制。有的國家寫出的憲法幾乎照抄美國版。但是區域內幾乎每個新生共和國都陷入內戰與獨裁體制。例如,阿根廷一八五三年制定的憲法很像美國的:三分之二的本文直接照抄美國憲法。但這些憲政安排沒什麼能力防止十九世紀末的選舉舞弊、一九三○與四三年的軍事政變,以及裴隆的民粹專制。
同樣地,菲律賓一九三五年的憲法向來被形容為「忠實拷貝美國憲法」。在美國殖民監督下起草,經過美國國會批准,這份憲章「提供了自由派民主制的典型範例」,權力分立、權利法案、總統限任兩屆。但是費迪南.馬可仕總統不願意在任滿後下台,一九七二年宣布戒嚴後相當輕易地過關。
如果憲政規則足夠,那麼裴隆、馬可仕或巴西的瓦加斯這種人──都在字面上包含大量制衡機制的美式憲法下就職──就會是一或兩任總統而非惡名昭彰的專制者。
即使設計良好的憲法也無法靠自己保障民主。舉例,憲法永遠不周延。就像任何規則,總有無數漏洞和模糊處。無論多詳細,沒有操作手冊能預料到所有可能的意外狀況或診斷在所有情境下該怎麼做。
憲政規則也總是要靠各方面的解釋。說到美國參議院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角色,具體來說,「建議與同意」是什麼意思?「犯罪與行為不檢」一詞建立的彈劾門檻是什麼?美國人辯論這些憲政問題幾百年了。如果憲法權力有多種解讀方式,就可能被用在創造者沒料到的方式。
最後,憲法的條文可以用侵蝕立法精神的方式在表面上遵守。勞工抗議最具破壞性的形式之一就是「照規則工作」活動,工人們只做契約或職務說明上要求他們做的事,絲毫不多。換言之,他們嚴格遵守書面的規則。幾乎毫無例外,職場會立刻癱瘓。
因為所有法律系統先天必然有漏洞和模糊,我們不能只依賴憲法來捍衛民主反抗企圖專制者。「上帝從未賦與任何政治家、哲學家或任何人足夠的智慧,」美國前總統哈里遜寫道,「去坑騙一個人人都可以被取代的政府體制。」
那也包括我們自己的政治體制。美國憲法在大多數時候,是份高明的文件。但是原版的憲法──只有四頁──可以用很多不同甚至矛盾的方式來解釋。例如,我們沒什麼憲法機制防止在名義上獨立的機構(例如聯邦調查局)安插效忠自己的人馬。據憲法學者阿濟茲.哈克(Az iz Huq)和湯姆.金斯柏格(Tom Ginsburg)說,防止歷代美國總統搞定裁判讓他們對付政敵的只有「薄弱的傳統」。同樣地,憲法對總統有權透過公告或行政命令採取片面行動沒有規定,也沒有定義危機時期行政權的界線。所以,哈克與金斯柏格最近示警說「[美國]民主的憲法與法律護欄……在真正的反民主領袖面前,終將被證明相當容易操弄。」
如果一七八七年在費城制定的憲法不是確保美國民主這麼久的東西,那又是什麼呢?許多因素都很重要,包括美國的龐大財富、廣大的中產階級,還有活躍的公民社會。但我們認為答案也大多在於強力民主規範的發展。所有成功的民主國家都仰賴不成文規則,雖然憲法或任何法律沒寫,但眾所周知又被尊重。在美國民主制度中,這一直很重要。
如同社會的各個層面,從家庭生活到企業與大學的運作,不成文規則對政治也有很大影響。要了解它如何運作,請想想鬥牛籃球賽的例子。街頭籃球不受NBA、NCAA或任何聯盟制定的規則管轄。也沒有裁判負責執法。只有對什麼事可以接受什麼不可以的共同理解,能防止這類比賽陷入大亂鬥。鬥牛籃球半場賽的不成文規則對有打球的人都耳熟能詳。以下是一些基礎:
- 得分是一分一分算,而非正規籃球賽的兩分,勝隊必須贏兩分。
- 進球的隊負責控球(「進籃者拿球」)。得分的隊把球帶到罰球區頂端,為了確保防守隊準備好了,把球傳給最接近的對手球員「檢查」。
- 持球開始的球員不能直接投籃;必須把球傳出去。
- 球員自己抓犯規但是有限制;只有嚴重犯規才算數(「沒見血,不算犯規」)。但是有人叫犯規時,必須尊重其意見。
當然,民主不是街頭籃球。民主國家確實有明文規則(憲法)和裁判(法院)。但在明文憲法有自己的不成文遊戲規則強化的國家,才能運作得最好,維持得最久。這些規則或規範扮演民主的緩衝護欄,防止日常的政治競爭惡化成毫無保留的衝突。
規範不只是個人特質。它不是單純仰賴政治領袖的善良品德,而是在特定社群或社會裡成為常識的共同行為守則──被成員們接受、尊重與奉行。因為沒有明文規定,通常難以看見,尤其運作良好的時候。我們可能誤以為那是不必要的。但是這麼想就錯得離譜了。就像氧氣與乾淨水,規範的重要性在缺乏時最感受得到。規範夠強時,違規會讓人表示不以為然,從搖頭嘲弄到公開批評與直接排斥。違反規範的政客可想而知要付出代價。
不成文規則在美國政壇到處都是,從參議院與選舉人團的運作到總統記者會的規格。但特別有兩項是民主制度運作的基礎:互相容忍與制度性自制。
互相容忍是指只要我們的對手照憲法規則走,我們接受他們有存在、競逐權力與統治的平等權利的概念。我們或許不同意,甚至很討厭對手,但我們還是承認他們的正當性。這表示承認我們的政治對手是正派、愛國、守法的公民──像我們一樣熱愛國家也尊重憲法。這表示即使我們認為對手的觀念很愚蠢或頑固,並不把他們看成存在的威脅。我們也不把他們當成叛賊、亂黨或無法接受。對手獲勝時我們可能在開票夜掉淚,但我們不認為這種事就是世界末日。換個說法,互相容忍是政治人物承認歧異的集體意願。
這聽起來或許只是常識,政治對手不是敵人的觀念是個傑出又深奧的發明。整個歷史上,反對當權者一向被視為叛國,事實上,正當反對黨的概念在美國成立時仍幾乎是異端邪說。美國早期黨派爭戰的雙方──約翰.亞當斯的聯邦黨和湯瑪斯.傑佛遜的共和黨,互相把對方看成共和制的威脅。聯邦黨自認是憲法的化身;在他們看來,反對聯邦黨就是反對整個美國的計畫。所以傑佛遜和麥迪遜籌組後來的共和黨時,聯邦黨把他們當叛徒,甚至懷疑他們窩藏差點跟美國開戰的法國革命軍親信。至於傑佛遜的信徒,則指控聯邦黨是托利黨,受英國支持陰謀恢復君主制。兩邊都希望打敗對方,採取步驟(例如一七九八年的客籍法和懲治叛亂法案)以合法懲罰區區的政治異議。黨派衝突激烈到很多人害怕新共和會崩潰。在幾十年的過程中,敵對的美國兩黨才逐漸辛苦地認知他們可以當對手而非敵人,輪流執政而非互相毀滅。這個認知是美國民主的重要基礎。
但互相容忍不是所有民主國家與生俱來的。例如西班牙在一九三一年進行第一次真正的民主轉變時,期望很高。由曼紐埃.阿薩尼亞(Manuel Azana)總理領導的左傾共和黨新政府決定實施議會民主。但是政府跟兩極化的社會有所衝突,民間從左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到右派的君主擁護者和法西斯主義者都有。敵對陣營不是互相視為黨派對手而是死敵。一方面,右翼天主教徒與君主擁護者驚恐地看著他們最重視的社會機構──教會、軍隊和君主──被剝奪特權,不接受新共和國的正當性。依某位歷史家的說法,他們自認是在對抗「布爾什維克化的外國勢力」。
鄉下的騷亂和針對教堂、修院等天主教機構的幾百次縱火行為讓保守派感覺四面楚歌,陷入陰謀論的怒火。宗教權威人士陰沉地警告,「我們現在被捲入漩渦……我們必須準備好面對任何事。」
另一方面,許多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共和黨人認為右派,例如天主教右翼自治組織聯合會(CEDA)的領袖吉爾羅伯斯(Jose Maria Gil-Robles),就是君主擁護者或法西斯反革命分子。頂多,許多左派把組織良好的CEDA看成只是陰謀以暴力推翻共和的超保守君主擁護者的幌子。雖然CEDA顯然願意以選舉競爭參與民主賽局,領導階層卻拒絕無條件效忠新政權。所以他們仍受到極度懷疑。簡單說,左派共和黨和右派天主教徒、君主擁護者都不完全接受對方是正當的對手。
互相容忍的規範薄弱時,民主很難維持。如果我們把對手看成危險的威脅,他們當選我們會很恐懼。我們可能決定不擇手段打敗他們──潛藏著專制手段正當化的危險。被貼上罪犯或叛徒標籤的政治人物可能入獄;被認定對國家構成威脅的政府可能被推翻。
因為缺乏互相容忍的強力規範,西班牙共和迅速崩潰。新共和在右翼的CEDA贏得一九三三年選舉成為國會最大黨之後陷入危機。執政的中間偏左共和黨大聯盟崩潰,被排除社會主義者的少數中間派政府取代。因為許多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共和黨人認為最初的(一九三一到三三年)中間偏左政府是共和國的化身,企圖撤銷或改變政策被他們視為從基本上對共和國「不忠」。包含一批法西斯傾向年輕黨員的CEDA翌年加入政府之後,許多共和黨人把它當作深刻的威脅。左派共和黨宣稱:
把共和國的政府交給敵人的可怕事實就是叛國。[我們]與政權的現有機構不再合作,重申[我們的]決定以所有手段捍衛共和國。
面對他們視為向法西斯主義沉淪,左派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加泰隆尼亞和阿斯圖里亞斯叛亂,呼籲大罷工並組成平行政府。右派政府殘酷地鎮壓反抗行動。然後試圖把整個共和黨反對陣營和叛亂掛勾,甚至囚禁(沒有參與暴動的)前總理阿薩尼亞。國家逐漸陷入暴力衝突,街頭鬥毆、放炸彈、燒教堂、政治暗殺與政變陰謀取代了政治競爭。到了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的新生民主轉變為內戰。
我們研究過的幾乎每個民主崩潰案例,企圖專制者──從歐洲兩場大戰之間的佛朗哥、希特勒、墨索里尼到冷戰時代的馬可仕、卡斯楚、皮諾契特到最近的普丁、查維茲和艾多根──都把對手貼上存亡威脅的標籤來合理化他們的集權。
民主存續的第二個重要規範就是我們所謂的制度性自制(institutional forbearance)。自制意味著「耐心的自我控制;克制與容忍」,或是「保留不行使合法權利的行為」。方便我們解說,制度性自制可以想成避免雖然符合法律條文卻明顯違反其精神的行為。自制規範強大時,即使這麼做嚴格來說是合法的,政治人物不會用盡他們的制度特權,因為這種行為可能危害現有制度。
制度性自制的來源是比民主本身更古老的傳統。在君權神授的時代──宗教的認可提供君主權威的基礎──沒有世俗法律能夠限制國王的權力。但是歐洲許多民主時代之前的君主仍然表現克制。畢竟為了顯得「神聖」,需要智慧與自制。當理查二世之類的人物,在莎翁出名的歷史劇被描繪為暴君,為了徵稅與掠奪濫用他的王室特權,他沒有違法;只是違反了習俗。但是這種違反有嚴重後果,因為引發了血腥的內戰。如同莎翁角色卡萊爾在劇中警告同胞,放棄自制意味著「英國人的鮮血將會灌溉土地……而未來世代為此惡行呻吟苦惱。」
如同神聖權利的君主國家需要克制,民主國家也是。不妨把民主想成我們想要永遠玩下去的遊戲。為了確保遊戲的未來回合,玩家必須克制不能淘汰敵隊或把敵隊抹黑到他們拒絕明天再玩的程度。如果對手不玩了,未來就沒有遊戲了。這表示雖然個人玩遊戲就是想贏,但也要有某個程度的克制。在鬥牛籃球賽中,我們玩得很猛,但是知道犯規不能太過份──而且只抓嚴重的犯規。畢竟,你來到球場是打球,不是來打架的。政治上,這通常表示基於文明和公平競爭,不出爛招或狠招。
民主國家的制度性自制應該是怎樣?想想英國的政府組成。如同憲法學者兼作家基斯.惠廷頓(Keith Whittington)提醒我們,挑選英國首相是「王室特權事務」。
理論上,國王可以挑選任何人來扮演這個角色籌組政府。」實務上,首相是能夠在下議院贏得多數支持的國會議員──通常是國會最大黨的黨魁。現在我們把這制度視為理所當然,但國王有好幾百年自願遵守。至今還是沒有成文憲法。
或以總統任期限制為例。美國的大半個歷史上,兩任限制不是法律而是自制規範。一九五一年通過第二十二修正案之前,憲法並沒有規定總統做兩任之後要下台。但是一七九七年喬治.華盛頓做滿兩任之後退休設定了強力的先例。如同第一位遵守此規範的在位總統湯瑪斯.傑佛遜觀察道:
如果[總統]的職務終結沒靠憲法指定,或有實務支持,他名義上四年的任期實際上會變成終身……萬一有人成為第一個延長任期超過兩任者,我不得不成為無視傑出前任者設下的明確先例那個人。
就這樣建立的非正式兩任限制後來證明非常有效。連傑佛遜、安德魯.傑克遜和格蘭特等有野心又受歡迎的總統也克制不去打破。格蘭特的友人鼓勵他尋求第三任時,引發了眾怒,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宣稱:
華盛頓與其他總統建立的先例……在第二任之後……卸任已成為……我們共和體制的一部分……任何偏離這項經過時間考驗的習俗實乃極不明智,不愛國,也隱藏著對我們自由制度的危害。
同樣地,一八九二年民主黨也拒絕提名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競選不連續的第三任,警告這樣的候選人會違反「不成文法」。只有小羅斯福在一九四○年連任明顯違反了這個規範──這才引發後來通過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
自制的規範在總統制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如同林茲主張,分裂的政府很容易形成僵局、失能與憲政危機。不受約束的總統可能控制最高法院或以行政命令施政繞過國會。而不受約束的國會可能阻擋總統的每一步,杯葛政府預算威脅把國家打入混亂,或憑可疑的根據彈劾總統。
自制的相反就是以不受約束的方式用盡制度性特權。法學家馬克.圖施奈(Ma rkTushnet)稱之為「合憲狠招」:照規則走但是逼到極限而且「志在必得」。這是以永久性打趴黨派對手為目標的某種制度戰爭──不在乎民主遊戲能否持續。
兩位作者皆為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
李維茲基的研究聚焦在拉丁美洲與開發中國家。他是《競爭式威權主義》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一書的作者,得過許多教學獎項。
齊布拉特的研究聚焦在民主化、民主崩壞、政黨、國家建設和歷史政治經濟,主要是十九世紀至今的歐洲。他著有獲得多項獎項的《保守黨與民主的誕生》(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一書。
李維茲基和齊布拉特都為許多媒體寫作,包括Vox新聞網與《紐約時報》。
書名:《民主國家如何死亡》作者:史帝芬.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
意者:李建興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時間:201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