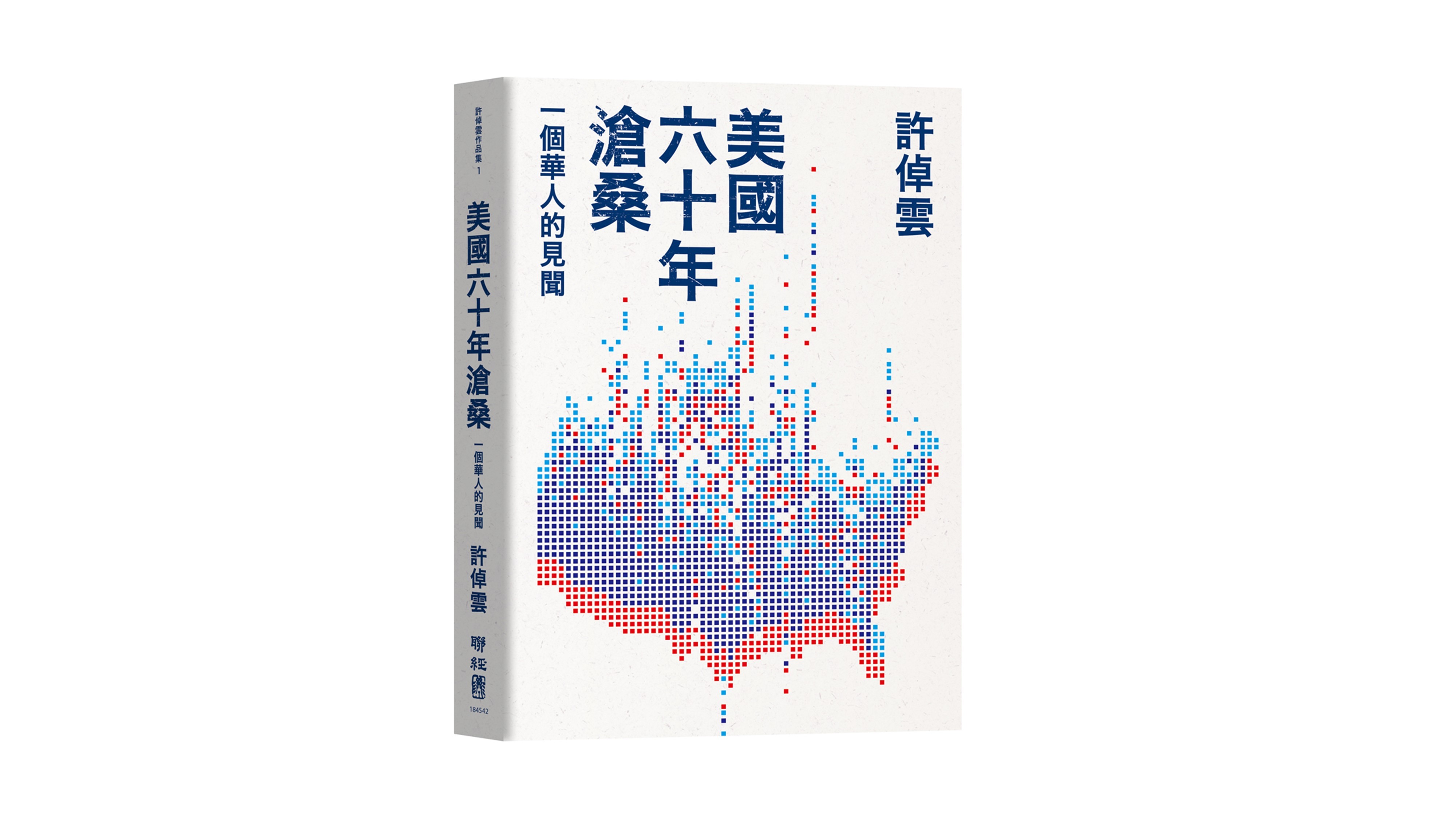
第十一章美國發展的文化脈絡
任何大的人類共同體,其謀生的部分是經濟,其組織的部分是社會,其管理的部分是政治,而其理念之所寄,心靈之所依託則是文化。以個人生命作為比喻,文化乃是一個共同體的靈魂。本章的主題,則是從各個時代承負,我們可以體會美國的文化脈絡,如何不斷轉換。
先從中國和美國歷史,作一比較:中國是一個經歷幾千年的共同體,這龐大共同體的靈魂,是數千年來演變的過程。美國只有三百年的歷史,其開國之初,從歐洲帶來的文化,就是美國三百年來的立國之本:他們一切的典章制度,所以設計的依據,及其人情風俗所寄託的理念。在中國的共同體,追溯中國文化的最初理念,由於時代久遠,演變過程之複雜,其實已經沒有提到源頭的必要。美國的個例則不一樣;三百年來,美國一切的變化,萬變不離其宗,都還多多少少可以從最初的根本理論,見其端倪;轉變過程,也可以從這個端倪作為零點,檢查其變化之關口及其起伏。
在五月花登陸美國以前,歐洲人不是沒有在北美大陸立下基地。如前所說,在今天馬里蘭、佛州和南、北兩卡州的沿河岸上,英國人也曾經有過多次嘗試殖民。例如,英國人於1607年,就在今天的詹姆斯鎮附近,開闢過殖民地,也維持了一段時期,可是不能發展。此外,西班牙人、法國人、荷蘭人,都前前後後在美國的東岸,紛紛尋找自己的立足點。在美國的西岸,從墨西哥出發的西班牙拓殖隊伍,也曾經伸展到北加州,建立若干據點。這些不同的個例,其不能具有五月花在普利茅斯建立一樣的重要性,則是因為五月花號帶來的移民,是一群人,以其堅定的信仰,要在新大陸上建設一個新的國家,以落實他們所憧憬的目標。
五月花號的移民,都是歐洲宗教革命之後,最崇仰自由的一批加爾文派信徒。他們堅持單一神信仰,並且以為神和信眾之間,有直接的感應;每一個信徒,都是直接承受神的恩典(providence)。這一個理念,使加爾文派新教的信徒們,以其堅定信仰,具備最強烈的自信心。他們以為自己所作所為,是根據神的指示,絕對沒有錯誤;他們能夠成功,本身就是神意旨的落實:他們成為選民,是神已經決定的。因此,每個選民必須要以自己的成就,彰顯神的庇佑和神的抉擇。
基督教的單一神信仰,最早的源頭乃是埃及阿克那登法老所創建的信仰。這一宇宙間獨一無二的大神是太陽神:太陽神給所有天下萬物生命和庇佑,因此,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而且所有生命的存在,由於神的護持,他們一切行為,也是單一神創造意旨的體現。雖然從埃及的源頭到基督教,中間經過不同階段的轉折,摩西從埃及帶出單一神觀念時,乃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也從這個理念上,才有從宗教革命以後,根據教義引申為個人自由、人間平等:這兩個重要的觀念。
從中世紀以來,歐洲的居民,在戰爭部落占據土地後,建立封建制度,將人民分為貴族、平民、奴隸:一個階級化的社會。宗教革命以後,經歷啟蒙時代,歐洲各處都捲入反封建的浪潮。法國大革命和英國的光榮革命,都提出以平等解除階級的隔離、以個人自由解除封建制度人身的束縛。法國革命提出的博愛,則闡明人與人之間,應當如同兄弟手足,不應該再有不同的身分。相對而言,英國的光榮革命,則是農村大地主爭取自己的財產權和人身權。英、法兩國革命的方式,及其的理念背景,是相當不同的。
五月花號的移民,來自英國,英國當時的新教,是依據王權向教權奪來的信仰自主權。英國的國教會,只是一個獨立於羅馬的公教會而已。五月花號上的移民們,雖然來自英國,他們的宗教信仰,卻是西歐大陸上,最激烈的加爾文主義。在到達北美之後,雖然理論上,他們還接受英國王室的統治,只是在海外建立英王政府所管轄的殖民地而已。實質上,登岸之時,他們就已有決心,要在這個新的土地上,創建一個新的制度:神恩的庇護下,落實每個人自己應有的平等和自由。
於是,在新英倫最早的地方政權,除了他們自己建構的地方自治體以外,當地加爾文派的清教教堂,擁有極大的威權。他們的法律,是自己創建;立法的理論依據,都必須追溯到聖經傳達的理念。當時,法庭根據法律的決定,和根據教義判斷的是非對錯,兩者相輔而行。早期新英倫的英國殖民地,竟可稱為一個神權政體。獵巫和懲淫,在新英倫的社區中,其實是根據教義,法律以外的舉動。教權之專斷、嚴酷,與不合理,超出我們想像之外。如此結構的神權社區,其實並不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則。
這一段開拓的經歷,無論如何是相當辛苦的過程;如果沒有清教徒秉持神恩的勇往直前,這些殖民者很難在陌生的新大陸上,堅持開展的勇氣和能力。從那時候以後,如前面若章已經敘述過,一波一波的新移民進入美國,推向內陸。那些新到的人群,有的是同一個宗派的教徒,有的是基於經濟動機的移民。開拓部隊,是在歐洲沒有發展餘地的人群;他們寧可拋棄一切,進入美國,前途未知,卻是勇往直前:他們在顛簸的篷車上,翻山越嶺,度河過江,在洪荒新世界,覓一空間,站定腳頭。這些開拓者的精神,是美國的史家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特予強調,可以代表美國立國的精神。向西開拓的歷史,即是美國整個歷史的定調。
從好的方面說,這種精神一方面是承受著神恩,要以自己的行為,表彰神的恩典:這一種個人主義,如此有恃無恐,這些開拓者才有勇氣和決心,一步步往前走。可是,從另外一個方面看,這些依仗上帝眷顧的個人,他們自以為是神的選民,對他們而言,「神的選民」四個字,就讓他們自己的地位,和其他人有了區隔。異教徒不能蒙受神恩,乃是異類;那些他們認為是野蠻人的原居民,簡直是羞以為伍的異類。對於這些人,蒙受神恩的個人主義者,可以理直氣壯地任意處置。在美國歷史上,正因為這種不成理由的理由,論百萬計的原居民,被他們驅趕離開自己的土地,甚至於以近代的武器,對付弓箭,任意地殺戮和驅趕。從他們手上奪取的資源和土地,白人可以理直氣壯地據為己有。這些錯失,在今天看來,是人類歷史上的污點,但是在當時那些開拓者的心目中,他們卻正是以這種理由,毫不留情地將新大陸占為己有。
向西開拓,成功與失敗,在當時人是一半一半的機會。失敗者葬身異域,成功者卻可以自我肯定:神的眷顧就是因為我的能力和才幹。這種自我肯定,是個人主義轉變為獨占和自私的關鍵。在激烈的競爭考驗之中,能夠生存、能夠成功,就是一個證明:「我是優越者,所以我能成功。」在達爾文自然演化論,當作「真理」的時代,從生物演化論引申出來的社會演化論,即可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正如生物界的適者生存一樣,成功與失敗的差別,就在成功者站住了,失敗者倒下了。將生物演化論中弱肉強食的原則,引申到社會演化論時,個人主義成功者對失敗者不會有憐憫,更不會同情。
上面兩個階段的推論,演變為美國社會上,瀰漫著一片無情競爭,「勝者為王」的觀念。一方面從宗教的神恩衍生,一方面又將生物科學的演化論,武斷地轉變為人類關係的科學主義,儼然定論。數百年來,在美國的一般觀念中,卻是影響到他們的行為,以至於清教徒們所秉持的,在神的面前一切都平等,在神的庇護下,所有人都應當有自由,竟然轉變成為,「我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我是勝者。」這個現象,到今天並沒有嚴重的修正。―這一理念,或者社會性的意旨,乃是這一新大陸的新舞台上,劇中人演唱的主旋律。
這一新局,畢竟還是有其從基督教承受的理想層面,亦即其中的博愛與公義。憑藉這一溫柔的曲調,在社會主義浪潮進入美國時,作為弱者的勞工,可以憑藉集體的力量,向雇主爭取平等的人權,要求合理的待遇;弱者的立場,也可以要求婦女、兒童,不應當擔任過分勞累的工作。這一番新的社會正義,其實還並不能真正平衡上述強烈個人主義,所造成的獨斷和自私。迄於現代,美國才出現進步主義思潮,將社會公義和公平,視為應當落實的要事。
在工業發展的階段,工商業的園地,就等於是向西開拓時候的內陸;龍騰虎躍的戰場,成功與失敗的標誌,都是以金錢衡量。那些鍍金時代的大亨們,他們努力工作,聚集龐大財富,創建企業帝國:他們的動機,也就是上述特納所指的開拓精神。好處在他們努力工作,勇往直前,從無到有,從有到多。匹城的卡內基而論,據說他每日工作十七、八小時,睡覺只有四個小時左右,他飲食清淡,生活簡單,他的臥室是一張相當行軍床樣的單人床。
這些人物的努力工作,他們要求的回報,就不是物質上的享受,也不是貪得無厭的欲望,而是實踐神揀選了「我」,「我」對神的回應。他事業成功以後,他所有的產業,都捐為公益之用:辦了一個大學,捐了全部蘇格蘭、愛爾蘭和賓州地區的公共圖書館,捐了自然博物館,也捐助了紐約的音樂廳,還設立了一個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基金會。他自己沒有子女,身後沒有留下家產給自己家人。類似例子,洛克斐勒聚集了龐大的財富。在他身前,他將大部分的財富捐作公用他:留在人間最大的貢獻,是設立美國第一流的大學,芝加哥大學,和無數教會學校和教會醫院:都是由他補助。中國第一間現代醫學院和醫院,就是他所捐助的。
洛氏基金會總財富,大概比整個台灣的財富還要巨大。這個基金會支持和補助各種公益工作,遍及全世界,尤其在落後地區,非洲、南美洲等處。卡氏、洛氏、同時代的巨富,例如福特、貝爾、梅隆……等人,均捐財推動公益事業。他們的動機,幾乎都因宗教信仰,身體力行,修德為善。我們欽佩這些巨富:他們能夠將自己聚集的財富,回饋社會。他們如此行為的動機,還是基督教倫理,對於他們的感召。―凡此現象,因是前述宗教情緒的體現。
正在如此認知和體現利他情操的時代,美國卻也出現另一潮流:立足於個人主義,轉向於滿足個人欲的享樂主義。二戰以後,由於美國迅速地繁榮,儼然躍登世界發展領導者的霸主地位。美國聚積了巨大財富,於是,國民在工作之餘,也尋求娛樂。如此取向,出現了娛樂業和運動業,兩項吸金的產業。而且,由於平等原則,人人有權利盼望獲得如此滿足的機會:這就啟動了全民同樂,可以稱為民粹主義(populism)。這一轉變,則可導致在文化、經濟,和政治,各個領域,均出現巨大衝擊。
美國本來就有民間娛樂的傳統,例如,歐洲的民歌,轉移到美國,發展成為美國的地方音樂。在開拓內陸的時期,小劇團先是搭乘篷車,後來則是隨著鐵路和公路的路線,訪問各地農村,演劇、歌唱,娛樂內地的居民。在大城市中,有高級的歌劇院、音樂廳,和一般純藝術的劇場;也有在俱樂部或者酒廊,演出的小型樂隊。除這些分散全國各處的娛樂業以外,在紐約的百老匯,是美國娛樂業集中之所在,也是新作品、新形式競爭的中心。
以上這些文化娛樂活動,真正普及於一般人民,則是在一戰以後,快速發展的電影業。加州的好萊塢,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影片,一次製作,可以將影帶在全國放映,獲取巨利。因此,一戰和二戰之間,在娛樂業方面,最出色的成就,是電影業:一個佳作,上映千百場,一個明星,收入巨萬。然而,我們也必須了解,一個成功的巨星,攀登的路線上,有上千嘗試、不能繼續下去的失敗者。最得利的當然是出投資拍攝影片的大商家。
二戰以後,電視出現,過去無線電能夠將歌星的歌聲,話劇的對話,帶到客廳。電視出現,不僅是聲音,具體的形象,也就成為每一家直接可以享用的娛樂設施。電視台用這些娛樂業的產品,推廣電視使用,而以廣告作為主要的收入。這一波的發展,從黑白到有聲有色的彩色電視,在二戰後不到二十年時間,一躍而為,美國娛樂界足以和電影抗衡的一種新產業。電視上的巨星,不僅天天和觀眾對面,他們和電視公司累積的財富,又比當年電影業的數字,更為龐大。
乘著這一波波浪,美國的文化也得到刺激發展的新空間。那些歌唱的巨星,貓王、麥克.傑克森、英國來的披頭四……:如果沒有電視作為網絡,擴張他們的聽眾群,這一行業不可能在如此迅速的短期內,堆塑出擁有如此龐大群眾的巨星。當然,他們後面的經紀人,所獲得的利益,比他們所得更為龐大。數百萬、上千萬的歌迷,在各地還會舉行巨型的演唱會,例如,1960年8月胡士托音樂節(The Woodstock Festival)的大型音樂會,連續四日,參加者不下四十萬人。從那次成功的音樂會以後,歌迷們經常有機會舉辦音樂會,每次聚會,以萬計的群眾,在場應和。這一股力量,創造了美國新的文化,其特點是淺薄而煽情,熱鬧而空虛。在文化方面的衝擊,也在另一章討論。
與這些出於感性的群眾活動相伴而行,陽剛的體能活動,則是嗣後大為興旺的運動業。歐洲來的美國移民,秉持印歐民族好動的傳統,本來就有許多不同的體育活動。在美國創造的棒球、籃球,和將歐洲的足球改造的美式足球:這三種運動,原本都在學校作為體育項目。慢慢地,這些運動的參與者和觀眾,普及於全民。於是,本來每個小鎮上,在週末,公園一角,當地中、小學的孩子,比賽體育課學到的棒球。由此,逐漸發展為大學之間的比賽,以至最後,全國有幾個大賽的聯盟。同樣地,足球和籃球,以及最近又加入的曲棍冰球,都成為全國性層級比賽的項目。上述三種運動,很快就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休閒活動:許多職業球隊,定期比賽,提供市民觀賞。今天,運動產業在美國成為龐大的第三類產業中,重要的部分。
學校發展體育的原來用意,是提供青少年鍛鍊體能的機會。在工業化的社會之中,工廠工作並不一定是適當的體力活動。許多上下班的文員的工作,更使一般人缺少體力活動的機會。如此用心,原來的構想,乃是盼望人人都有機會,培養「身、心」均能健全。後日的變質,不是當年提倡體育者,設想的本意。在19世紀前半段,還僅是民間社區活動之一,並沒有後來商業性牟利企業的特色。
最初,各處大學、中學各有自己的校隊,校際友誼賽,並不涉及財利。逐漸,由於觀眾超過學生和校友,學校紛紛設立球場。校際比賽的門票收入,不是小數。學校的各種球隊變質,幾乎就是職業球員了。學校羅致有潛力的學生,遂以高額獎學金,吸收好球員。在學校中,這些球員不必注意課業,只須在球賽效力。他們入校目的,不在求知,而在開拓職業球員的機會。學校接受這些學生入學,目的在校際球賽的好成績,就可勸說富有的校友,捐助學校經費。於是,「身心俱健」教育宗旨,扭曲為學校、球員、和富有贊助人,三者之間的金錢遊戲。
今天,各地的大學,都紛紛擁有自己的球隊,也建有自己的球場。賓州大學和俄州大學的兩家大學,都曾經被人稱為「球場附設的大學」。那些球員,可能在中學時代,如果稍露頭角,就可能被職業的星探,吸收作為補充隊員,一步一步上升:他們成功的比例,也就和娛樂界的明星一樣,一個成功者後面,有上千上萬個失敗者。
無論成功,或失敗,他們僅是變相博戲的工具,並沒有成就入學求知的本意。
成功的球星本身,在球場上高速運動和撞擊,往往造成職業傷害,有的可以醫治,有的終身不治。例如,劇烈的腦震盪,成為球員的剋星,很少有球員可以躲開腦震盪的後遺症,或者骨骼、肌肉受傷的後遺症。他們暴得巨富,生活不再檢點,後果是糟蹋了人生,換來了毒品、醉酒和女色。
職業球賽,當然完全以營利為目的,則是在體能活動層面,加上博彩性質的吸引力。在1970年代的時候,全國大概只有第一排的大城市,會有某一項目的大球場。現在則是二線城市,也都擁有各類大球場。大球場的規模,從我剛到美國時看見,芝加哥的白襪隊球場,可以容納二、三千人,到今天,匹茲堡,一個二等的城市,可以有三、四個大球場,容納不同球隊的活動。棒球場、足球場的容量,都是五萬人左右。曲棍冰球和籃球,也可以有上千人的觀眾。如此龐大的觀眾群,撐起了一個非常殷富的運動企業。球隊其實都有老闆的,一個老闆集資若干,主辦一個球隊。球隊晉級升等,球員成為明星,也因此吸引更多的觀眾。球場和球隊的收入,和球員本身的薪資,都同步上漲。今天,一個全國級的球員,無論足球或棒球,年薪大概是數千萬美元。球隊主人的經營,除了門票以外,更多是賣廣告、食品、紀念品:累積為數十億的資產。
這些財富的來源,往往是工廠勞工階層,竭力儲蓄,盼望能夠在比賽季節,看一場球。一場球賽,一個觀眾支出是200至500元之間,加上旅費、住宿、飲食:一位勞工看一場球,他的月薪就要去掉一大塊。但是他們樂此不倦:因為美國人需要尋求刺激:快速地活動,群眾的吼叫,以及球星的英雄形象。許多人自以為,球隊代表城市,就是代表自己;我們到達匹城時,匹城三個球類隊伍都獲冠軍,「三冠王」的榮耀,市民們在第三次勝利時,全城徹夜狂歡。我詢問鄰居:「球員都是匹城本地隊青年嗎?」他瞪我一眼:「匹城隊,這個字,還不夠嗎?」在今天社區/社群均已淡漠疏遠時,本地隊勝利帶來的虛榮,填補了已經淡化的群體歸屬感。冷眼旁觀者看來,是聖經上所說「虛空的虛空」:如此泡沫,卻是將辛苦工作得來的收入,堆砌了無數的巨富,加上若干明星球員短暫的名譽和財富。
娛樂業和運動業,都是不能有累積的產業。固然電影,如果一部佳作,可以等於一部好的小說,永垂不朽,實際上,一百多年好萊塢,真正稱好的名著,大概雙手可以數的數字而已。運動場上,一場球賽下來,等於一陣風飄過水面,當時會激起漣漪,在場會感到興奮,後面沒有累積,也不會成為人類試探體力的極限。在我自己看來,這兩個行業在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上,正如同羅馬帝國,從盛而衰的時候,鬥獸場和格鬥場上的活動,乃是人群虛空的浪費。
更可悲嘆者,這兩種行業,尤其娛樂業,使用的媒體,所及群眾之廣大,以至於宗教人物和政治人物,也都見獵心喜,運用同樣的管道和場合,或者作為宣道之處,或者作為競選工具。以後者而論,羅斯福運用無線電,直接向全國的選民,解釋他的政策;甘迺迪利用電視,以英俊的外表、善辯的口才,吸引了無數的選票,而他的對手,卻還沒有認識這個新的工具的存在。現在的川普總統,利用資訊業中的傳播工具「推特短信」,傳達他的訊息,直達每個選民手上的手機。這種訴之於群眾喜好和工具的方便,已是今天政治活動中,無法擺脫的一個圈套。情緒化和直接印象,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辯論。如此的政治活動,導致的後果,即是譁眾取寵的「群眾民粹主義」(populism)。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7年赴美進修,半生流寓美國。在美讀書與執教的師友,帶領他參與社會活動,觀察社會結構與動態;尤其任教匹茲堡大學後,同事大多研究社會史,因此有緣理解美國社會和文化的種種變化。終身學習社會史和文化史,追求社會學、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知識。以為高度專業的學術研究,往往矚目廟堂動靜,卻忽略庶民的生活及其理念。深感美國文化與社會正在蛻變,目前整個世界正在經歷全球化過程。從英國移民建立13州,其實「美國」已經成形,從那時開始,三百餘年,美國的變化,經常會帶動世界各處的變化。目前世界正在經歷「全球化」,此時全球大格局的重組,海峽兩岸以及海外的華人,都難以脫離如此變局的影響。
書名:《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作者:許倬雲出版社:聯經出版時間: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