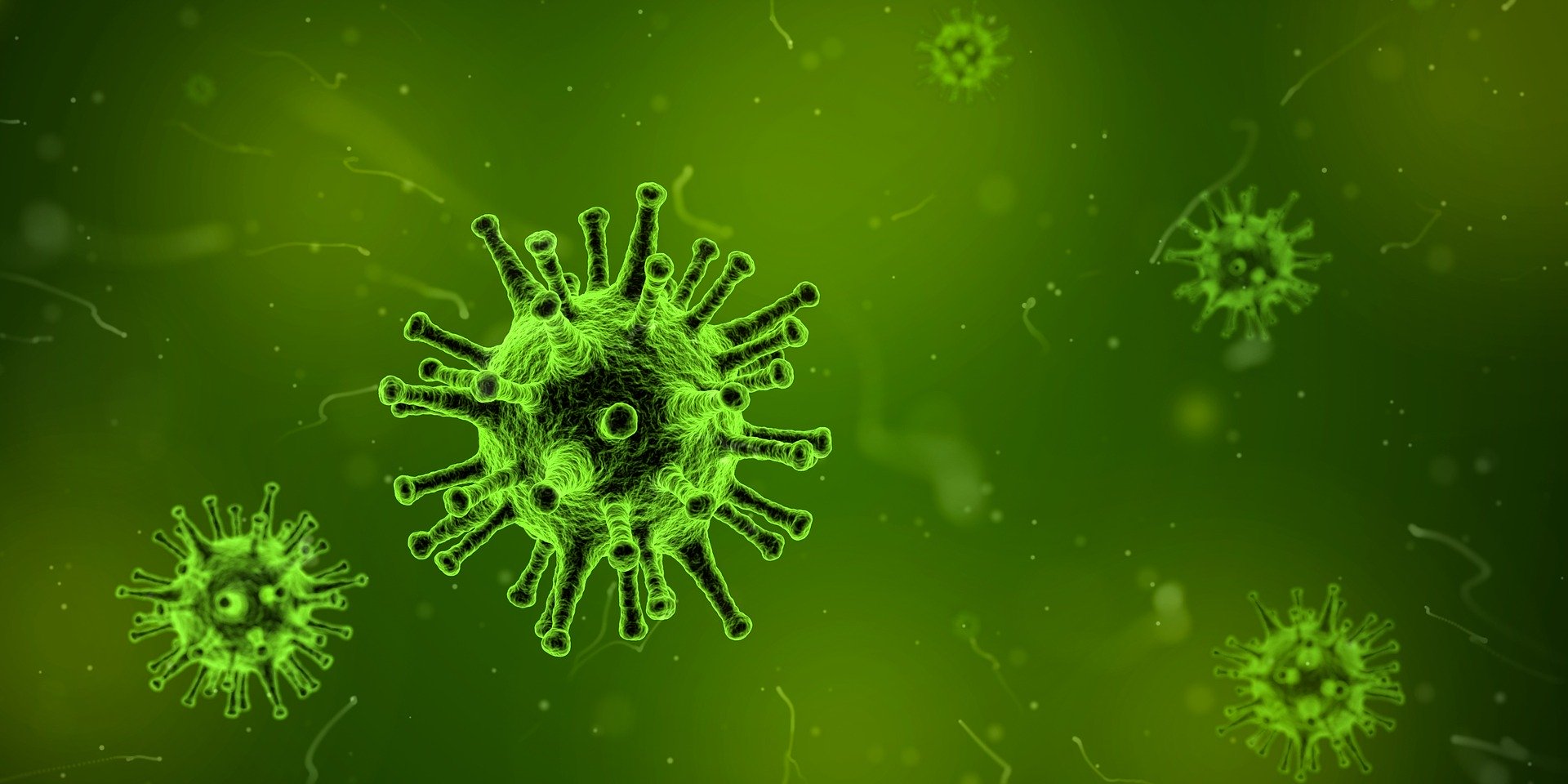
圖片來源:Pixabay
恐懼是古老的情緒,儘管科技日新月異,面對未確定感多少有所對策,但恐懼仍如影隨形。以生物觀點而言,恐懼是人類的理性設計,是存活的提醒機制,適當的恐懼可以保全人類,是一種演化論的情緒產物。從社會學習而言,恐懼也可能是模仿觀察而來,就如同制約反應而言,都是一種行為連結。
當然,恐懼也可能是不當的認知解釋後果,過度的災難化預期,認為恐懼事情終將發生的「恐懼的恐懼」(fear of fear),更容易引起孵化反應,無形中益加放大擔憂和恐怖。新型冠狀病毒的恐懼是詭譎暗影,如同弗洛伊德指出的不被理解的事物再度出現,就像是一個尚未找到位置的鬼魂。
面對武漢肺炎的疫情發展,恐懼感染的蔓延與民眾瘋搶口罩成為新興的社會現象。流行病的或疫情的英文是epidemic,辭源來自希臘字源epidemia,由介系詞epi (在…之上)和字根demic (人民)組合而成,字面意義是指流行或是人民之上,因此,該字詞本身意涵著一種人民之間的流傳共存狀態。流行病不只是區域性,更具規模性的越界傳播特性,因此,容易引發群眾的情緒感染。
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經由媒介訊息對於流行病案例動態的不斷暗示和滲透,不時散發民眾排隊搶購口罩的狀況,往往會使群體間產生如催眠效果般的感染作用,人們的意識、情感和判斷,彷彿全部隨著催眠師的指揮棒跳躍翻動。我們可以快速地給予情感一種情緒分類,如悲傷、罪惡或恐懼等等的指認,但那只是一種所謂的「道德經濟學」(moral economy),把複雜的情緒政治分配到一個合理領域,真正的關係網路反而被取消。
於是,我們看到這段時間在群眾效應的暗示下,加上口罩政治介入的情感道德經濟學效應,我們陷入集體恐慌的複雜心理社會反應,被簡化為擔心買不到口罩的恐懼歸類位置。
由於流行疫病威脅所伴隨的不確定感,具現風險的概念從抽象的層次轉化到親近的生活形態裡。社會學家紀登斯指出,「前現代」時期,人類以命運解釋危險,其整體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似乎充滿了作為基本信任的對立面的恐懼感。進入「現代性」社會,風險的概念代替了命運,「一切依歸如常」是信任和本體性安全得以穩固的基本要素,而這種心態也適用於具有嚴重後果的風險。
但如何歷經疫病風險後,就是回到日常生活,涉及的是危機管理是責任判斷,而非逞口舌之快的廉價消費。面對新興病毒的因應,並非只是挑動仇恨敵對的「硬」憎恨政治,而是需在危機與共的處境中帶出學者塞荷提到的「軟」實踐生活,「軟」是溫柔、寬厚、和平,同樣也帶有倫理、道德、知識、技術和踐行意涵。
健康無國界,在危機中的「軟」能夠使人們參與並且進入生命與我們共在的土地。但此刻,媒介政治的演出,以及政治人物的發言,無非使得防疫工作的安全網彷彿已是漏洞破裂,危機四伏的狀態。不求真實,只有利益計算、而無倫理知識的姿態,更醞釀恐懼溫床,讓擔憂如震源區,震盪不斷而日益擴大。
其實,不同的時代產造差異的經驗,驚嚇反應是當代的主要經驗。因為當代人類面臨更多難以理解的刺激,這些刺激逐漸變成受創的震撼,打破了存活的保護盾牌,受創的感受已經形構為生活的一部份。流行病毒侵襲所帶來的受創情感,可以分成兩個層面。
一類是普遍意涵的身體性受創;一類是社會建構符號(包含道德和宗教編碼),映射出心理上、存在上或靈性上的受苦狀態。面對流行病侵襲的恐慌,不僅是因為遭逢身體罹病風險的威脅,周遭他者或病人也承受汙名化,被認為失社會體面,甚至是「污染」的來源,相當程度也反映出人類本體上的不安感。
這樣本體上的威脅,無非是我們文明社會自詡的理性技術進步主義,向來是人們守護的功能性意義的喪失或空白的反應。若文明化的驕傲成果就在於達到理性目標,以為凡事都是可以思考的理性狀態,那災厄謎面的現形作為一種無以思索的幽靈,正沾染了文明社會的理性思維假象。
從震災、水災到SARS,到近期的武漢肺炎威脅,我們難免產生恐懼感。但恐懼力量的弔詭,不在於它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感受,而在於它是一種微不足道的感覺。正因為它的微不足道卻又無所不在,我們總是未能正視它,而藉由事件的現身,才又回過神知悉我們本來就在風險體系裡。「流行病」一詞已進入日常生活用語,恐懼文化使人我之間變得陌生,助長懷疑擔憂。恐懼文化的嚴肅後果,是任何問題都可能轉變為生死存亡的問題。民主社會更需要回應的是「貧窮是階級的,但風險是公平的」議題。
媒體傳播與政治口水的擴散在這焦躁時刻,儼然已成為另種入侵人類生活世界的變種病毒。面對不確定的生死攸關風險性,做好政府的防疫工作自我管理,按照政府宣導需要戴口罩的時機準備,體現一種權利隱含的義務(duties implied by rights)的主動積極公民參與,不隨波捲入這股盲流是重要的實踐課題。流行病恐懼文化的指向,更為重要的是喚起我們對於置身苦難中,人我之間的責任倫理。
當懷疑焦慮佔據了我們的生活想像,恐懼文化蔓延造成人我之間的罩阻,從卡繆的小說《瘟疫》啟發,顯示著瘟疫一如戰爭的謀害殺戮、考驗人性。當傳染、死寂、遺棄的、絕緣的封城處境在真實生活重演,更讓集體苦難的不可表徵性,轉化為可被陳述的歷史。當下,能夠對抗瘟疫的,就是正直,是人們理解並踐行「存在作為一種責任」義理的時刻。
作者為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 待招領的災變謎面──九二一大地震23周年 - 2022 年 9 月 21 日
- 我們都是緩期的倖存者 - 2021 年 4 月 7 日
- 後疫情狀態下防疫共同體 - 2021 年 1 月 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