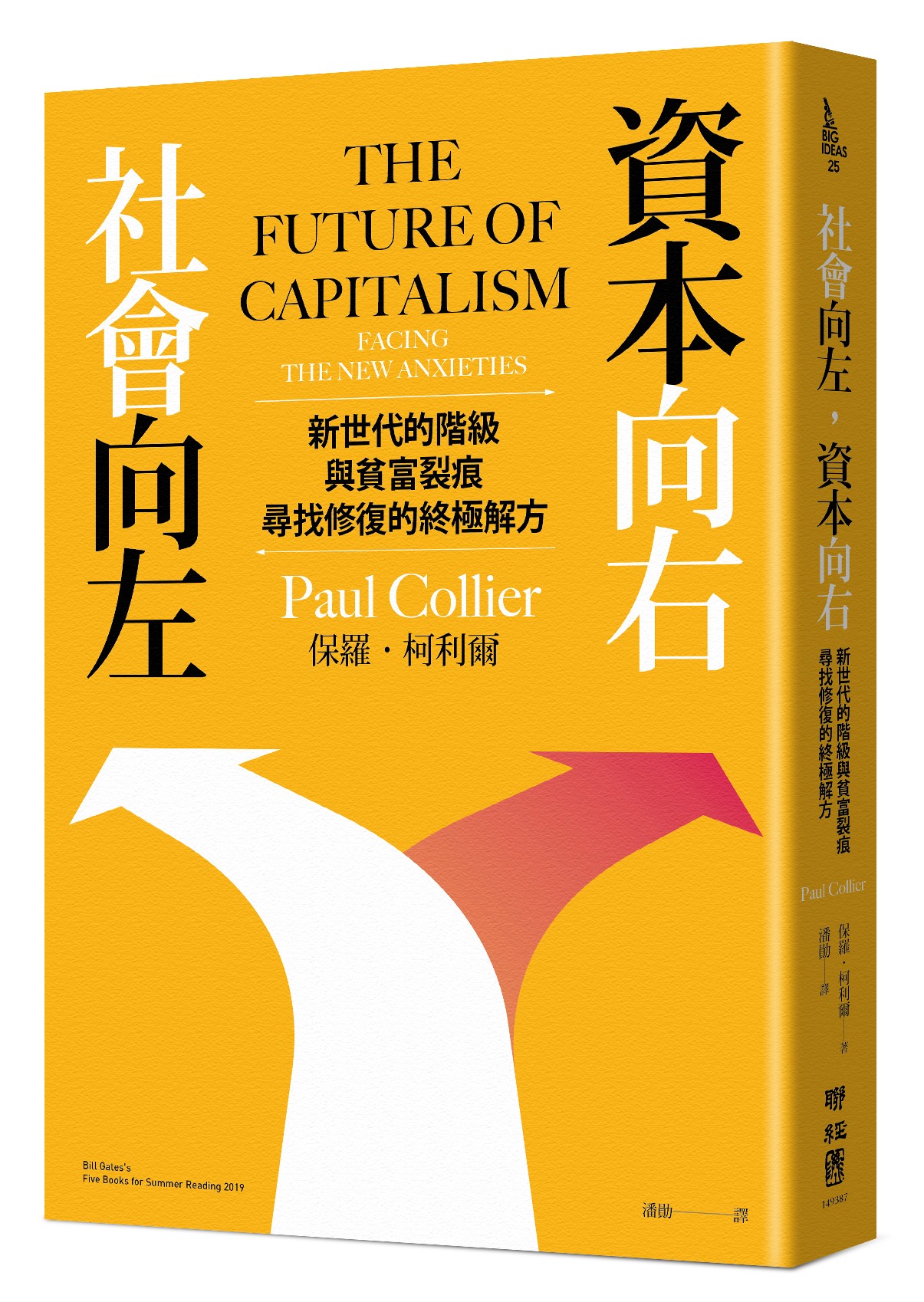
第七章 地理分裂
勃興的大都會,破產的地方城市
倫敦、紐約、東京、巴黎、米蘭。環顧西方世界,這些大都會一直超前全國其他地方,而且這條加寬中的分裂赫然在目,不管我們以收入、就業成長或房價來衡量,都是如此。這是相形晚近的事,始自大約一九八○年;在此以前,區域之間收入差異本來一直在縮小。美國堪稱經典,長達一個世紀,城鄉貧富差距一直以每年近百分之二的速率縮小。然而自一九八○年以來,除了發現都會區大為成功以外,還瞧見很多省會城市受苦於經濟突然下跌。經合組織的新研究發現,在高收入國家,過去二十年間首善地區與其他大部分地方,兩者間的生產力鴻溝擴大了六成。英國也是典型:自一九七七年以來,人口每年都由北往南漂移,而且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一九九七年,英國省分地區的總經濟,要比倫敦大四.三倍;到了二○一五年,已變成三.三倍。
這種狀況在新的政治分裂中上演得淋漓盡致。各省的怨恨不滿,大都會則以蔑視又自信來迎擊。美國有個常用蔑視詞「飛機經過不停的城市」,最近才被《金融時報》政論家甘尼許(Janan Ganesh)引用的「跟死屍銬在一塊」所取代。由這些詞彙,看得到同理心嗎?互惠責任感到哪去了?那些善良人性遭粗暴拋棄,隨著以往團結都會與地方各省的共同認同淪喪後,一起蒸發消失。都會區投票強烈抵抗一些敵對攻勢如川普、英國脫歐、勒朋及「五星樂團」(Five Star),而破敗的城市卻覺得它們很叫人心動。
那麼,究竟是什麼經濟力量在擴大這道裂隙,而我們可以怎麼做來因應?
驅動這種新分歧的是什麼?
好些力量導致這種都會與各省的分歧,而奠基的是兩種簡單關係,它們回溯到工業革命。第一種是生產力與專精化的關係,俗話就是「邊做邊學」。人們專門做較少的項目,更能發展出較深的技術;另種關係介於生產力及規模之間,俗話就是「規模經濟」。
為了利用規模及專精,人們必須群聚到都市來。對一家營運達規模的公司,必須有一大群工人、一大群顧客,設址在其他類似公司附近。隨著工人專精化,他們必須在其他擁有互補專精技術的人附近工作。城市提供地利之便,讓這一切能連結起來。但聯絡方便的城市必須大額投資於地鐵、道路、多層式大樓、機場及鐵路樞紐。直至一九八○年代,只有歐洲及北美的城市負擔得起。
由這種連結簡便衍生的生產力,報酬十分驚人,很多城市發展出某些特殊產業的企業聚落,讓它們能橫行全球。我的故鄉雪菲爾德就建立如此星羅棋布的專業鋼鐵廠,以及相應極專業的勞動大軍。到了大約一九八○年,一名身處這種城市的標準工人,相形世上其他沒有產業聚落的地區工人,其生產力要大很多很多。因為收入往往對應於生產力,城裡人的富裕程度也大得多。
大約自一九八○年起,這種情勢遭兩個同時發生但有別的過程打斷:知識大爆炸及全球化。知識爆炸讓專精及都市化之間的老關係力量暴增,導致最大城市成長壯觀。全球化開啟新契機,可以利用規模經濟的利益,但也讓既成聚落接觸到新的競爭,有時導致舊聚落的式微。
知識革命及大都會的興起
自一九八○年代起,知識經濟以指數速率膨脹。這種現象的動力,部分來自大學進行的基礎研究前所未見地成長,部分則是大企業大舉進行互補式的應用研究。駕馭物質造福人類的潛力,只受限於物理的基本定律。將這個過程以爬山為比喻,我們現只在山腳而已,原因在想掌握物質世界是極其複雜的事。新發現一而再再而三,我們涉險進入這個複雜世界,而逐步革新生產力。我們人類的能耐有限,要想駕馭複雜,唯一之道便是讓才智最高的人變得更為專精。最後一個可以認真宣稱自己通曉所有知識的人,大約在十五世紀就滅絕了。今天,人類中最聰明的人對某個窄小領域浸淫極深,已抵達學域的邊界,相應的則是距離其他別的學域疆界愈來愈遠。這一點不僅對學術研究是如此,有商業價值的技術亦然。舉個例子,法律變得更複雜了,以至於法學專業已界定得更精細。大學擴張,衍生出來的不僅是學術研究,還有學養能駕馭那些技術的畢業生。
但是專精與都市的基本關係依然適用。極端專業,只有在不同專家彼此靠得很近時,才有生產力。所以,愈是專精,就需要能互補的專家結合成更大聚落,還要有管道,通往相應人數更大的潛在客戶。在倫敦,一名專精的律師與擁有其他專精的同儕很近,距離需要其專業的客戶還有法院也很近。同一位律師若執業於小鎮,那麼一年大多數時間會投閒置散。
專業群聚,要靠大都會提供絕佳的聯繫力。倫敦及其衛星城市囊括英國兩大國際機場;首都還有歐洲之星高鐵直入城內,而聯通巴黎及布魯塞爾。倫敦還是全英鐵路幹道的交叉點,大多數高速公路也匯聚於此。倫敦有地鐵,在中倫敦(Central London),尋常工人可以在四十五分鐘內,與其他二百五十萬工人的任何一位聯繫碰頭。倫敦另是政府所在地,所以仰賴公共政策近水樓台的任何活動,最好就設在當地。
國際商業障礙被除掉,讓高專精民眾群聚的益處更為升級,潛在市場由全國擴大到全球。服務業群聚於倫敦,以往的主要市場是英國全國,目前則是全世界。所以,市場目前力挺律師們更為專精,他們的法律技巧及生產力相應地也提升,結果便是他們的收入很可觀。
接下來,廣大收入極高的人口創造出一個服務業市場來娛樂自己。地點不遠很重要:餐廳、戲院、精品店擠進大都會,以滿足錢很多但時間很少的人之一時衝動。這種奢華叢集進一步吸引全球富人湧入。倫敦、紐約、巴黎都住有億萬富豪,他們在別地發大財,卻樂於來大都會享樂花錢。
你瞧——勃興的大都會!
全球化革命及各省城市的沒落
上述描寫的光景,跟雪菲爾德、底特律或里爾市的際遇無關。我記得一九六○年有位訪客來雪菲爾德時說:「哇!這個城市真富庶!」到了一九九○年,已經沒人會那麼說了。
城市群聚世界級的企業,比如一九六○年代的雪菲爾德,對新競爭者便具有很大的優勢,但並非牢不可破。雪菲爾德就產鋼而言並沒天然優勢,能吸引企業聚集到該市的特點,在它有湍急的河流,可以推動滾輪;到了二十世紀,它唯一優勢便是已駐留當地的企業及技術工。各公司留下來的原因,在於別的公司也在當地。勞工大軍有生產力,但生產力反映在工資上,所以企業獲利並非特別高。
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個崛起中的經濟體南韓,正興建新的煉鋼產業。等到南韓建立起自己的產業聚落,它還有一個不同的優勢:勞動力便宜得多。到了一九八○年,在南韓煉鋼比起在雪菲爾德,已變得較有利可圖,因此南韓企業在世界鋼鐵市場中,開始贏過雪菲爾德。雪菲爾德煉鋼業開始萎縮,而南韓的開始擴張。隨著雪菲爾德的企業聚落萎縮,很多公司交疊在鄰近地區而產出、稱為「聚集經濟」的利潤,便告減少,結果便是成本上升。南韓群聚膨脹時,它的成本下降,後果像爆炸一樣:最早在喬叟《坎特伯里故事集》便著稱的雪菲爾德的煉鋼業,以驚人速度崩塌。煉鋼業技術工,其父執輩也是技術工,發現自己失業了,沒希望再找著要他們技術的工作。這種協作震撼下的人類悲劇,值得矚目,透過一部電影《一路到底:脫線舞男》(The Full Monty)而銘記下來。電影辛酸自嘲的幽默,襯映整起不幸的背景,傳神地捕捉到所發生的事。雪菲爾德是我的故鄉,我感覺這起經驗好苦澀,然而它在很多一度繁榮的城市重複上演,比如斯托克(Stoke),當地由威治伍德(Josiah Wedgwood)帶頭創立的陶瓷業聚落也內塌了。這一些,再加上其他案例,比起美國底特律市一九八○年代以來的遭遇,都算小巫見大巫。
那些城市有復甦嗎?右派意識形態信徒相信,只要政府不干涉,市場力量就會解決問題。很不幸,這只是意識形態的信仰而已。想取得真知灼見,我們得求教於專家。
市場對聚落的崩潰有所回應,但不是汰舊換新;相反地,一開始是住商地產的價格大跌。屋主的淨資產變負數,想搬去勃興的城市有困難,原因在房價遠貴得多。商用地產下跌,的確會吸引某些活動,但那些只是組成全國經濟下半截的東西:服務當地的大賣場、生產力低落而只有廠址非常便宜才能苟活的製造業,還有靠著地租便宜低薪零工維持的電話服務中心。城市充斥這些活動的時候,房地產價格及工資會稍有起色,但城市已走入死路。那些商業活動技術含金量低,因此勞動人口不再參與複雜的專精化,而不斷提升生產力。大都會裡超級巨星般的企業依然在科技的前端,因此都會人口受益於收入上升,但不管是科技或收入,都沒有涓流到凋敝的城市。舉個例子,美國新數據顯示,高薪、高科技工人變得愈來愈強勢集中到最大的聚落。講得更炫一些好了,科技由領袖擴散給後段班的速率已經減緩了。
破敗城市現淪落到那種地步,不能再用「你瞧」這個熱情的感嘆詞了。
解決這種新分歧
前述分析有助於解釋:何以跨越所有先進經濟體,大都會都在高歌猛進,而很多省分城市受苦於黯然衰退。對此現象,我們能做什麼?聽來很熟悉的「解方」數目不少,意識形態信徒攪一攪就丟出一堆。話雖如此,它們只引領我們走到過度自信的死胡同。
就解決這種新分歧,民粹人士最瀟灑寫意。他們建議,既然分歧是新出現的,那麼讓時光倒流回它發生之前就行。他們用以辦到這一點的政策,便是保護主義,倒轉市場全球化。讀者冷笑這種回應法之前,我們應有所體認,它倒不是蠢到不驗自明。假如在某些重要方面,很多人認為過去確實優於現在,那麼採取策略恢復過往經濟,似乎既可行又安全。同一批人已學懂,不可相信樂天的保證,說什麼假如他們接受進一步的變化,到最後一切會變得更好。
只是,時光倒流的策略注定要失敗。關鍵原因在新興市場經濟體,比如南韓,已建立起新的世界級聚落,它們可沒半點興趣回到過去。全球化讓它們脫貧的程度,實為成就空前。假如南韓繼續支配鋼鐵業,不管英國用多大力氣在保護主義,都無法恢復雪菲爾德在世界市場的地位。那樣做充其量把英國鋼鐵市場交給雪菲爾德,但市場不夠大,無法恢復雪菲爾德一度擁有的高生產力。而且在過程中,英國鋼鐵成本升高,將損害需要鋼鐵的一切產業。
保護主義無法讓雪菲爾德復元,一大批限制性質的政策倒有可能逆轉倫敦的繁榮。誠如雪菲爾德煉鋼聚落經證實會遭別地方異軍突起所打敗,倫敦的金融聚落也可能被打扁。倫敦花俏的繁榮,對英國其他地區胼手胝足的努力,可謂一大侮辱,因此打扁它,或許英國某些地區還會歡心慶幸。只是這麼做,一樣是愚蠢的策略。一處大都會如倫敦,甚至比一塊油田還來得好——大都會永遠不會枯竭。這隻生金蛋的鵝或許叫人不高興,但比起扭斷牠的脖子,還有更好的策略。不幸的是:本書寫作期間,英國採行脫歐戰略,有可能導致金融部門協調一致,轉到歐洲其他城市;英國好像鐵了心,要把金鵝宰了。
何不改採揀金蛋的手法?換種講法,何不動用向大都會徵稅而取得的歲入,來重振各地城市?
碰到這種建議,每個意識形態信徒都可以大噴口水。右派會鐵口直斷說,加稅將引發遏制效應,同時嘟嚷著,反對把各省轉變成龐大的「福利街」(Benefit Street),充斥想不勞而獲的人,「跟死屍銬在一塊」。左派就熱衷於抽倫敦的稅一事會過了頭,無意間引發有戒心的公司大出走,導致聚集經濟解體。
左右兩派都有足夠的真相在自己那一邊,能說服追隨者,但真相的量又不足以稱為真理。右派感受到的真相是:轉變各省城市為福利街,不能當成目標。幸福感端賴尊嚴及使命,絕不只是你能花多少錢來消費。用公共福利來貼補沒有收穫感的工作,這種策略,並不能代替創造出需要技術的職缺,而工人能為自己熟練於該技術而自豪。所以,目標在有生產力的工作,不是公帑補助沒生產力工作的收入。左派感受到的真相是:那些吮吸高薪大都會專業酬勞的人,有幾個臭錢就覺得自己了不起,道德上叫人火大。這些人認為他們自食其力,而我打算指出他們並不是。
我提議的策略自然會分裂成兩半:一半是向大都會課稅,另一半是振興地方城市。每一半仰賴不同的分析與論述。
課稅及都會:「我們自食其力」,真的嗎?
課稅應該遵守道德及效率。道德在兩方面很重要,第一是道德的本質,再來是課稅若不符道德,會面臨抗拒及逃稅。效率重要的原因,在稅捐會塞進價格裡頭,例如消費者購買產品付的錢,就會高於生產者賺到的錢。如此的稅捐塞子會扭曲資源的分配,所以傷害了效率。
左派、右派意識形態認為,它們知道課稅已經極化及毒害了我們的政治,稍微動用實用主義,就能讓我們頭腦鬆綁:明智的新稅,可以就道德及效率兩標準上,擊敗現有稅制。
一項稅捐的道德基礎,就稅制而言,可能比效率更重要。稅務行政極其仰賴自願繳稅。要分析道德立論,標準的哲學方法便是務實析理。雖說務實析理是課稅政策的重心,但它不屬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系統。結果便是經濟學家大致忽略課稅的道德面向。他們出任財政部顧問時,經常建議開徵破壞承諾的稅,原因在他們認為那些承諾真是愚蠢(他們的判斷很可能沒錯)。的確,經濟學家顯然在想,他們只消考量過收入不均,就已解決道德課題;而收入不均,是透過標準的功利派計算方式來分析的。誠如海德特所見,大多數人認為公平(fairness)的重點在「按比例」(proportionality)及「賞罰」(desert),而非平等。然而它們遭到忽視。賞罰?算了吧,若是懶人的錢比勤勞工作的人少,那麼轉移金錢還是能提升「功利」。應不應得?算了吧:假如有人努力存退休金,退休時錢比一生花在海灘度假的人多,錢轉給後者還是提升「功利」。責任?算了吧:此時你應該全部都懂了。功利派經濟學家應留心,有些金錢轉移會有抑制效應,因此沒有效率,但他們不會承認那麼做是不合道德的。這種瞠目無視更廣大道德考量,其實是更大現象的例子,也就是「西高工富發」。
一旦我們認定,賞罰這個命題在稅務設計很是重要,那麼它對聚集經濟所得的利益,就有強大影響。最早瞧出這一點的人,是十九世紀美國記者兼政治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他闡述完自己的思想後,便引起轟動。
亨利.喬治的宏大思想
喬治提出道德論據,支持對聚集經濟衍生的利潤進行差別課稅。他瞧出何以利潤因道德而有差別,歸結出合宜的政策,是向都市土地徵收加值稅。
讀者可以提出一系列問題而領略他的洞見。先由「誰由聚集經濟獲利?」開始。為了理解通透,眾所公認工業革命是這樣的:一開始,大家都是農夫。工業發軔於新城市,人們搬進來,到工廠工作。工廠的聚落成長,人們變得比務農時更有生產力,「聚集而增益」(gains of agglomeration)指的,便是這種額外的生產力。額外生產力反映在工資,原因是企業彼此競逐工人。但是,為了在工廠工作,人們必須住到附近,因此得向擁有土地、城市在土地上頭形成的任何人,租借土地。所以,搬去城市取得的利益,便是較高的工資減去地租(為了讓事態單純,我們假設:除了工資比他們原先務農來得高,人們在都市的生活與鄉間並無不同)。只要務農及工業間的生產力差異,要比地租來得高,更多人願意搬到城裡。但隨著他們那麼做,地租不斷被催高,過程持續到地租高到吃光整個生產力差異為止。到此時節,人們再沒誘因想搬過來;用經濟學術語來形容的話,就是我們達到平衡。但更興奮的是:我們歸結出強勁的一句話,而回答我們的問題:「聚集經濟的利益全以地租而歸給地主。」位居政治光譜右端的人或許會心生不安,但請放心,這項分析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喬治並非社會主義者。但他是精明的經濟學家;他死後多年,兩位經濟學者證實他的結論為定理。他們很得體地把它稱為「亨利.喬治定理」(Henry George Theorem)。
喬治接下來提出第二個問題,那在傳統經濟學框架裡是無法理解的,「地主夠資格取得那些利益嗎?」雖說經濟學家無法領會,但其他人倒是能懂。我們倒不需要什麼定理就能回答問題:我們要的只是務實析理。要了解某人是否夠格取得一筆收入,我們得回溯,找到導致他們取得收入的行動。只是,當我們由聚集經濟回溯利益時,會發現衍生利益的行動,每個在城裡工作的人都有參與;整體生產力的上升,人人都有貢獻。由聚集經濟而產出的利益,是因為大批大批的人群互動而來的,因此是集體成就,而造福大家,經濟學家把這件事稱為公共財。那麼,地主在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他們做的一切,很可能只是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的確,他們消磨時光的方式,很可能就是那樣。他們收取到那筆收入,原因只在於擁有土地,而人們湊巧群聚於那裡罷了。他們的活動,並沒參與聚集而衍生利益。用經濟學叫人困惑的術語,它被歸類為「經濟租」(economic rent)。
重點在於:按理性的道德標準,地主們沒那麼夠資格取得自己土地升值而衍生的利益,因為利益遠大於他們為土地付出的心血(假使有的話),也非反映他們經由儲蓄而累積的資本收益。這倒不是說他們半點資格也沒有。身為土地的合法擁有人,他們有權依財產權而取得聚集經濟而生的利益。但這一點,與所有城市勞工集體有權取得那些利益相衝突了;集體有權是依據賞罰。理性標準發生這樣衝突的時候,實用主義會叫我們妥協,而非陷入固執己見。課稅介入之時機,正在於此。假設社會同意,向一些賞罰與有權應得相符的人,課徵一定稅率,比如自耕農,他生產的農作物,既是他工作又是他擁有那塊農地的成果。假如公認稅率在百分之三十好了,那麼要決定因土地升值而取得的收入,該徵多高稅率,而反映聚集經濟所生的利益,我們應該把稅率訂在比百分之三十高得多。這可以反映這件事:地主對這種收入的主張權,力道遠弱於自耕農對自己收入的主張權。此外,唯有藉著向聚集經濟的增益課稅,使用這些稅款來造福整個城市,那麼造出那種增益的勞動人口,才能收到部分利益——而按上述分析,是他們應得的。
亨利.喬治的點子很早便用上務實析理,立足於區別出租金與其他形式收入之間的賞罰。他仔細分別出土地升值而生的租金,以及資本所得,而他認為後者理直氣壯:他的主張既非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民粹。
喬治的觀點離經叛道嗎?相反地,他的道德良知轟如雷鳴,《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變成整個十九世紀美國最暢銷的一本書。
作者為英國經濟學家,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政府學院經濟與公共政策教授。曾於哈佛大學與巴黎政治學院擔任教職,著有《The Bottom Billion》、《The Plundered Planet》、《Exodus》等書,並與Alexander Betts合著《Refuge》。2014年受策封為爵士,並獲得英國國家學術院的院長勳章;2017年獲選英國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
長期致力於研究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主題涵蓋農村貧窮、都市化、民主制度的問題,以及外國援助的影響。也曾探討全球暖化等環境議題,試圖於否認暖化現象與反對一切破壞兩個極端之間,找出中間之道。曾獲美國著名學術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評選為全球頂尖思想家,現為反貧困學術委員會(Academics Stand Against Poverty)成員。
書名:《社會向左,資本向右》
作者:保羅‧柯利爾(Paul Collier)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