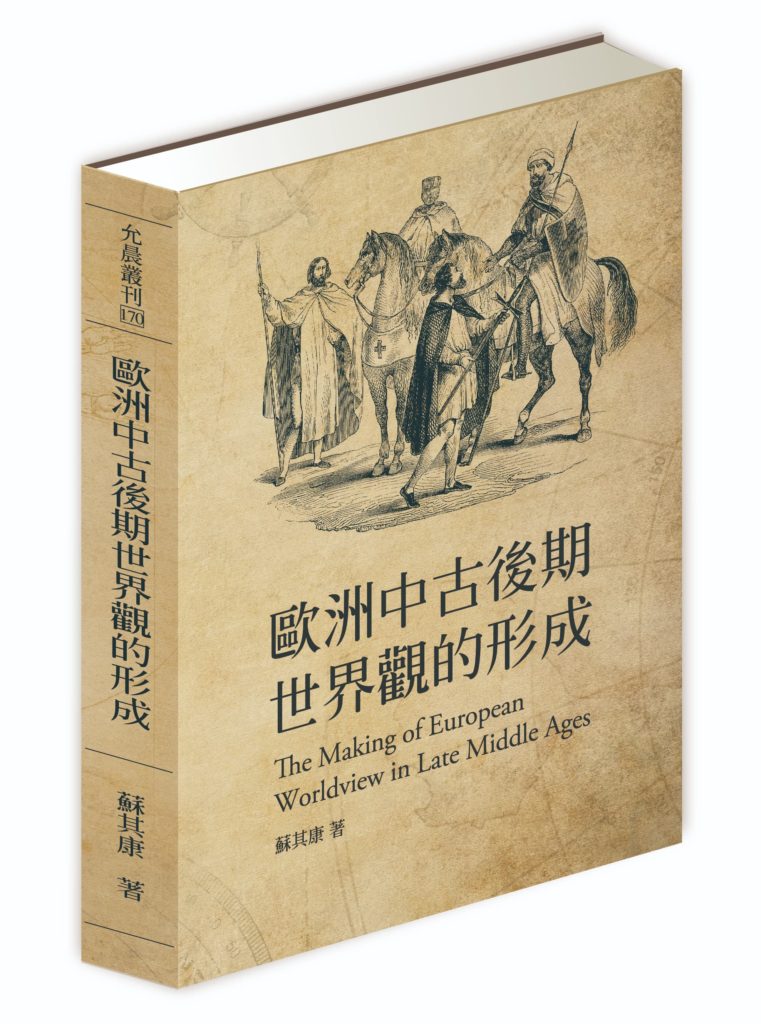
第三章 商貿現實的需要
前面幾個方濟各會或道明會傳教士的活動主要動機是在傳教和教化民風而兼及外交關係的溝通開發,兩個層級都屬於社團和制度面的活動,大體上是靈性面居多的建立,修道人的言行和說服力,不以個人利益為主,而能彰明他們注重清貧生活和懺悔、簡樸和謙虛,但貧窮的生活不是目的,卻基本上規範了方濟各和他的追隨者連成一陣線,直接效仿當初傳播福音的基督(Cook and Herzman, 244),以出世之姿、清貧之樂在異地傳教。雖然方濟各會的會眾發展迅速,影響層面也廣,畢竟對俗世的民眾來說,他們所追求的大多是物質的滿足,但個人的成就經常希冀可以留存給自己的後人,形成資本財富的累積,因此,在個人和家族方面的想法,則另有不同層次的經濟和營生的活動,其中心旨趣恰好和方濟各會的理念相反,但他們的開拓策略卻緊密步塵方濟各會傳教士之後,在遠赴東方一途,特別是前往中國的開拓,最著名的一員無疑是馬可孛羅。其人出身自商人世家,父執輩已是經商有成,在十三世紀初第四次十字軍進攻君士坦丁堡後便遷徙到克里米亞東南端黑海旁的重要港口索底亞(Soldaia,即今天的蘇達克 Sudak)市作為商貿基地。然而在1240年代黑海的北岸已為蒙古人所掌控,操拉丁語的商人已開始在這個地域活躍而同時快速地熟習不同的政治和商貿規矩。到了1261年,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勢力再次潰敗時,馬可孛羅的父親及其弟弟已轉移陣地,前往威尼斯落籍並計劃向東面蒙古人操控的地域發展。因為接受了使用拉丁語商人的建議轉向到伏爾加河(Volga River)欽察汗國(又稱金帳汗國 Golden Horde)的大汗成吉思汗的孫子別兒哥(Berke1257-1267在位)那邊建立貿易關係,不久還成為大汗的商業代理人且獲得豐厚的商業利益(Jacoby196)。有了這樣先代的經驗和可能傳承的人脈,馬可孛羅(1254-1324)日後的亞洲行,特別是1271至1295之間在中國的遊歷(或應稱為商業旅行),可以直達忽必烈的朝廷,雖然他停留在中國17年之久超過一般商業活動的時程,但對深入認識居留地的風土民情,擁有絕對的發言權,也就是他遊記所載,除了別有所圖的巧飾之詞和不經意誤導的可能不算,其所介紹和臚列的資料應具相當參考價值。馬可孛羅之所以順利成行,是因為父執輩所建立的經商人脈,一方面是拜占庭所掌控的君士坦丁商業重鎮已地位不保,另方面也是十三世紀時蒙古大汗對與西方貿易發生興趣,經常以雙倍的價格換取西方貴重奢侈貨物,增添商業投資的誘因,尤其是對馬可孛羅的叔伯父親而言(Jacoby196)。因此可以說,在政治上,君士坦丁堡與黑海北岸之間的軍事和政權遞演影響到地中海地區貿易發展的大方向,另方面,蒙古統治者的偏好也改變了商人和區域營運的眼界和逐利的作法,促成了歐洲對蒙古所治理的亞洲,包括最重要的中國腹原的開發,馬可孛羅的父叔因而在1271年八九月間再次離開威尼斯到亞洲遠行經商(Jacoby 197),有了這些奠基的經歷,自是方便日後馬可孛羅的東行,而他也只是地中海眾多商人族群中的一員。活躍的商界此時已嗅到新的契機,也就是把傳統地中海的視域,如同方濟各會的傳教士那樣,向遠東方面延伸和擴張。地理、文化、環境、語言和政治體系的改變,自然也就影響甚至改變思維和處事技巧方式,世界觀隨之有所調適變動,商業誘因成為極大的原動力。十七世紀以後的歐洲,所組成的東印度公司也用類似的做法,只不過成為後起之秀而且加入政治和軍事力量在背後支撐而已。
馬可孛羅的地理和市場知識:《馬可孛羅遊記》
馬可孛羅的遊記經口述由比薩之魯斯蒂車羅(Rustichello de Pisa)用古法文記錄下來,書成時定名為《世界各區域》(Le Divisament dou monde或應作Le Divisement dou monde , 1298),可見這部遊記面世的初期,馬可孛羅和委託書寫人認定這是一部瞭解世界(du monde)各地風貌的作品,然而在馬可孛羅身後不久,佛羅倫斯商人裴哥羅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在1330年代卻把全書素材重編組合而成為一部義大利文商務手冊,並改名稱之為《各國區域與商品度量衡之書》(Libro di divisamenti di paesi e di misure di mercatantie或可簡稱作《各國商業誌》),把商品(mercatantie)的重心勾勒出來。事實上,馬可孛羅書的價值,不只因為與東方和西方的史料大致相符合,奠定其材料的可信度,其中大量的資訊還反映了受過專業訓練和威尼斯商人角度的心性取向的紀錄,尤其是他對市場、商品的期待、價格、甚至轉換成威尼斯的價值、統治者的收益、數量資料、以及高價位貨物的運輸情形(Jacoby 207),這些都構成了一種新的人文地理和商業調查脈絡的圖象,尤其是東方和西方貨物價格的對比和等值的訊息,除了給時人打開眼界之外,還有物質文明和社交文明附加利益建構的作用,再來就是時尚和風氣的無形參考價值。當然,這個義大利商人從東方之旅所帶回來的,完全是同為義大利清規生活的方濟各會傳教士所倡導觀念的強烈反照和對比。歐洲世界的視覺和關注點已進入一個多元五彩繽紛的爭妍鬬麗的局面,在無意間已把某些東方規格和價值納入他們的生活理念之中。世俗化的物慾思維已蓋過傳教士所倡導的克己精神文明。
其實在十一到十三世紀期間義大利的貿易方式已成了可稱作是商業革命,從地中海地帶推進到歐洲北部,構成了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的指標。利用河川航道和沿海航運的方式使貿易和旅遊都較前大為方便,另方面,從義大利所創導的銀行業務技巧,諸如信用、貸款、和匯票等,擴張了貿易資本(DuBruck102),促使大貿易商的出現,譬如1300年至1400年間在佛羅倫斯的梅第奇(Medici)家族,或奧斯堡(Augsburg)的福格(Fuggers)家族,貿易加上財務的操控,使富商巨賈控制了城市和特許的事業,中古的市場遂構成了西方世俗文化和技術的根源(DuBruck 102-103)。雖然此時歐洲大部份的人口居住在鄉村地帶,到了十二世紀時,城市已開始發展,地中海區域因為聯結起歐、亞、非三洲,使日漸增多的商人群體在這些發展中的市鎮,充份利用其彈性的社會、經濟和宗教組織找到立足點,貿易的擴張,使商人找到新的和更形重要的角色,科技的發展使海陸的交通較前大為方便,而貨幣供應的增加更成為頻繁貿易的催化劑。因此,馬可孛羅遊記所載的新穎奇特資料和訊息,自然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特別是商人,他的書成為當時的流行書刊也就自不待言。從父執輩接下各種資源、技巧和衣缽,基本上,馬可孛羅仍然是一個行商的作為,也就是不居留在定點經商,而為了貿易和營利的緣故,需要穿山過嶺和遠涉重洋,因此道路的情況、距離、天氣、各地的民風、交通工具的使用、路上鄉鎮城邦的要求和稅賦、貨品的運送方式、風險和人身安全問題,以及不同地方產品特色和需求、計算和記帳方式,都必須在事前和在途中充分掌握,還有就是應變之道,再來就是溝通時所用的語言或外語的問題,馬可孛羅的遊記都有所觸及,而他對特定地點和城市經濟榮景的敘述,更叫歐洲人大開眼界,在商界中廣為傳閱。其中一個比對的數字就是在十四世紀下半葉時,馬可孛羅的手卷流通共有八十份,而鄂多立克的手卷只有三十六份(Espada201),足見馬可孛羅的商人角度資訊比之廣為普通人尊敬和接納的方濟各會神父鄂多立克的書寫更備受歡迎,或可說對很多人而言更為實用。其實,馬可孛羅遊記初始時是遭到大眾質疑拒斥的,不是因為內容有相當多對歐洲人來說是荒誕不經或怪異不符想像的事,而是因為他對蒙古人有好一些讚許的言辭,而蒙古人對歐洲人原不友善,並且時人覺得基督徒是人類文明演化中進入更為完善的階段,遂覺得遊記的故事顯得難以置信。這一點又牽涉到以歐洲為中心的自視問題,即基本上那時的歐洲人認為他們比「野蠻」的蒙古人有更高級的文明基礎和發展,基督教文化比其他宗教文化更適合人類社會的發展,其次,他們不覺得元朝的勢力可以產生中國文化的花果。殊不知蒙古人只是在中國建立統治階層的元朝,中國文化並不是在蒙古人手中創立和發展,十四世紀初傳到歐洲璀璨的中國文化事蹟也不是蒙古人的功勞,質疑派的歐洲人可說是弄錯了對象,也過於投射出敵我的心理因素。
寓言化的地理學
整體而言,中古時代歐洲對亞洲和印度的見解和想法,經常把現實面從寓言角度去詮釋,過分仰賴當時歐洲層級和階級性的社會結構,加上文化上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偏重希臘以及伊斯蘭文化遺產的思路,難以使當時的人們正確地掌握印度和東方的複雜面貌及其意義所在(Espada 204)。但無論是鄂多立克、柯文諾山之約翰或馬可孛羅等人的書寫,都被粗略地歸類為「東印度群島的描述」(descriptions of the Indies),也就是西方文化長期對東方的理論構思的結果,從印度洋周圍的波斯直到中國的地理和地緣認知的抽象層次(Espada 204)。故此,「印度群島」不只是今天亞洲次大陸的印度和鄰近國家,還包括了印度以外從蒙古大草原以南,含中國,直到東非,也就是前面《旅遊誌》所稱的「下印度」(Lower India)之地,這種籠統的處理方式,明顯反映出當時知識界的不足和所知有限的缺失,卻又不願接受缺席裁判的結果,因而這個指標的述辭,無疑成了知性上和精神上的外在刺激,誘發對現實的思維和人類歷史原始的探索,隱約間背後存有基督教聖經對人類發展和移徙概念的影子,形成歐洲對遠方國度社會應用面認識的原則,更甚於對真正具體資訊和數據的使用和理解,也就是在他們的知識界裏賦予偏遠地域一個政治層面的輪廓。神職界如方濟各會傳教士們對廣大世界的學問所以獲得推廣,其實是因為這些學問可以增進他們社會對靈修和政治上的理解,而不是基於利他主義之目的,也同時方便了人們利用那些知識主張政治和社群上的先例,故此,對東印度群島這種偏遠區域知識的寓意價值加碼,有效地形塑成為中古時代對世界的構思和概念化的做法(Espada 205)。這種取向可由方濟各會的會祖在答問中證實。曾經有門人弟子問聖方濟各,在修會裏可否讓有學問的會士花時間發揚和研究學問。聖方濟各的回應則為只有對傳教事業和實行基督的榜樣有幫助時始能為之,會士應以發揚簡樸和謙遜生活和傳道為第一要務(Cook and Hergman 243)。就這個角度而言,傳教士的遊記所登錄和商人如馬可孛羅所載錄,表面上有些敘述和紀錄會相同,但背後的描劃動機和角度則是兩種不一樣的功利主義型態,一種是為了傳教的靈修目的,含有某種特殊的意識型態的動機,而另一種則是為了經濟和政治利益而書寫。然而後者到亞洲地區的行商旅遊紀錄原來就非常稀少,或者是十九不存,少部份的資料是從傳教士所接觸到商人之中間接爬梳而來,故此馬可孛羅代表了十三世紀活躍於地中海的商人階段,他的遊記雖然說不上是空前絕後,卻是純然從經濟和政治利益角度所描繪的第一手實用資料,對當時人們想像和見解的異質化圖像,具極大的震撼和驚奇,在傳教士對中東和遠東的地緣經濟政治的檔案之外,馬可孛羅的遊記幾乎是另類透視的唯一紀錄,難怪佛羅倫斯商人斐哥羅蒂亟願以之做底本,直接了當的編成一部商人寶典的《各國商業誌》。馬可孛羅遊記之特別吸引人,不只因為他交待了元朝中國南方和北方兩地的物產和人文經濟地理情形,更因為他去程採用陸路而回程改採水路,所以歸途路經南中國海而抵印度洋,再由荷姆斯港靠岸,此外,又加上他在忽必烈朝中曾隨同出使東南亞,因此他的旅途囊括了印度和南海諸島,也就是那個年代的東印度群島大區域的概念,無論作為比對、修訂、挑戰和刺激時人對東方—所謂東印度群島的基本概念或重新思考對世界的認識,馬可孛羅遊記無疑提供了知識上重大的激素和貢獻,對地中海的商人來說,水路交通及其有關問題,自然是熟識又能吸引他們的興趣,另方面,東亞和東南亞諸島的見聞資訊,補足了那時外國市場和地理輿圖的知識,而且所有的紀錄文字都不是當時菁英分子所使用的拉丁文(教會官方的語言),在某個層次來說,馬可孛羅商貿的文本已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世俗化社會所大感興趣觀看世界的觸覺和角度。
傳教士和商人
最有趣的現象就是從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托缽僧傳教士,亦即是方濟各會和道明會的僧侶,他們與商人的關係以及處事型態非常接近,甚至有學者稱呼這兩個修會的會士為「教會的商人」。然而的確在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初托缽僧和商人這兩組人馬同時在社會中浮現佔上顯著的地位,尤其是在地中海區域的城市和市鎮中心點,這兩種人經常互踩足跡,生活方式和行蹤都有所重疊和交叉。中古的商人經常要面對高利貸和生意上道德的作為而教會則是反對高利貸的,因此僧侶和商人的互動又可從如下的方式窺見一斑:托缽僧傳教士給商人靈修和道德上的指引,有時還給予商務交易上的幫助,商人在另一方面則給予修道院設立、擴充和裝潢上財物的資助,好能替他們的財富合法化並獲取永恆的救贖。十三世紀托缽僧修會的奠立剛好和地中海地區城鎮的擴張同時配合,至於商人經商手法有關的高利貸和道德行為,不易見容於當時,在城市裏,商人經常被教會和衛道之士所批評,從十三到十五世紀教會名人往往在宣教教諭中指責商人不誠實和放高利貸,並在著述中直斥其非(DuBruck 100-101,105-106),此一大環境的氣氛迫使商人們願意支持地方宗教機構的藝術品和建築物,或捐款以表明他們的宗教情操(Chubb and Kelley 154),也因此,地中海一帶商人的興起和托缽僧人的擴增也有連帶關係,地中海地區佔了連貫歐、亞、非三洲的地利,其中貨物的交換流轉,也促成了意見的交換流傳(Chubb and Kelley 153)。在這個脈絡裏,商人積極參與公民權利的事務,也催化教育機構(包括大學)在城鎮重點的出現、土語方言的大量使用、商業上派上用場的數學和基本識字率,這幾個文化項目在商人聚居的城市要比少有商人的鄉村地方來得明顯,而商人在這些基礎教育的訓練上又多靠托缽僧人給他們傳道授業(Chubb and Kelley 156),形成某種共生的關係。商人的活動在反諷中同時帶動托缽僧人的動能,兩個看似非常不一的階層,在中古後期可說成了關係密切,而且相當程度地共同促進中古歐洲某些文化面向的發展和成長,對城鎮的凝聚更功不可沒。單以商人捐獻的修道院建物而言,許多中古城市之標的物或著名的特景就是落座在其地的修道院(Chubb and Kelley 160)之中,神職階級和世俗階級構成了共生共利的現象。其實這兩個階級的旅人對知識體系最大的貢獻要算是地理學和尚未開發的民族誌。在這些人的遊記還沒有面世之前,歐洲所瞭解的地球僅有三大洲和地中海文明古早傳下來的傳統,理論和幻想都有,構成他們的宇宙和世界的心象,然而這些東遊傳教士和馬可孛羅家族所親身經歷的遊歷口述和載錄,不只是哲理的求證,或補遺《聖經》對東方的描述,也是真實土地、人物、風俗習慣、天候、河川水域、甚至沙漠和城市建築的細部登載,如果從前的理論地理資料對旅客和朝聖者來說沒有多大作用,這些親歷其境的史地資訊和故事,縱然有部份是歐洲人難以理解,視為怪異的奇譚,但奧秘神奇的印度洋東岸,包括南海諸島和遠東中國的情景,在十三世紀之後經由行商的炫麗記述,終於讓躍躍欲試的商人階級有更正確的資料和指南,不以犧牲性命做底線,而以增加財富逐利和拓寬見聞,順便探究奇妙的他方做出發點,一舉數得,歐洲於是從地中海開始,在蒙古人撤退之後,大幅度的動了起來,而且填補了某些先前知識界不足之處,包括了民族的歷史。
作者為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中山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歷任中山外文系系主任、圖書館館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院長,復接掌文藻外語學院完成升格為文藻外語大學,先後續任靜宜大學特聘教授及高雄醫學大學講座教授。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古與文藝復興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擔任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臺灣西洋、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會理事長、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諮議委員、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顧問等職。專書著作有《西域史地釋名》、《文學、宗教、性別和民族:中古時代的英國、中東、中國》、《歐洲傳奇文學風貌》,《情義與愛情─亞瑟王朝的傳奇》(編印中)等。此外編書多種,西書編輯則包括Moder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Revisited,Emotions in Literature,Perceiving Pow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2 vols.),並譯註全本之《亞瑟王之死》(上下兩冊)等作。
書名:《歐洲中古後期世界觀的形成》
作者:蘇其康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1年5月
讀冊|博客來|金石堂|誠品
- 【書摘】《歷史的快門》 - 2023 年 12 月 28 日
- 【書摘】《流光.散策》 - 2023 年 8 月 17 日
- 【書摘】《茶室女人心──萬華紅燈區的故事》 - 2023 年 6 月 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