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葉啟政(台灣大學社會系退休教授)
訪問者:
晏山農(「思想坦克」總編輯)
鄭凱榕(「思想坦克」副總編輯)
紀錄整理:張詠瑛(台灣大學社會系碩士)
地點:紫藤廬
時間:2018.7.23

王昇原來有意籌辦一份雜誌,以筆戰的方式再次發動另一次對學院的整肅運動,對象即是主張現代化的楊國樞與胡佛,更具體來說,是這些自詡為自由主義的學者們。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最後,讓我再講一個時間上屬於較為後期的事情吧!從1970年代起,楊先生不只在學術上推動有關現代化的研究,而且,也在實際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推動「現代化」,政治民主化即是「現代化」中重要的一環。若說這事一項社會運動的話,,楊先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旗手,貢獻厥偉。
從1974年返國任教以來,我一直就從知識社會學與西方社會發展史的角度對現代化現象有所批評,與楊先生是有著不同的意見的。在我的觀念裡,我不同意現代化有著超越時空經緯的普全性的。毋寧的,它基本上是西方(特指西歐與美國)之歷史─文化優勢擴散所帶來的結果,特別是透過諸如科學理性、技術、政治制度、資本主義等等的形式予以擴散出去的結果,所以背後其實有著特定的意識形態的,可謂是對「西化」一概念予以中性化的一種變形說法,可以、也需要批判的。其實,任何熟悉西方社會理論,特別是批判理論的人,都明白這樣的說法所意指的。
1977年我從政大離開到台大任教,為了回報政大民族社會學系收容我的情義,我一連好幾年一直在政大兼著課,直到他們找到適當的專任人選為止。兼課期間,在政大的交通車上我經常碰到一個先生,這位先生叫劉孚坤,他是哲學系教邏輯的兼任教師(後來,我才知道他在許多大學兼課,也在台大教課)。我們在交通車上聊起天,我不時當他的面批評著現代化的概念。有一次,他找我去位在愛國西路的「自由之家」西餐廳開會,當時主持人就是當年(1970年代)哲學系事件的關鍵人物孫智燊先生(1973─74年擔任台大哲學系主任期間,整肅了十多名教師),我立刻就覺得不對頭,心中有了警戒,但是,在那個肅殺氛圍瀰漫的時代裡,也只能學著虛委應付著。後來,我知道,劉孚坤先生是王昇底下的人。當時,雖然,王昇已經沒有像過去那樣勢力如日中天,深受著蔣經國的「寵愛」,但是其勢力尚未消失。據說,他的官邸夜夜燈火通明著,來往的人車依舊絡繹不絕。
王昇透過劉孚坤先生等人籌劃一連的座談會,原來是有意藉此籌辦一份雜誌,以筆戰的方式再次發動另一次對學院的整肅運動,也就是引發另一次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對象即是主張現代化的楊先生與胡佛先生,更具體來說,是這些自詡為自由主義的學者們。顯然的,他們的消息不夠靈通,不知道我與楊先生的特殊關係,否則,也不會找到我。不過,他們倒蠻清楚的,卻知道蔡錦昌與黃瑞祺是我的學生。後來,有一天,蔡錦昌打電話給我,跟我說:「劉孚坤準備找我和黃瑞祺寫文章,要寫有關現代化的」。我立刻告訴他,這是一個陷阱,目的是要寫文章批現代化,把楊國樞與胡佛等人幹掉。我一再告誡他,也要他通知黃瑞祺,千萬別介入,以免充當打手砲灰。幸好,當時,情形應當是,蔣經國發現王昇行止太過囂張,依舊不知收斂,削了他的勢力,貶到巴拉圭去當大使,這個整肅計畫才沒有實現。
當是時,我立刻把這個消息告訴楊先生,要他轉告胡先生提高警覺。這件事基本就這麼過去。到了1990年代,王昇卸任返台,勢力已失,但是,很諷刺的,他組了一個團體,名稱類似「現代化什麼什麼的」。在1993年左右,於圓山飯店舉辦了一個海峽兩岸的「什麼現代化」研討會,還邀請楊先生參加,他去了。當時,我就對楊先生說:「楊先生,你這個人太與人為善了,您難道沒想想他當年是準備怎麼對付您的嗎?」他沒有回答。這就是楊國樞,一個總是不計前仇,處處與人為善的好人,能幫忙的,他一定幫忙到底。
再說,1990年郝柏村上台擔任行政院長時,當時知識界掀起「反軍人干政」運動,楊先生身為「澄社」社長,有著不得不出面領導的責任,他去參加靜坐了。事後,他就向我埋怨:「啟政啊,我們這一輩,不習慣頭綁布條坐在外面抗議,總覺得很丟臉,很不自在。」說來,他們那一輩的學院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讀書人「潔癖」,他悶不習慣上街頭抗議或靜坐,總認為讀書人只寫寫文章論政就可以了。說來,這是楊先生為人拘謹、「羞澀」的地方,蠻可愛的。
鄭凱榕(以下簡稱鄭):老師我有另一個問題,您說楊老師是外省籍,他或多或少還是有中國情結在,但為什麼他為什麼後來推本土化?
葉:一開始不叫本土化,叫中國化,1990年初此一學術運動開始時,即叫學術的中國化,本土化是後來我跟他建議的,因為這樣的運動適用於所有被西方優勢國家「殖民」的劣勢社會的,要中性一點。
鄭:所以楊老師本來想要推的是中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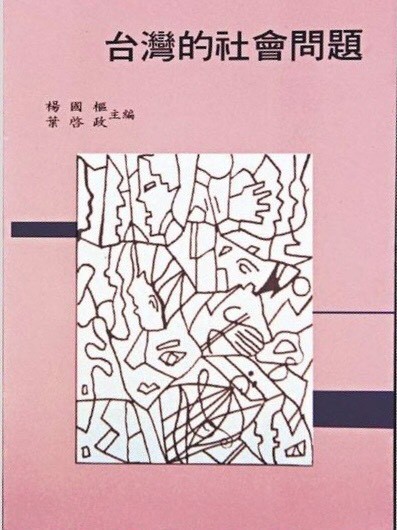
楊國樞與葉啟政合編《台灣的社會問題》一書。圖片來源:博客來
葉:在此,公允地來說,楊先生所以以「中國化」來形容這個學術本土化運動,應當不是基於具強烈國族情感的中國認同意識的,毋寧的,是當時國民黨長期統治下之整個社會的慣性思維模式使然的。我寧願說是具潛意識性質的「自然」反射用語。
晏:我有個想法,80年代初我還沒有進《中國論壇》前就常看這份雜誌,等到1988年底進了《中國論壇》之後,我的感受是:楊國樞、胡佛、文崇一他們這一輩的外省籍自由知識分子,就像舊俄小說家屠格涅夫《父與子》筆下的父輩,溫和、理性但限制大;而子輩是後來更年輕的學者群,力主行動和激進化。
葉:你要這樣講也可以,屠格涅夫時代的舊俄現代化(法國化)是兩代間有不同的見解,但是台灣有另外的因素,就是省籍。看看早期台灣人文社會科學方面之教授群的系譜,絕大多數是外省籍的。當年國民黨把清華和北大一些教授帶來台灣,像沈剛伯、查良鑑等都是。台大從光復,特別是49年以後,就擁有一批國民黨帶來的外省籍教授,基本上,除了法律系以外,人文社會科學的教授都是外省籍為主。再看看中研院的院士,早期人文社會都是外省籍。假若年輕一輩的台籍學者能當選,往往都有他的師承脈絡背景。上一代的外省籍人士有他們的理念與國族認同,這是情感的自然作用,應當尊重,也必須接受,但卻是整體台灣社會的歷史共業,我們只能接受。因此,你如果要為台灣的知識份子畫分父與子兩代,那就必須審視歷史,這個台灣糾結的特殊歷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