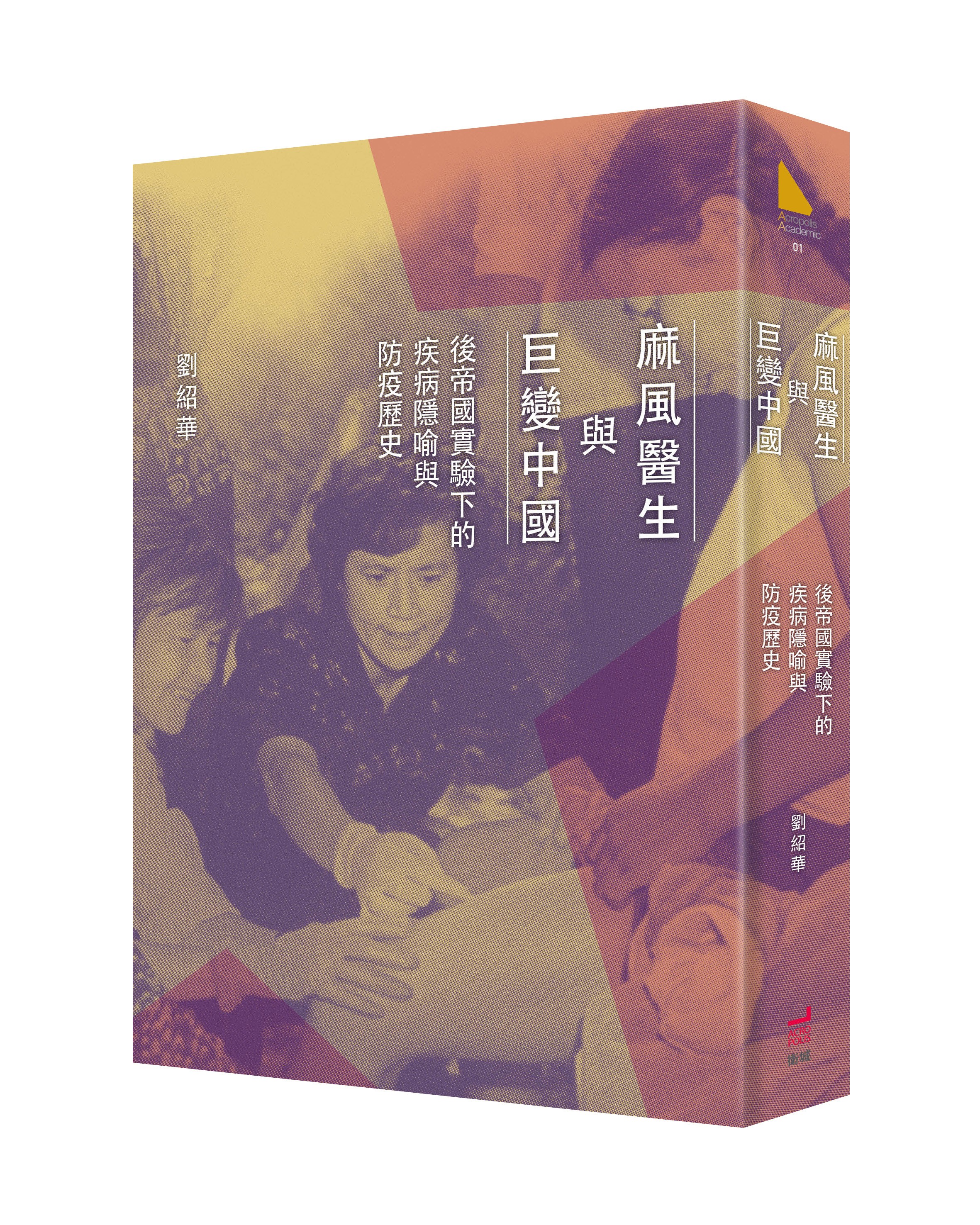
書名:《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
作者:劉紹華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8年10月
後帝國論述下的防疫運動
疾病防治是人道主義,還是政治計畫?抑或兩者皆是,但孰輕孰重?何種人道,如何政治?以何評斷成效?
麻風是人類最古老的傳染病,也是古今中外廣受歧視的疫病;中國是幅員遼闊的多元族群國家,其當代政治的動盪史上罕見。諸多稀奇的特質聚攏形成的中國麻風防疫,是一個糾結了疾病隱喻、底層救助、階級政治、科學主義、國家主體與全球衛生的複雜故事。
這個特殊的麻風防疫故事,是在中共邁向「後帝國」實驗的歷史脈絡中逐步展開。我以「後帝國」來定位本書的時代性,主要涵蓋一九四九至七六年間的中國。這段期間一般泛稱為毛澤東時代,但此一表述通常指涉政治極權與一九五八年正式開始的集體化公社制,卻無法彰顯本書強調的重點,包括:此期中國集體對於歷史、西方教會、醫學知識系譜、發展典範的論述與實作方向,以及眾人對此論述的擁護、配合與矛盾情緒。因此,我以「後帝國」實驗為時代定位,透過三個面向切入分析麻風防疫的實作及結果,並提出論點:(一)中共建國後推動的後帝國政治工程,企圖一併去除帝制中國傳統、殖民帝國遺緒,以及未能擺脫前兩者影響的民國政治與社會。然而,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是否真的超越了「帝國」的影響,值得探究。(二)檢視後帝國論述的歷史斷裂與實際的醫學傳承,得以看出一九四九年後的麻風防疫,是建立在教會及民國時期的衛生基礎之上,而後發展出其時代特性。(三)民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倡行的科學主義,在中共建國後更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結合,造就了政治性高於科學性的形式主義教條,對麻風防疫產生正負交錯的影響。
這三個分析面向呈現出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展開的後帝國論述與改造,如何陷於由民族主義、科學主義、唯物主義等意識形態交叉構成的政治教條。然而,弔詭的是,麻風防疫卻在種種的政治動盪與矛盾之中,表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因此,如何、從何評估其時代性與成效,是為挑戰。
後帝國論述及其內在矛盾
普世常見,後設史觀會隨著政治主體的位置移動而改變:從土匪流寇到革命家、從革命黨到執政黨、從傳統到現代、從殖民到後殖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簡稱「二戰」)後,殖民主義陸續終結,後殖民時代的反省史觀主要是為了重建主體的歷史,但新興國家的認識論與方法路徑則可能各有不同:有時強調去殖民的立場,愛恨情仇卻是常見糾結,甚至難以放棄前殖民國的影響或支援;有時企圖超越殖民/被殖民的二元架構,以突顯殖民地的能動性,如強調殖民醫學對於帝國和全球的影響等。後殖民時代主體重建的政治光譜,向來黑白斑駁。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不僅是「反傳統」的現代性改造,更可謂「後帝國」的巨型政治實驗。其動機正如毛澤東寫於一九四五年的〈愚公移山〉一文所示,這位極端民族主義的擘劃者呼籲民眾,挖除擋在中國前面的兩座大山:
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
於是,中共全面驅逐帝國主義勢力,並以美國為代表「西方」的頭號敵人,同時透過階級鬥爭與歷史清算,企圖推翻「封建制度」的「傳統」。從一個十九世紀末才逐漸進入現代性制度的國族及其後繼者來看,中共清算西方帝國、帝制中國與前朝民國的遺緒,至少在論述上,讓這個後帝國的斷裂相當徹底。由此展開的政治清理,使得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歷史論述、醫療走向、社會組織、文化慣習、教育制度等,都出現瞬息萬變的斷裂。
中共的後帝國清理,表面上與世界諸前殖民地的獨立建國歷程雷同,官方與知識分子都宣稱要揚棄帝國殖民主義之惡,以重建國族主體。然而,中國的情境並不盡然適用一般後殖民論述的政治架構,由以下幾個重要差異可看出其獨特之處。
中國不曾淪為單一殖民地。後殖民研究主要針對的歐美殖民國,雖聚眾占領中國,卻並非由單一帝國獨領風騷;仿效歐洲帝國而改造成形的「次帝國」日本,亦曾據領中國的部分地區。帝國的影響在中國,有聯手豪奪巧取的霸權,也有如百花競放的較勁與現代發展,多元而複雜。
在一般的殖民情境中,殖民政府掌有絕對的治理主權,所謂的殖民地菁英也多以仿效殖民母國的主流為自我定位。然而,諸多帝國都曾透過政權和非政權的管道,在中國不同角落發揮影響,尤其是英、美、德、法、日等國的實力最為深刻。這些國家主要並非透過主權政治橫掃中國大地,而是從不同面向發揮影響,如基督宗教、生物醫學、科學技術、觀念思潮、經濟貿易、政法制度、生活方式等。甚至,不同的中國學習者也對不同帝國的制度與知識來源有其好惡,對現代性的接收反映國際政治的競合,常見諸如英美派、德日派、蘇聯派等不同分類與認同,這些都可能影響其日後在中國本地的知識與技術實作,以及鬥爭。
在這些帝國影響的前線上,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底層與菁英、主流與非主流的分野模糊。有時,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菁英率先學習這些西方引進的科學技術與現代觀念;有時,底層民眾反而因緣際會站在現代性的風口浪尖,在醫療慈善與福音傳教等方面尤其如此。不少最早接觸並信仰基督宗教者乃中國貧民,走投無路之人較可能主動接受「邪門歪道」的西醫治療,家貧子弟也較願意為了生計而接受西醫培訓,如一九四九年後的首位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便是一例(第二章會再提及)。
中國知識分子揚棄傳統的程度與決心,遠非一般後殖民國家常見對傳統本質化與美化的傾向可堪比擬。自清末民國以來,不少中國知識菁英嚮往西方現代性,他們更為痛恨的可能是造成國力積弱的「傳統」,甚於侵略中國的「帝國」。殖民批判的先驅薩伊德(Edward Said),以「東方論」(Orientalism)的觀點,直指殖民主義對殖民地人民與文化的貶抑傷害。相較之下,日本和西方帝國在中國引發的情緒,不僅有一般民眾對外國人士的仇恨,也常見知識菁英藉他者之眼來批評己身國民,以企圖重塑民族形象。這種徹底反傳統的思潮,自一九一九年興起的「五四運動」即明顯展現,只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並沒有足以導致社會基本改變的力量。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官方論述與作為,則延續甚至擴大此一趨勢,更為徹底地揚棄傳統。
不過,中共雖然更加批判帝國主義的影響,卻也同時採納諸多西方觀點來檢視自身的發展與文化。歷史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稱這樣的現象為「東方人的東方主義」,認為各種的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不僅受到歐美觀點的影響,更皆以化約的方式想像中國的過去,不論是稱之為「儒家主義」、「專制主義」、「文官制度」、「家庭主義」,乃至於「封建」或「亞細亞」生產模式等德里克稱之為「馬克思版本的東方主義」的說法,都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的分析與批判。更弔詭的是,中共建國後十年內,卻是以全盤仿效另一個「西方」帝國—蘇聯,來推展其後帝國的政治及科技改造(見第一、二章)。這個實驗設計頗為嘲諷:既是建立在對中國歷史與傳統的化約主義之上,又是建立在以社會主義「帝國」取代資本主義「帝國」的一廂情願之上。然而,傳統社會的階序服從與社會主義的階級政治交融混雜,效應如影隨形。與蘇聯交惡後,毛澤東思想的大纛又讓中國落入帝國般的高壓統治。
中國的後帝國掙扎,未曾走出內化深刻的帝國架構。中共因近、現代中國的劇烈變遷而產生的後帝國論述與改造實驗,交織了複雜的自我批判與二元對立、內外混融與前後矛盾,是本書案例的歷史脈絡。因此,儘管後殖民討論的某些觀點,例如殖民影響下多元混融的認同,或強調讓在主流歷史中消音的底層得以發聲等,有助於我檢視中共的國家主體重建,進而看到中國面對多重帝國影響時的糾結及其代價。但是,在內容分析與政治指涉上,我使用「後帝國」而非「後殖民」一詞,便是為了指出中國和後殖民國家在歷史情境與分析上的差異,尤其是國家論述與實作的矛盾,突顯毛澤東時代下中國的帝國反覆情結。
教會與民國的生物醫學遺產
在全球邁向後殖民的時代,中共以強制性的社會主義政策,讓中國進入後帝國的集體精神狀態,雷厲風行祛除新舊「帝國」(反帝、反封建)與「殖民」(教會、文化)的影響。然而,宣稱與過去決裂的中國,並不可能從歷史的「真空」中開展未來。
生物醫學自一八四○年左右由基督宗教傳教士引入中國,各種現代性之力同樣由此進入,形塑中國近代以降的歷史變遷。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生物醫學論述及發展,以麻風為例,明顯可見對於教會影響的二元對立、借力使力等並存的愛恨矛盾。借用非洲醫療史學者梅根﹒沃恩(Megan Vaughan)的話來涵蓋,「殖民醫學史可以成為殖民理念史、殖民論述史,我們也可以透過它來檢視殖民主義的權力與限制。」同樣地,分析後殖民時期的殖民醫學敘事,也可檢視後殖民政權的權力與性質。
無論歷史論述如何斷裂,從醫學制度、醫療機構、醫學教育及教材語言、衛生發展藍圖等觀之,一九四九年後,在否認史觀和技術移植(蘇聯化)的困惑中,正是無數實際上承襲了多重歷史影響的醫療專業人員,尤其是知識分子型的醫師,銜接起斷裂,讓中國的麻風防疫得以繼續往前走。第一代麻風醫生及其前輩的醫療訓練背景,悉數受到福音醫學或帝國醫療建制與師資的影響(包含民國時期的公立醫學院校)。中共建國後,首要之務也是清點與接管教會及國民政府建立的各種衛生基礎設施(見第二章)。由帝國力量開始發展的生物醫學,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國麻風防疫的創業基礎。
教會的影響是檢視中國現代性之路時不可或缺的面向(見第一、二章)。這方面的影響之巨及遺產之龐大,在此僅藉「中華續行委員會」於一九二一年八月的一份調查,以蠡測海。中國當時成立二十七所醫學校(見附表一),其中十四所由中國人主辦(三所為國民政府的中央政府建立、七所由省政府建立、四所係私人贊助維持)、十一所由外國人管理、兩所為中外聯合管理。由外國人主辦的學校,包括醫學大學與醫科專科學校,除了一所醫科學校係為日本在東北所辦,其餘皆具教會背景。教會學校採取五年學制;由中國人建立的學校多為四年制,皆為醫科專門學校,尚無醫學大學,教學師資主要畢業於日本的醫科專門學校。順帶一提,此份報告強調教會建立的醫學大學與日本和中國人自建的醫科專校的差異,透露出對於不同模式的偏好。一九三○年代,以維護世界和平為旨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對源於德國的日本醫學訓練,亦不以為然,指日本主要培訓中級技術的醫療人員。因此,國際聯盟建議國民政府應雙軌併行,同時培育高階醫師和中級醫士。這些都顯示當時在中國的各種國際制度、學派及語言的競合影響(第一章「北京」一節會再提及)。
而在醫院方面,一九二○年在華宣教會報告的醫院總數為二四六所,中華續行委員會調查了其中的一六五所,當中「有一個外國正規醫師的醫院」占六九%、「有兩個外國正規醫師」的占一八%、「有三個以上外國正規醫師」的占八%、沒有外國正規醫師的醫院占五%。民國時期,國民政府已計劃在每縣建立醫院並補充醫療人力,雖然醫師數目依然不足,但據一九五○年的統計,全中國擁有五萬一千名醫師。
一九二五年起,國民政府與「國際聯盟」專家合作,提出國家醫療衛生的組織改革藍圖,並著手進行標準化的疫病統計。一九二八年,進一步立法通報九大傳染病,麻風雖未列入強制通報名單,但也受到相當關注。中共建國後的衛生發展,相當程度上延續了這份農村衛生基礎建設藍圖,包括:控制農村傳染病(如結核病、性病與血吸蟲等「社會性疾病」);普及農村衛生組織與協調、建立農村保險;仿效東歐模式發展農民衛生人員(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赤腳醫生」)等。此外,一九三五年,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蘭姆生(Herbert Day Lamson)根據六年的授課教材與經驗,詳細彙編了中國社會性疾病的各式資料,以社會學觀點分析貧窮、生計、文盲、健康、婚姻、家庭等中國普遍的社會問題面向,其中並包含麻風、結核、性病、心理疾病、公共衛生等獨立專章。以麻風為例,蘭姆生列舉教會和國民政府的既有防治措施與規畫,如一九三二年中華麻瘋救濟會在上海舉行第一屆全國麻風會議,並擬設置全國麻風委員會等構想。
由此可知,民國時期官方及民間(含教會)的醫療工作者很清楚疾病的社會面向,並依此理念及國際合作開展相關防治計畫,如著名的河北定縣農村衛生實驗區。然而,國際聯盟的中外合作藍圖等規畫及成果,幾乎不見於一九四九年後中央級的官方記述主線。不過,在地方志、機構志或各式內部報告中,仍留下關於以前衛生建制的零星描述(如第四章的「雲南」一節)。
換言之,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農村衛生發展,與民國時期最大的差異,並非是對農村與「社會疾病」的關注乃社會主義人道創舉等常見宣稱,而在於中共的關注力道與投入規模,造就了可觀的衛生人力,擴張了農村衛生基礎建設。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時,全國已培養三十五萬名醫學院層級的醫師、七十萬名中專層級的醫師、以及一百八十萬名赤腳醫生(文革後改名為鄉村醫生)。中國得以在三十年間造就此衛生成果,最關鍵的做法,便是縮短學制、簡化訓練,以強力政治動員達成衛生目標,第一與第四章對此會再討論。綜合來看,中共延續了教會與民國的醫療衛生遺產,加上其特有的政治論述與實作,從而明顯改造了廣大農村的衛生地景。
麻風的慢性病特質,正適足以理解中共後帝國論述的渴望與遺忘,及其衛生實作軌跡。麻風是跨越十九世紀而貫穿二十世紀的慢性傳染病,與短期爆發、致命性的疫病危機或較不受歧視的傳染病相比,對於我們理解政治和醫療糾纏的歷史,有其獨特之處。因此,麻風不僅是後世追尋西方傳教士在世界各地進行醫療救助的重要疾病,也是檢視本土社會對帝國衛生建制反應的常見疫病。歷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的說法切中麻風研究的意義:
傳染病,就性質而言,是危機中的非典型事件及醫療介入……。檢視如麻風之類的慢性病,得以讓我們見到更多病患和醫療人員的日常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在應對政府政策的過程中,如何緩慢地變化。
透過慢性的麻風病,我得以揭開教會與民國建制對當代中國的影響,並檢視中共後帝國實驗下的治理特性與防疫日常。以人類學的方法研究在地日常生活史,有助於探討本土社會在殖民與後殖民過程中的調適。如此由下而上重建的醫療史,也得以對照由帝國的英雄觀點或反殖民的對立觀點所再現的一元論歷史。
作者是人類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領域主要從愛滋、毒品與麻風(漢生病)等疫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國際與全球衛生,理解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此外,亦從自然資源的治理變遷,研究環境、社會與政治經濟角力等議題。英文專書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及其譯寫而成的醫療民族誌《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2013),獲得臺灣、中國、香港等地的諸多獎項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