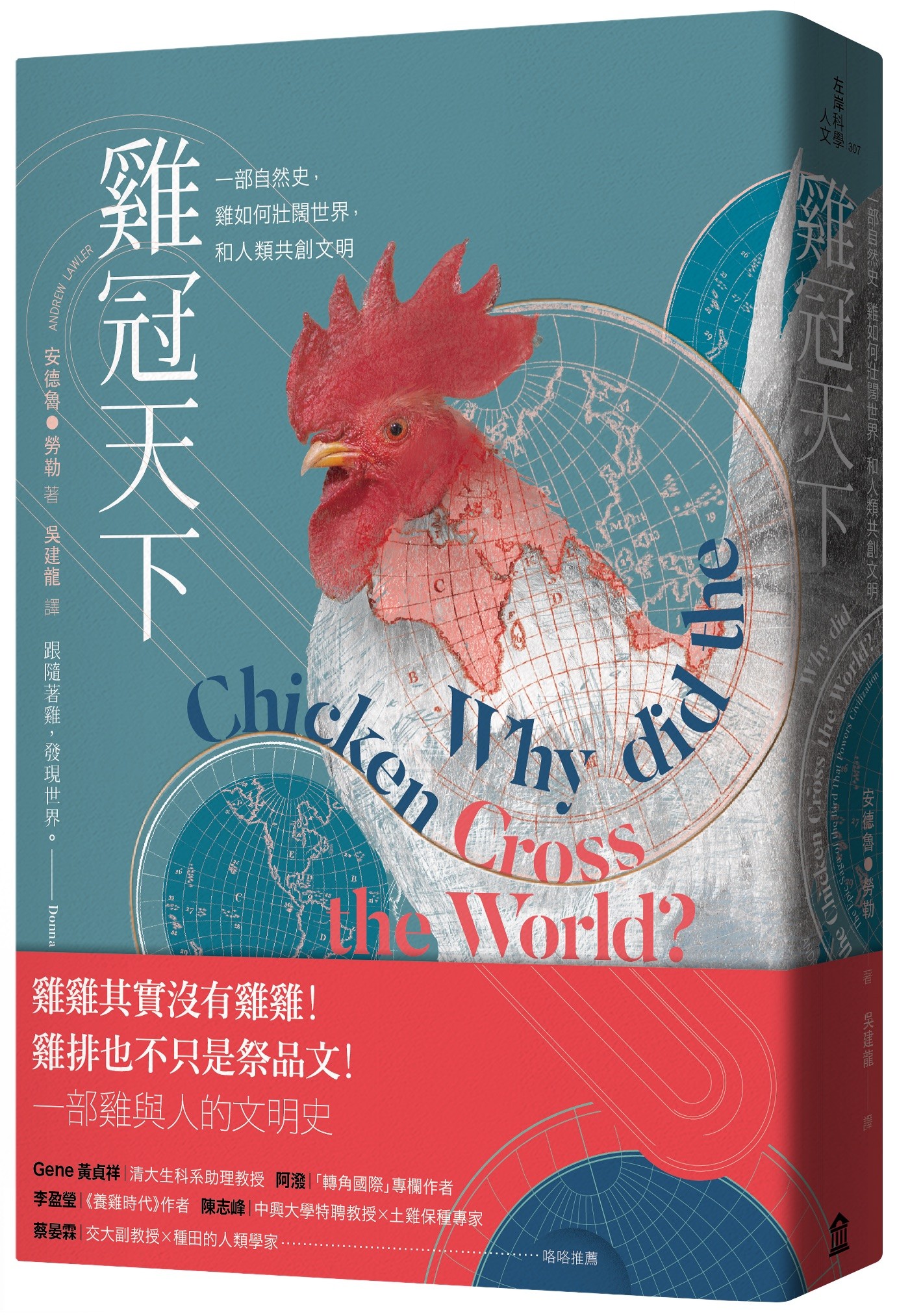
公雞頭上的冠,是鳥類最出色的特徵。它可以幫助散熱,向潛在競爭對手提出警告,也是引誘母雞的信號。在公的紅原雞身上,雞冠就是紅色鋸齒狀,稱作單冠。然而家雞的冠就不是那麼簡單了,其種類多如繁星,包括玫瑰冠、軟墊冠、花型冠、豌豆冠、胡桃冠、V型冠以及希爾基斯冠等等,每一種都有自己的來歷。比如花型冠這種華麗的變異,可追溯到中古世紀時,統治西西里島和諾曼第的歐洲皇室所培育出來的品種。而較小的豌豆冠在寒帶地區有其實用性,因為它可以減少體熱散逸。此外,雞冠也有灰色和鮮藍色的。
任職於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雷夫.安德匈明白,這種由於人為選擇所改變的生理特徵有助於我們探索家雞早年馴化的歷程。舉個例子,比起單冠公雞,有玫瑰冠的公雞較難讓母雞受精。安德匈想知道,為何人們甘願花大錢,只為了把雞冠改造得看起來像個小型法式貝雷帽。他和其他十九名研究者所組成的團隊,利用新近發展的遺傳工具找到了參與製造雞冠的等位基因(對偶基因)。等位基因是位於染色體特定位置上的那些基因,而染色體是由盤繞成螺旋狀的DNA所形成。安德匈及其研究團隊發現,長出玫瑰冠時,有個基因會「跳躍」到其他位置,但這會破壞讓精子得以健康游動的機制。可想而知,該研究將有助於研究人員了解人類男性低生育率的原因。
玫瑰冠的優勢,在於較難被鬥雞擂台上的對手給抓住。安德匈也知道,懸掛在鬥雞兩頰的肉垂往往小於紅原雞或其他家雞品種的肉垂。該研究提供了遺傳上的直接證據,證明人類長期以來就一直在改造家雞,使之在打鬥時更佔上風──即便是以低繁殖率為代價。
紅原雞在面對體型較大的對手時,會拼命守護母雞和小雞,但是當自己面臨危險時,牠們也可能逃跑。因此,要繁殖鬥雞,就得選擇那些會留下來與對手搏鬥,並且具有體型優勢的個體。有些學者推測,源自亞洲南部的鬥雞活動,最開始是種宗教活動。一個氏族或村落,也許會將其神聖的公雞拿來跟其他群體的公雞一較高下。舉例來說,在泰國北部有一崇敬祖靈的儀式稱為「faun phi」,該儀式包含了一種宗教性質的鬥雞,這可能是古老習俗的展現。
如果比拼鬥雞是馴化過程的主要驅動力,那麼家雞之所以能夠傳遍整個亞洲南部,然後再到世界上其他地區,這或許都跟鬥雞活動密切相關。今天的美國鬥雞養殖戶在古代可能有些同行,他們帶著自己所養的貴重雞隻長途旅行,而且不只帶著雞,連怎麼拿雞來賭博也都帶到其他社群裡去了。
史上最早的鬥雞紀錄之一,發生於公元前五一七年的中國,該次鬥雞的地點在孔子故鄉魯國境內,彼時孔子仍在世。那時,鬥雞已是具有繁複禮法規範的貴族運動,而家雞出現在華中及華北地區至少有九百年了。雙方的雞都配有金屬距,有一隻雞還被灑上芥末,好讓牠更加光滑而難以被抓住。兩個敵對氏族之間的鬥雞賽,最終竟開啟戰端。「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一份古籍如此述道。
而西方最早關於鬥雞的確切證據,也來自相同時期。考古挖掘者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墳墓裡發現過一顆小圖章,上頭有隻呈現打鬥姿態的公雞圖像,該圖章的擁有者是耶撒尼亞,他被稱作「國王之僕」。有個同名的男子──瑪迦人之子耶撒尼亞──在聖經《列王記》和《耶利米書》都有提到,他是巴比倫人於公元前五八六年攻擊耶路撒冷之後的一名軍官。戰爭結束時,所羅門聖殿被夷為平地,城內菁英則被囚禁於巴比倫。那顆圖章或許可以追溯到這個時期。另一顆有打鬥公雞像的圖章,則為號稱「國王之子」的約哈斯所有,這顆圖章可能也是同一時期的產物,但出處不詳。
當時,耶路撒冷不遠處有個地中海岸的港市亞實基倫,那裡的菲立斯人可能有養鬥雞,因為挖掘人員曾在該地發現許多足距發育良好的公雞遺骸。他們在那個時期也會利用母雞,因為這些母雞的骨頭顯示牠們為了生產大批雞蛋,正在消耗大量的鈣質。耶穌誕生前的幾個世紀裡,鬥雞在中國和西方都扮演著一種準宗教性的角色。中國有篇大約出自公元前四世紀的道家著作,裡頭的故事講述了為國君飼養鬥雞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這是則關於培養泰然自若所需之耐心的寓言。而同一時期的古希臘,雅典人會聚集在獻給戴歐尼修斯的劇場裡觀看鬥雞賽來提醒自己,曾有兩隻爭鬥的公雞激發出希臘軍隊的鬥志,隨後他們打敗了比自身還強大的波斯軍隊。在那座獻給酒神及歌謠之神戴歐尼修斯的莊嚴劇場裡,鬥雞則被安置在大祭司的座椅上以為裝飾。
時序推移,心靈的搏鬥轉型成一種較為世俗的活動,也許就如鬥牛一般,最初是種儀式,隨後逐漸變成世俗娛樂。公元初的幾個世紀,在西方的羅馬帝國和東方的漢朝這兩大舊世界帝國境內,鬥雞已是許多村民、士兵、貴族的尋常消遣。這種活動成了許多不同階級的男子相會面、搞投資,還有坐觀雄性動物逞威風的去處。
到十九世紀初,這種把兩隻公雞丟在一起打到至死方休的活動幾乎在全球各地都能看到,不過非洲西部及南部是個例外,鬥雞在這地區反常地從未落地生根。在印度,英國官員曾把他們的雞抓去跟穆斯林王子的雞比賽。一名造訪中國的英國人在一八○六年寫道,自唐代以來的千年裡,「鬥雞是中國人極為熱衷的運動,」他還補充說鬥雞在中國盛行於上層階級,就跟在歐洲一樣。鬥雞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玩法,有些玩家是給雞繫上長的金屬距,有些用短距,其他則是讓鬥雞留著天生的足距去打鬥。但鬥雞一般來說是男人們──幾乎總是只有男人──拋下種族跨越階級彼此廝混聚首之處。十九世紀初時,有位造訪維吉尼亞州的歐洲人非常驚訝地發現,黑人奴隸在鬥雞賽場下注的狠勁跟他們的白人主子沒有兩樣。
沒有人比英國人更樂於鬥雞,他們或許在羅馬人到達之前就已經在玩了,而且可能是從腓尼基商人那兒學來的。鬥雞場在英國農村的普遍程度曾經就像在今天的菲律賓那樣。十六世紀時,英王亨利八世在他位於倫敦的主要居所白廳宮內蓋了「皇家鬥雞場」;在那個年代,絕大多數的莊園宅第都有數百甚至數千隻雞,為此還有自家鬥雞場、訓練師,以及飼養及打鬥的獨門秘訣。詹姆士一世也是個鬥雞的狂熱愛好者。環球劇場最開始是作為鬥雞場之用,而非演員的舞台,這點莎士比亞完全明白,他在歷史劇《亨利五世》序幕的合唱中問道,「這座鬥雞場豈能容納法蘭西遼闊的疆土?」環球劇場中的廉價座位區被稱作「pit」(跟鬥雞擂台同一個英文字),便是鬥雞較量之處。人們偶爾會把一群雞給放進去,讓牠們打到只剩一隻活存,這便是片語「battle royal」(混戰)一詞之由來。日記作家塞繆爾.皮普斯曾在一六六三年前往倫敦看一場比賽,目睹一名國會議員跟麵包師傅和啤酒師傅對賭,「這群人全在一起互相咒罵、辱罵、打賭。」
皮普斯替這些公雞感到難過,並且驚駭於窮人蒙受的損失,但是其他人卻深受鼓舞。有本十七世紀初的書籍,聲稱鬥雞能使男子更勇敢、更有愛心、更為勤奮。《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狄福於一七二四年寫道,「看到這些小動物的勇氣實在令人欣喜,牠們總是堅持戰鬥,直到其中一方倒下,當場死亡。」那個時期的一名蘇格蘭作家建議應舉辦「鬥雞大戰」,以宮廷之間的鬥雞賽來取代人群的衝突,從而結束歐洲的血腥鬥爭。在一七八○年代,光是泰恩河畔的新堡一地,在為期一週的鬥雞賽中,掛掉的公雞就有上千隻之譜。
威廉.賀加斯在一七五九年的版畫是以相當諷刺的《皇家運動》為題,作品描繪一個混亂的倫敦鬥雞場,裡頭有個失明的貴族、幾個扒手和一票地痞流氓,全都看著兩隻公雞互相繞圈子,而一名震驚不已的法國紳士正審視著眼前這一野蠻場景。時至今日,鬥雞在美國、歐洲及其他工業國家皆被禁止,這主要是著眼於強迫動物打鬥至死的殘酷行徑。賀加斯創作的場景則顯現了其他關注點,其畫作所透漏的問題並非虐待動物,而是人類的愚蠢、糜爛及貪婪。當英國國會於一八三三年禁止在倫敦鬥雞時,其理由並不是為了保護鳥類,而是要終止犯罪以及失序行為。
跟二十世紀初在菲律賓的美國傳教士以及今日的印尼立法者一樣,那些英國國會議員對於來自不同社會群體的大批男子聚在一起連續喝酒賭博數小時的行為深感擔憂。這些行為在鄉下地區或許無人聞問,但在快速工業化的經濟體制下,會被視為沒有生產力而且具備潛在的顛覆性。在新興都市裡──十九世紀的倫敦、二十世紀的馬尼拉、二十一世紀的雅加達──窮人與富人隔離,工廠生活要求迅捷,而賭博是道德薄弱的標誌。
羅伯特.布狄斯表示,「傳統上,關於動物權興起的說法是種英雄式、直覺式的敘事,內容大致是說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在經歷了數千年的奴役和虐待動物後,終於醒悟了過來。」他是位年輕的英國歷史學者,曾研究過動物權運動。他認為,這並非鬥雞者對動物殘酷,而是這群人的舉止本就粗俗。在工業時代,紳士們不會去跟下層階級混在一起,而工人理論上就是要去做工。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和美國,上層及中產階級的婦女經常站在鬥雞禁令的最前線,因為正是她們要求禁止鬥雞的。賭博及飲酒對留在家中的女人來說,通常意味著貧窮跟家暴,而且有礙在新社會階梯往上爬。
英國國會在一八三五年禁止英格蘭及威爾斯境內的鬥雞活動,再過兩年,維多利亞公主成為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贊助者。繼任為女王後,她在一八四○年將「皇家」一詞加諸於該組織的名稱之上。鬥雞仍繼續進行,但他們轉移陣地,到勞工階級愛好者出入頻繁的不起眼處,而多數貴族都放棄參與這項運動了。雖然鬥雞早已失去其地位及合法性,但獵狐活動倒是延續到二○○五年才被禁止。
美國人放棄合法鬥雞的年代比英國人晚,鬥雞受歡迎的程度堪比賽馬,尤其在南方。一七五二年,喬治.華盛頓在威廉斯堡跟維吉尼亞皇家總督一起用餐並討論軍務後,在鄰近的約克鎮觀看了一場他稱為「精采的公雞大戰」。同一年,位於當時維吉尼亞首府的威廉與瑪麗學院禁止學生參與鬥雞這類活動,說明了鬥雞的吸引力。為了彰顯這項運動受歡迎的程度,現今的歷史保護區「殖民地威廉斯堡」仍然養了兩隻鬥雞──漢奇院長及路西法──只是維吉尼亞州法律禁止牠們打鬥。
維吉尼亞州議會曾於一七四○年宣告鬥雞違法,但玩家還是繼續從海外進口鬥雞。喬治亞州於一七七五年跟進;美國國會的前身大陸議會則是猛烈抨擊這項運動。美國獨立後,鬥雞開始被視為英式野蠻的遺毒,但其盛行程度卻未衰減。曾有那麼一段短暫的時間,鬥雞有機會在這個新國家的國徽上佔有一席之地。一七八二年,一位二十八歲、名叫威廉.巴頓的藝術家把一隻鬥雞放進他所提議的國徽設計上。然而,美國國會最終選了以海鵰為設計的國徽。
根據湯瑪斯.傑佛遜的奴僕所述,這位美國第三任總統對於鬥雞跟賽馬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安德魯.傑克森這位戰爭英雄、發跡於田納西州的政治人物,卻熱衷於賭博與鬥雞,他參選總統時的對手就曾拿過這點來反對他。「他對鬥雞的激情讓人害怕,」傑佛遜在一八二四年時對丹尼爾.韋伯斯特說道,當時傑克森正在爭取總統大位。傑克森在競選期間堅持自己已經洗心革面,已有十三年沒賭過鬥雞了。亞伯拉罕.林肯則是不願反對這項運動。有人引用他的話說,「只要全能的上帝允許依其形象所造出來的聰明人公然鬥毆並互相殘殺,而全世界看起來也對此大為讚賞,那麼我就不能從雞隻身上剝奪掉相同的特權。」
在十九世紀這段期間,美國人對鬥雞的狂熱持續減弱。馬克.吐溫曾觀看一場鬥雞賽,他對觀眾們「沉浸於歡樂的狂暴中」感到相當驚訝。他稱之為「一種不人道的娛樂,」但又補充說,「比起獵狐,鬥雞似乎是種更值得尊重且較不殘酷的運動──因為公雞樂在其中,牠們不僅體驗樂趣,也給予樂趣,獵狐則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
婦女團體則是針對鬥雞連同烈酒和其他形式的賭博一起攻擊,各州開始立法禁止鬥雞。到了一九二○年代,鬥雞跟黑幫和酒類走私販子之間都有關聯,不過在奧克拉荷馬州等農業州仍然普遍存在。在首創報紙體育版的媒體大亨威廉.藍道夫.赫斯特運作之下,加州成功禁絕了鬥雞活動。
直到二○○八年,路易斯安那州立法禁止鬥雞之後,整個美國的合法鬥雞賽才完全絕跡。雖然鬥雞在當前美國多數州都屬重罪,但依舊風行於阿帕拉契地區和西班牙裔社區內。比方說,在翻過阿帕拉契山稜線就進入北卡羅萊納州的田納西州寇克郡,鬥雞在檯面下還是挺常見的活動。近年破獲了兩處營運中的大型鬥雞場,這是田納西州大規模進行貪腐調查行動的部分成果。相關單位設局誘捕,托馬斯.法羅指揮了其中一場關鍵行動,他告訴記者,「這就像冷戰期間在蘇聯中樞建立反情報行動一樣。那兒可沒有啥友誼賽,都來真的。」他還說,「行動當天,大家紛紛去上教堂或去工作,就像諾曼.洛克威爾筆下的恬靜社區一樣。但日落之後,他們全變身成吸血鬼了。」
二○一三年時,一名田納西州的共和黨籍議員瓊.倫堡打算提高該州鬥雞相關法規的刑責,現行法律為可處五十美元罰款的輕罪。他希望把鬥雞等同於鬥狗這種可處罰款及徒刑的重罪,但最終事與願違。修法失敗後沒多久,我去他的辦公室找他,就在位於納許維爾的州議會大廈不遠處,他對於反對者頗為不滿,反對者認為鬥雞是田納西州的一項傳統,連安德魯.傑克森都愛這一味,豈可將之妖魔化?「蓄奴也是傑克森支持的田納西傳統呢,」他酸了一句。這位議員擔心,寬鬆的法令會讓田納西州成為組織犯罪的溫床。「我們已經準備好要讓人進來拼經濟,但我不認為這是我們想吸引人家來田納西打拼的東西。」
傑克森對鬥雞的「激情」被人批評超過一個半世紀之後,在二○一四年慘烈的國會初選階段,鬥雞一度成為密奇.麥康諾及其政敵馬特.貝文之間的選戰焦點,前者是肯塔基州參議員,也是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後者則是茶黨力挺的對象。麥康諾支持一項農業法案,該法案提高了參與鬥雞活動的罰款,鬥雞養殖戶聯合協會的主席預言道,這項舉動將會「摧毀」麥康諾的政治前途。幾個月後,貝文參加了一場鬥雞支持者的大會師,他表示,「如果某項行為是這個州的傳統之一,我認為將之入罪並非好主意,我是不會支持的。」
他的出席及意見引發了全國輿論譁然,後來當一段競選談話的錄影畫面公諸於世後,抗議聲浪更是有增無減,他在錄影中敘述小時候是如何把雞腳綁住,然後抓著在頭上甩來甩去,最後再把雞頭砍下。「有時候雞腳會突然扯斷,」他用搞笑的口吻對著群眾的不安笑聲加了這一句。
當我在馬尼拉向盧宗問到美洲的鬥雞活動時,他悲觀地搖搖頭,也證實鬥雞在墨西哥、哥倫比亞和美國都跟毒品交易和犯罪集團日益緊密結合,進一步敗壞了原本在全球各地都已經很差的名聲。跟任何血腥的運動一樣,鬥雞長期以來總是跟喜愛喝酒賭博的男人扯在一起,而且只要哪裡有在玩鬥雞,哪裡就有下毒、咒術,以及任何可以拿來擊敗對手的奧步。但現今這個年代,高科技藥物和大把鈔票才是王道。
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貧民窟的邊界,一名叫做羅連佐.弗拉濟歐的鬥雞養殖戶告訴我,在這擁有十幾座鬥雞場的都市裡,發生著令人不安的變化。「養殖戶之間不再稱兄道弟,」弗拉濟歐說道,他是個留著粗硬黑鬍子的削瘦技工。「以往人們都會關注彼此──過去一向是很友好的。」如今,鬥雞場外的比拼往往更為暴力,「場外不時有人拳打腳踢,一地碎玻璃,」他搖頭補充道,「超多人在喝酒。」鬥雞場的老闆會收入場費,而鬥雞主在每場比賽要繳出賽費和裁判費,但真正的金流是賣啤酒的收入。
弗拉濟歐在他小農場的一端有個大雞舍,裡頭養了三十五隻鬥雞,每一隻的籠子都很寬敞。裡頭通風良好,地面鋪著乾淨的鋸木屑,也沒有多數集中式養雞場經常會有的刺鼻阿摩尼亞味。有些雞的羽色看起來像紅原雞。有個名叫「博洛斯」的品種是沒有尾巴的,而帕蒲侯斯則是在臉頰上長著小簇羽毛的品種。這些特徵都能夠在打鬥之中保護雞隻。打從他的教父在他十二歲那年送他人生中的第一隻雞,弗拉濟歐就開始飼養並參與鬥雞比賽,迄今已三十年。「這不是因為有利可圖,」他微笑道,「而是熱情。」
一旦他看中了某隻有潛力的新鬥雞,他會花幾個月的時間讓那隻雞適應周遭環境。他會把牠的雞冠切除,這樣在場上對手就不能抓住牠;修剪羽毛,使其不致於被熱帶地區的酷熱所影響;並且將尖銳的足距給截斷。等到傷口癒合,雞大約一歲大時,就會在庭院裡的一個臨時鬥雞場內進行訓練。他在飼料裡只添加了維生素,那些飼料是他的母親根據他的配方每個星期自製的。他說,「每個養殖戶都有自家的配方。」針對某些看起來無精打采或狀況不佳的雞,他也經常調配特定的飼料給牠們。
弗拉濟歐會先拿「鬥雞偶」來測試鬥雞的戰鬥力。之後他會把牠跟另一隻雞一起放進場內,不過在一開始他會謹慎地將雙方的嘴喙包起來,然後在牠們雙腳銳利的人工距上面再套上小「塞子」,以避免受傷。大多數的公雞要滿十四個月大才能進行比賽。傳統上,委內瑞拉是使用玳瑁殼製的短距,跟其他國家所使用的缺德鋼刀形成強烈對比。由於海龜目前是保育類動物,所以他們改用塑膠製的人工距。他從架上拿了一個給我看,我看了嚇一跳,跟我在馬尼拉看過的致命金屬長距相比,眼前這個是如此輕薄,看起來也鈍鈍的。弗拉濟歐歎道,「這裡現在有很多哥倫比亞來的養殖戶,所以越來越多人使用長距。」那些比賽就很暴力血腥,他補充道。當然,使用長距的鬥雞賽通常都是速戰速決,幾分鐘就定出勝負。而委內瑞拉的鬥雞賽則可持續十五到二十分鐘,因為得要花比較久的時間才能幹掉對手。
他把我拉到角落的一個籠子邊,裡頭有隻黑白相間的公雞,因為打鬥受傷而正在調養。「鬥雞的職業生涯只有一個終點,」他說道,「死亡。」弗拉濟歐的兒子走進雞舍,這十二歲男孩顯然是待在家中跟雞群一起長大的。「要是他有興趣,那也不錯,」弗拉濟歐邊說邊看了他兒子一眼。「但我不會強迫任何人參與──自己得要有心才行。」
鬥雞熱潮的衰退始於十九世紀的英國,因為雞開始在都市居民的餐桌上有了新任務。不過鬥雞就算到下個世紀依然不會消失,在菲律賓、委內瑞拉以及肯塔基和田納西的偏僻林間,這活動肯定照樣蓬勃。隨著都市興起、替代性娛樂像是電玩的發展、越來越多人意識到虐待動物的情況且對此現象難以忍受等等,導致鬥雞在絕大多數的國家面臨長期而緩慢的衰退。還有一點,在我們這個都市化的世界裡,幾乎看不到活生生的雞,也摸不著牠們。讓機器去互毆,更乾淨也更單純。
然而,這個古老運動的幽靈依舊飄蕩在我們日常的英語詞彙和片語中。我們或許不適合(cut out for)一項工作─這片語是引自一隻鬥雞的羽毛正被修剪─但我們仍然可以打一場混戰(battle royal)、展現勇氣(pluck)、保持自大或自信(cocky or cocksure),有時還能鬥上一鬥(have a set-to)。無論鬥雞的道德位階或法律地位如何,我們還是會繼續從駕駛艙(cockpit)裡駕駛我們的船舶和飛機。
作者為科學線記者,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家地理雜誌》《史密森尼學會雜誌》等撰文,《科學》雜誌專欄作家,主題多為考古、文化遺產等。
書名:《雞冠天下》
作者:安德魯・勞勒(Andrew Lawler)
出版社:左岸
出版時間: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