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塔中的銀行家
「銀行交叉口」(Bank juncture)匯集了不下九條街,口語中說的倫敦「金融城」或那「一平方英里」即金錢機器長年運轉的輪機室,就是以這個路口為中心。交會於此的其中一條街是針線街,那裡有擔任英國央行一職的英格蘭銀行以沒有窗戶的科林斯柱式,巍然宏偉地延展開來。它在銀行交叉口是個讓人仰之彌高的存在,負責穩定地印著錢並定出政策,好維持聯合王國金融體系的運作。英格蘭銀行透過一種名為量化寬鬆的手法創造了數位英鎊,然後再拿這些數位英鎊去購買資產與政府債(券),藉此將這些無中生有的錢注入英國經濟裡。量化寬鬆會讓資產價格膨脹,所以也自然會讓富者愈富。央行運行的關鍵機制,天生就利於富人。銀行交叉口也是倫敦交通的樞紐:計程車稍早被禁,為的是紓解壅塞。我站在七點鐘的人行道上,天上下著微雨,但城市運作已經完全入檔了。我今早的行程是要去拜訪銀行家,地點是他所在那棟由玻璃、鋼材與混凝土堆疊出的高塔。但首先我想去各條街上晃晃,吸收一下這一帶的氣氛。
金錢機器的人類齒輪從四面八方抵達這裡。從肖爾迪奇或其以北的地點,他們會走A10這條可以一路通往諾福克郡金斯林(King’s Lynn)的公路。從南邊,也從延伸到海濱的郊區、村鎮與城市,他們會行經倫敦最古老的火車站—倫敦橋站。在晨間通勤的尖峰時刻,上班族大軍就像一場沒在舉牌的抗議遊行,從車站的方向出發,穿過倫敦橋的本尊,然後湧入倫敦的古老金融區(晚間這同一批群眾會反向穿過泰晤士河,朝著回家之路而去)。利物浦街站會接收從東邊過來的混亂。而來自各個方向數以千計的上班族就從「地下鐵銀行站」(Bank Underground Station)冒出到地面上,進入到又一個工作日。那些移動中的人體震動著為金融業而奔波,也為這些狹窄的街頭賦予生命。
英格蘭銀行的壯觀石柱毫不客氣且具體地為倫敦主張了他們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透過奴隸船、勞埃德的咖啡館,還有船運保險,金融城從十七世紀以降操縱著大英帝國與重商主義財富中的金融架構。金融業那將倫敦連結到世界各隅的全球性,如印痕般烙在了金融城的古老街道內;那些街道就如歷史學者大衛.基納斯頓(David Kynaston)所言,鋪對了好東西,鋪著金錢。那些—由倫敦銀行界出資的—「發現」之旅開啟了新世界,催生出奴隸制,也創造了得以對人類與物質資源進行擷取的整具帝國機器,而內嵌在這些旅程中的種族政治,並無法讓人一目了然。但有一種早期用來擴張金錢的機器,伴隨其不可見的陰暗過往,確實在這些街道上留下了印跡。
金融業的古老運作在這些如迷宮般複雜的通道與巷弄中,留下了路名的線索—從兌換弄(Change Alley)到康希爾街(Cornhill St.)的皇家交換所3 都是例子。不過如今在這些地方你要不是看到癮君子聚集抽菸,就是會看見靠著牆的女性匆匆把午餐吃完,好繼續去擔綱薪水沒那麼理想,但可以讓金錢機器不至於散架的服務業角色。在社會學家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對倫敦金融業員工的研究中,她形容那是一種菁英主義的雄性環境,當中有一種氣氛是被誇大的陽剛氣質,而這一點也讓—在行政職占大宗而與高位高薪無緣的—女性難以入主帶頭的管理職。金融圈的陽盛陰衰已慢慢變得有目共睹。
從銀行交叉口走到莫爾蓋特(Moorgate,一譯沼澤門),我途經一長串被塞進古老建築的咖啡店,每一家都是家喻戶曉:Pod、星巴克、Eat、Pret、Coco。而在時尚的米其林餐廳如Hispania 裡,服務生會穿著白色西裝伺候身穿深色西裝的男客。當代金融業的需求重組了這些古老街道的商業行為。密室金融服務中心填入了餐飲店舖的空檔。在像Capital House 這樣的公司裡,滿辦公室的律師與會計師會扮演金融業者的嚮導,讓他們不會為監理法規所困,另外他們也會用充滿想像力的會計手法,讓富裕的個人或企業客戶把稅務負擔降到最低。我步行經過大和資本市場(Daiwa Capital Markets)這家日系的投資銀行與證券公司,也經過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這些渠道讓金融流通在倫敦與糾結複雜的其他地點之間。英國境內來自逾二十六個國家的兩百五十家外資銀行,就群集在這些街道上。通往倫敦金融市場的大門被轟開,靠的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的那場「大爆炸」,期間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性質轉變為股份有限企業,並開始歡迎外國金融機構進駐倫敦。與此同時發生的,還有嶄新的數位科技促成了電子交易上路,而電子交易又促成了屬於成交量的第二場大爆炸。一波波包含金流、潮流與飲食文化在內的國際化浪潮灌入了這些街道,也改變了街道的面貌。
衣著打扮與行為舉止都很正式端莊的金融從業者穿梭在街上,看上去一副目標明確、依例行事、自信滿滿,偶爾也與人十分親暱的模樣,祕密與甜言蜜語在門口被悄聲傳遞。大步從我面前邁過的一個個男人身穿帥氣的深色西裝與粉彩的襯衫:領帶已經不是必備。女性的衣著規定是男性的翻版,就是多了高跟鞋這一項。街道上的奢華展現得大大方方,保全工作則做得十分低調。我經過皇家交易所的入口處,那兒站著一名非裔警衛在觀望著四下。始建於一五七一年並重建於一八四四年的皇家交易所歷經定位的調整,如今有高價位的餐廳進駐,包括我坐下來解決午餐的福南梅森(Fortnum & Mason),還有店家在販售名表、珠寶等閃閃動人的無用玩意兒—或者該說是避免人錢多到花不完的工具。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人事物把這個地方收攏起來,也帶動了這個地方。
我一邊吃著沙拉,一邊把耳朵的頻率對準隔桌一對律師母女的對話,她們秀氣地吃著海鮮,看起來份量不大。因為有錢人常懶得搭理我,所以我往往不得不主動「旁聽」。她們安靜的對話透露出這一帶的氣氛背後存在著哪些內心的焦慮。她們討論了職場的人際關係,討論了工作需要的專業能力,討論了與績效綁在一起的紅利獎金,也討論了這些獎金分配上的不公義;然後她們又接續說起古典馬術、騎術學院、競技馬術、在瑞士與巴黎舉辦的國際馬術活動,乃至於她們共同對「駿馬」的欣賞。最終,她們各自收起一模一樣的Burberry 聯名蘋果筆電,走入了雨中。我另外一側的兩個男人在討論身為主管帶人的難點,討論著他們的雄心壯志,討論著麻煩的辦公室政治,也討論著那些「能為你所用」的人。「家裡怎麼樣?」「不太好:我在試著多花點時間跟家人相處。」
從莫爾蓋特走到利物浦街與金融區的東南邊,我途經一個名叫「空間」(Spaces)的房間,裡面滿滿的辦公桌要鎖定、出租給在城市裡巡迴的勞動力。我看到了更多湊在一起抽菸的癮君子,還有用潮濕睡袋裹住自己的無家者,後者告訴我比較安全的做法是白天睡覺,然後晚上醒著保持警戒。一名清道夫推著推車經過,雇用他的是法國企業威立雅(Veolia)。以上便是一部分在金錢機器轉動的街道上創造出各種律動的日常活動。
傳統的金融區戛然而止在朝利物浦街車站而去的路上—那裡有一座當代城市正在布羅蓋特(Broadgate)破土而出,那整個區域都已經開挖,為的是要建設「橫貫鐵路」(Crossrail)。這個巨大的城際運輸基礎建設計畫承諾要紓解地下鐵那令人難以忍受的擁擠。由開發商「英國土地公司」(British Land)所持有徒步區化的廣場已幾近完工,但仍以工地的圍板圍著,這麼做一方面可以宣傳廣場要招租,一方面可以把建築工人大軍給藏住,他們許多人都是來自英格蘭相對不那麼繁榮的東北部。這是一幅以上千種方式持續動盪中的城市地景。廣場旁邊有以無趣的金屬包覆起來的新建物,當中包括瑞銀集團(UBS)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而這些建物正好就代表把古老與嶄新版本的金錢城市劃分開的那條縫線。一個以玻璃跟鋼鐵建起的二十一世紀版金融區往南沿著主教門(Bishopsgate)延伸,接上倫敦橋,然後再沿泰晤士河往東綿延三英里,連起倫敦的新金融附庸,也就是那些直上天際、自信滿滿的銀行與保險業高樓;建築師羅萬.摩爾(Rowan Moore)形容那是一座「走路有風的峽谷」(canyon of swagger)。
這裡就是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一個由加拿大開發商「奧林匹亞與約克」(Olympia and York)主導的私部門城市再生計畫。這個計畫出師不利,在一九九二年遭到清算時有兩百億美元的負債,當時幾乎沒有任何一家在「一平方英里」尋找辦公室空間的國際級金融企業被說動遷至金絲雀碼頭那些閃閃發光的玻璃高塔裡。碼頭地開發公司(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與金絲雀碼頭集團(Canary Wharf Group)在一九九五年接手,而奧林匹亞與約克的負責人—國際不動產開發商保羅與阿爾伯特.賴希曼(Paul and Albert Reichmann)—則繼續活躍在新公司裡。這個開發案自此開始吸引財力雄厚的投資人,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的瓦里德.賓.塔拉勒親王(Prince Waleed bin Talal;一譯阿瓦里德親王,有中東巴菲特之稱),同時交通方面的大型公共投資也開始進駐,由此金絲雀碼頭在一九九九年連上倫敦地下鐵網絡,後來又連上啟用於一九八七年的倫敦城市機場(London City Airport,位置在比金絲雀碼頭更東邊的碼頭區)。瑞士信貸、美國銀行、國民西敏寺銀行、花旗銀行、匯豐銀行—匯豐的大樓設計是由建築名家諾曼.佛斯特(Norman Forster)操刀—還有摩根大通等,都在此地插了旗、開門落戶,並共同樹立起一種城市建立的新模式,後來還被推廣到全球各地,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國各地與重建的貝魯特。在這個模式下,從建築本體與公共空間,再到街邊小吃跟安全防護等事務, 民間開發商會統統攬成自己的責任。一個個綠色廣場與所謂的「 圓形廣場」(circus)—看起來像公共空間,但是由民營保全公司密切巡邏的私人空間—提供了新的私部門都市主義的模板。
倫敦的新金融區是建立在社會住宅跟廢棄碼頭所在的土地上。一九八○年代,柴契爾政府發起將公共住宅私有化,使公共住宅成為一種「殘餘選項」的運動。同一時間,地方政府因為預算吃緊而對公宅表現出一種策略性忽視。這兩者結合產生了致命的結果:社會住宅的社區被擺著任其頹圮,乃至荒廢,而這就導致拆除獲得了正當性,倫敦金融核心地區的東擴也順利取得了土地。至於此一東擴的前進動力,則來自原本應該讓社會住宅的租戶受益、照理要投入基礎建設的公共投資預算。金絲雀碼頭就是建立在對倫敦窮人的剝奪上。街坊與社區之間多年來累積出的軟性社會基礎設施,一夕之間土崩瓦解。那兒的街頭與建物表達著一種獨特的政治傾向,且用的是由玻璃、鋼鐵與混凝土所組成的語彙。
但,時間拉回現在,我人仍在布羅蓋特前往赴銀行家之約。曾經束縛住這片歷史區域的規畫限制獲得了鬆綁,而推了一把的人也包括千禧年早期的明星建築師,他們的作品在當時工黨政府藉「規畫申覆系統」進行的判斷中,被認為將對城市的建築做出顯著貢獻。這種論點讓建商得以突破由聖保羅大教堂為準的限高,也對國際金融界開放了倫敦的天際線。因此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設計了碎片塔;諾曼.佛斯特設計了「聖瑪莉艾克斯三十號大樓」,也就是俗稱的「醃黃瓜」(The Gherkin);詹姆斯.史忒靈(James Sterling)設計了後現代主義的商辦兼零售大樓「家禽街一號」(No. 1 Poultry)。就在一棟這樣的建築中—我不能明說銀行家在哪裡工作—保全人員站在通往大理石門廊的玻璃旋轉門旁。氣派的規模投射出此處的重要性,同時也保護銀行家不受街上的人來人往干擾。接待處一名笑容可掬的女性放我通過了玻璃隔間。另一名女性則引導我進一步走入銀行,來到一間沒有標示用途的會議室,而就跟旁邊其他彷彿複製人大軍的會議室一樣,這間的內部也如出一轍:供人討論如何讓錢長大的場景,是由桌椅跟瓶裝水共同組成。我停下腳步欣賞起藝術家戴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多幅畫作。
四十出頭的銀行家身穿剪裁合身的灰色訂製西裝,搭配光亮的黑色皮鞋。他向我表示,其實有「規定」不讓他跟記者或學者交談。大部分金融從業人員的觀念都是盡量「飛在雷達能偵測到的高度以下」,也就是愈低調愈好。他解釋說:「高調沒有任何好處。」各自為政與保密到家造就了這個地方;對於他能首肯見我,在欣慰之餘,我也感到十分詫異,沒想到他會願意跟我深入說說金字塔頂端的富人是如何利用金融這種黑魔法賺錢。我盡了各種努力去舒緩他對於匿名性不保的疑慮—包括稱他為銀行家。如今身居資深管理職,銀行家的工作是讓金錢機器正常運轉,確保有錢付給銀行的客戶。
銀行家成為金融業大軍的一員,是在千禧年前夕。經由前輩同事的口耳相傳,他得知在以往的交易大廳內,股票會在吵吵鬧鬧中進行實體的交易,甚至他也目睹了一九八○年代那場大爆炸的蛛絲馬跡,當時正逢美國銀行大舉揮軍倫敦。在交易前會喊出我買了或賣了什麼的時代,東倫敦的廢金屬與市場交易員曾經可以走後台通道進入交易大廳,但大爆炸之後的他們已經在機器面前消失無蹤。銀行家入行是在「高接觸交易」(high-touch trading)年代的尾聲,客戶下的單已經愈來愈不由手動方式執行。他形容那「有點像在八○年代的尾聲跟九○年代當一名礦工」。「我開始做這行時,」他說,「交易都已經電腦化,銀行的人才招募政策也發生了質變。」
在這個數位化的美麗新世界中,銀行需要腦袋最好、學歷最高的人才去探索金融引擎當中更迂迴、更有利可圖的可能性,也要去利用那些在複雜性上遠超過單純買賣股票的商機。一個金融投資工具的新時代—包括那些由仲介負責營運,初試啼聲的資產管理產業—於此迎來了黎明的曙光。銀行家獲聘是在「牛奶輪」場合:銀行每年都會主動前往英國各間頂大去吸收人才進入金融業。就這樣,銀行家從牛津的學生搖身一變,成為了雷曼兄弟的交易員。他被用頭等艙載到紐約,並在當地住進銀行給他的公寓,此外他在市區裡移動都靠計程車代步。二○○八年九月十五日,也就是雷曼兄弟破產那天,他人已經回到雷曼的倫敦分支工作了。當時的美國聯準會主席班.伯南奇(Ben Bernanke)將那形容為全球歷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而銀行家的生活就位於這場金融危機的震央。
他告訴我:「記得我星期天上床睡覺,這件事就是頭條。我們知道在紐約有危機的傳聞。我在國家廣播公司(NBC)或彭博新聞之類的媒體上追蹤著消息。」然後他看到一個突發新聞的副標橫在螢幕上:雷曼兄弟申請(美國破產法)第十一章保護。銀行家一下子不知該如何是好。他隔天早上照常去上班,就跟平日一樣,結果公司大廳站了個人在發影印資料,上頭寫著雷曼兄弟國際已經從雷曼兄弟控股的中央企業結構中被移除,在英國進入破產管理狀態。他跟他的同事被要求繼續到班一個月,期間他們不能進行交易,但雷曼正在試圖把一些部門當成持續經營的業務售出,這時候如果勞動力憑空消失,他們跟潛在的買方就會很難談。在例行發薪日的一週之前,銀行家記得「高階管理層說,﹃很遺憾我們沒有資金可以在二十一號發薪給你們。﹄」這比他想像中最糟的狀況還糟。他說,「通常你會想說在投資銀行業,就算打個比方,我身為交易員賠了很多錢,最壞的狀況也不過是被裁員。」這通常不至於成為一場災難:「你會提前三個月被告知,你可以拿到所有累積的配股,那通常就是你被遞延支付的薪酬。」但這次的情形是他連當月的帳單都付不出來。他說,當時的狀況「壓力挺大。」
作者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社會學教授,也是英國國家學術院城市和基礎設施計畫(British Academy”s C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programme)主任。先後於倫敦、香港、北京、福州、阿迪斯阿貝巴、科威特和首爾進行研究。著有《夾腳拖:全球化不為人知的後街小巷》(Flip-Flop: A Journey through Globalisation”s Backroads)和《香港:移民生活、地景與旅行》(Hong Kong: Migrant Lives, Landscapes and Journey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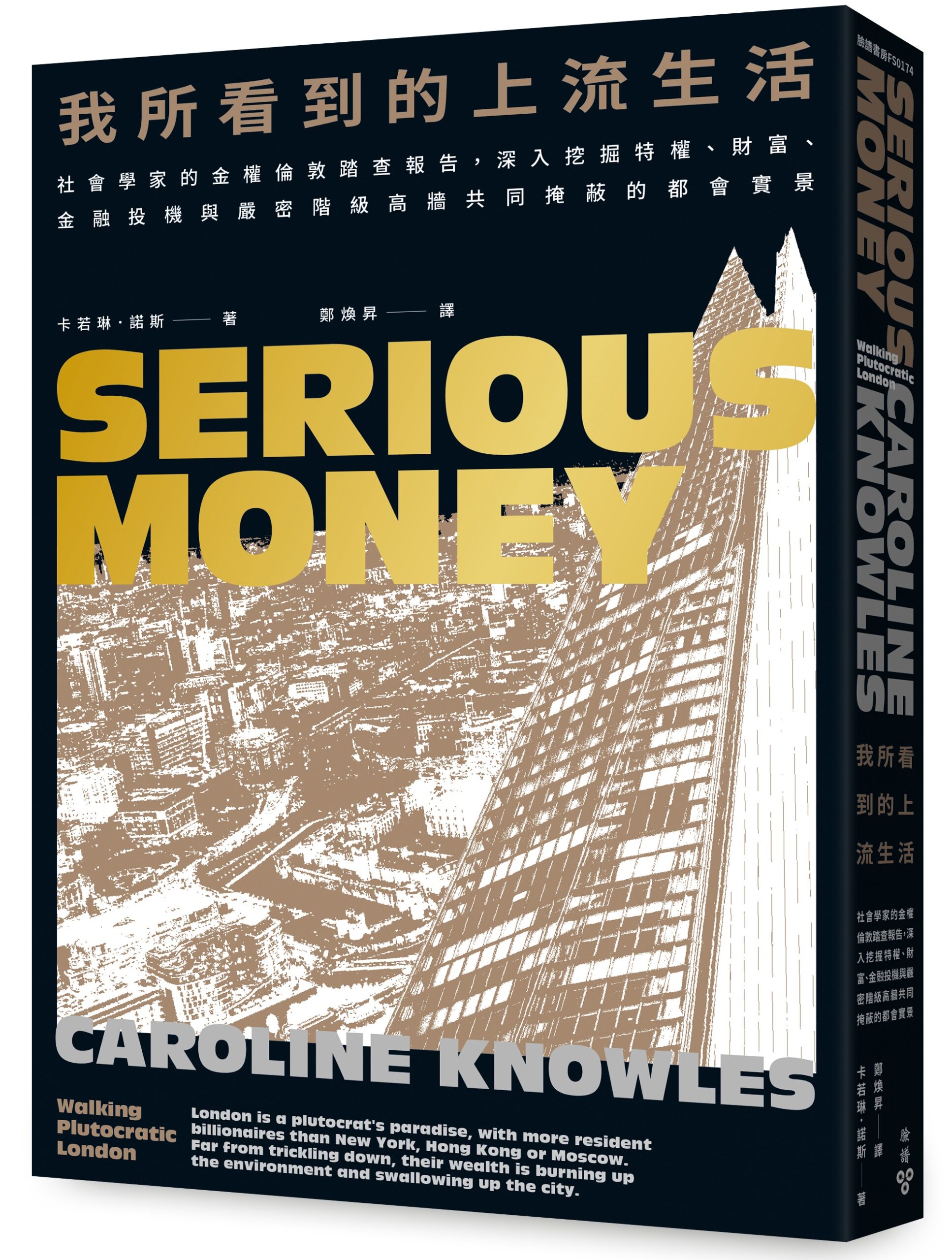
書名:《我所看到的上流生活》
作者:卡若琳.諾斯(Caroline Knowles)
出版社:臉譜
出版時間:2024年1月
- 【書摘】《絕不讓步:龐培歐回憶錄》 - 2024 年 5 月 9 日
- 【書摘】《民族的虛構:建立在想像上的集體認同,如何成為現實的族群矛盾?》 - 2024 年 5 月 3 日
- 【書摘】《拆解反動修辭的大師:赫緒曼思想傳記》 - 2024 年 5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