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新人民?
用一位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的話來說,真正的革命旨在清理過去的時代,並將它粉碎。在許多方面,古巴革命似乎就是這樣做的。過去古巴舊有的軍隊、立法機構、政黨等等機構都消失了。來自美國的遊人發現自己越來越不受歡迎,他們很快就被自己的政府禁止前往古巴旅遊了。美國大使館也關了。古巴與美國政府之間看似不可動搖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型私營企業──無論是地主莊園,還是公司,不論是外國的還是本國的,統統消失了。革命還打破了舊有的階級關係。理論上,配給制使每個人都能以同樣的價格獲得同樣數量的商品。以前的女傭上了學,現在以會計和銀行出納的身分與她們以前的雇主打交道。白領專業人士自願在烈日的灼烤下砍甘蔗,他們的勞動表現通常不如那些他們在革命之前不屑一顧的人們。中產階級的女孩和男孩跋涉到偏遠山區教人讀書,學習如何在沒有廁所的情況下生活,並承擔起體力勞動的責任。政府將勞動人民遷入到了漂亮的大宅院裡,而這些住宅之前的主人現在卻在邁阿密或紐約,住廉價公寓,在製衣廠裡工作餬口。那些被稱作先生(señor)和小姐(señora)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señor的歷史含義更接近於主人或領主。在新古巴,這種稱呼顯然不再適用了。男人和女人的稱呼變成了同志(compañeros和compañeras)。服務員是同志,他所服務的顧客也是同志。即使是斐代爾.卡斯楚,他在革命之初一直被稱為博士,後來乾脆成了斐代爾,有時也叫斐代爾先生。當然,任何過去都不會消失,任何改變都不會是徹底的。儘管如此,革命熔爐中發生的許多事都指向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古巴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斐代爾.卡斯楚在豬玀灣戰役中獲得了勝利,並在飛彈危機中倖存了下來,他試圖實施一場比國家所經歷的更系統、更有目的性的變革。學者們有時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年稱為「向共產主義邁進」時期。古巴領導人從馬克思關於歷史分階段發展的思想中推斷出,只要政策得當,古巴就能縮短發展所需的時間,快速經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實現向共產主義的大躍進。為了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國家幾乎消滅了所有私有財產。一九五九年的《土地改革法》已經沒收了大片土地,一九六○年的國有化沒收了大中型私營企業。但是在一九六三年,革命政府更向前邁進了一步。在這一年,第二次土地改革對私有土地面積進行了更嚴苛的限縮,到六○年代中期,古巴三分之二的農村土地處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到了一九六八年,一場名為「革命攻勢」(Revolutionary Offensive)的運動將多達五萬八千家企業從私人手中收歸國有──從酒吧、餐館到零售店和街頭小販的手推車,無所不包。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年間推行共產主義的目的是一勞永逸地戰勝過去,實現徹底和不可逆轉的變革。
但事情還不僅如此。革命者們認為,與過去的決裂不僅發生在社會層面,也發生在個人層面。隨著革命對社會基本結構的改變,人們自身也將發生變化。社會關係將徹底改變,個人與工作、與金錢、與他人、與自己的關係也將發生變化。在古巴革命中,這一觀點的主要支持者是切.格瓦拉,這位阿根廷醫生在墨西哥參加了斐代爾.卡斯楚的革命,跟隨革命來到馬埃斯特拉山脈,來到哈瓦那擔任工業部長和國家銀行行長,並最終去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推動其他地方的革命。在一九六五年,格瓦拉在新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撰寫了《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Socialism and Man in Cuba)一文,闡述了實現真正共產主義的途徑。他寫道,「正在形成的新社會必須與過去展開激烈的競爭。在向這個未來新社會過渡的過程中,過去尚未消亡。這是會致命的。」對格瓦拉來說,與過去的鬥爭無處不在,甚至發生在個人內部。為了實現共產主義,人們必須戰勝自己的過去,採納全新的「價值尺度」。人們必須重生,象徵性地重生為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
格瓦拉是根據他對古巴革命的深刻了解和體驗寫這篇文章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所描述的事是否真的在古巴發生了?當他們周圍的國家發生變化時,古巴人是否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古巴人的內心是否發生了變化?他們變成了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了嗎?革命與人類生存中最私密的領域有著奇妙的關係;革命會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最不可能的領域。無論有產者、舊政權或美國政府如何抵制古巴革命,但是在家中、在幽靜的臥室、在熟悉的餐桌上,過去的一切都要發生革命,這些地方是舊有事物的抵抗最為激烈的地方。在這些領域,即使是那些為革命喝彩的人,有時也得為改變自己而痛苦掙扎。
新政府知道,要建立一個具有新價值觀的新社會,兒童是關鍵。用切.格瓦拉的話說,他們是「可塑的黏土,用他們可以塑造出沒有任何舊缺陷的新人。」革命政府在一九六○年宣布建立免費的國立托兒所,旨在為婦女提供更多走出家門的機會,同時培養出「更先進的青年」──革命青年。第二年,共產黨成立了一個兒童輔助俱樂部,名為「先鋒隊」,旨在向六至十四歲的兒童灌輸熱愛祖國和革命的思想。同年,卡斯楚將教育國有化,關閉了所有私立學校。政府還在農村建立了寄宿學校,將傳統學科、社會主義價值觀薰陶和農業勞動結合起來。到一九六七年時,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高中生曾在這些寄宿學校就讀。
所有的這一切對古巴父母來說都是全新的,有些父母擔心這樣會出問題,於是便沿襲了過去的作法。傳統上,子女的價值觀是來自父母的言傳身教,而不是政府;子女何時離開家庭是由家庭決定的,而不是由國家決定的。一些父母認為,新學校和新計畫表明國家急於干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私人關係。一些人甚至說,政府將把孩子們變成反對自己父母的間諜。關於兒童將被從父母身邊帶走,並運往蘇聯接受思想灌輸的傳聞甚囂塵上,這導致一些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獨自送出了國。從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有一萬四千名學齡兒童在「彼得潘行動」(Operation Peter Pan)中離開古巴前往了美國,這是西半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有組織的無人陪伴未成年人的移民活動。
在一九六一年的掃盲運動中,政府和古巴兒童之間也出現了緊張關係。掃盲運動的目的是掃除文盲(古巴文盲率超過百分之二十),因此掃盲計畫大受歡迎。幾十年來,掃盲一直是古巴進步政治綱領的一部分;在一九三○年代末時,巴蒂斯塔本人就曾帶頭開展了掃盲運動。但是,如果說普及識字是一個長期目標,那麼革命政府則是透過新的手段和完全不同的規模來實現這一目標。教師手冊和學生早期讀物透過教授革命內容來傳授知識。在這些書籍中,M代表馬蒂(Martí),R代表勞爾(Raúl)。F代表信仰(Faith)、步槍(Fusil)、斐代爾(Fidel),或者三者兼而有之。簡單的陳述句講述了土地改革的故事。掃盲運動不僅僅是掃除文盲的手段。它也是一個政治工程。它給農民上了新的政治課。它動員並吸納了大批年輕人,他們不僅是教師,還是革命的生動化身。
在古巴的約七百萬居民中,約有一百二十五萬人作為教師或學生直接參與了這項運動。一年內,約七十萬古巴人學會了讀寫。近三十萬人自願教農民識字,其中許多人前往了島上最偏遠的角落。如此多的年輕人自願參加到這項運動中,以至於政府將他們組織成了特別青年隊,擁有超過十萬五千名成員。其中約百分之四十八的人的年齡只有十五至十九歲,另外的百分之十只有十至十四歲。女孩的人數略高於半數,其中一名教師年僅八歲。沒有自願參加教學或學習的古巴人也以其他的方式參與到其中。為了讓教師能夠參加運動,大多數學校停課八個月。不能去教書的母親們自願整天看顧突然閒下來的孩子們。其他人則在工作崗位上頂替那些離開學校崗位的教師。人群歡呼雀躍地歡送掃盲工作者;志願教師們手持巨大的鉛筆遊行,這是他們自己版本的斐代爾步槍。新脫盲的農民在節日和公開的畢業典禮上接受國家的表彰。
然而,儘管掃盲運動聲勢浩大,但在民間,人們對其影響的感受可能最為強烈。農民們向教師們敞開了家門──為他們提供食宿,為他們洗衣服,與他們建立聯繫。絕大多數教師都是年輕的城市教師,他們突然與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在完全陌生的生活條件下,有時甚至很不舒服。每當一位充滿希望和理想的年輕教師離開時,他們都會在家中與家人進行多次交談。許多家長為看到自己的孩子參加如此崇高的計畫而感到自豪。但古巴父母對子女的要求也很嚴格,尤其是女孩。父母不允許家中的女孩就這樣離家,這種壓力迫使意志堅定的青少年會在文件上偽造簽名,並將自己的計畫隱瞞到最後一刻。一位十五歲就加入掃盲隊的年輕女性後來回憶起她的親戚是如何反對她的:她的母親怎麼能允許她「孤零零去天知道在哪的地方,在沒有自來水和電的鄉下和天知道的什麼人生活?」頭腦發熱的年輕女孩們一再被家人耳提面命,像她們這樣年齡的女孩不能離開家。家長們不禁要問,誰來保護自己的女兒免受農民或其他教師的性挑逗呢?反對者開玩笑說,如果說一九六一年是教育年的話,那麼掃盲運動將使一九六二年變成生育年。古巴革命讓父母變得十分緊張,尤其是關乎自己的女兒和性的方面。
諷刺的是,當城市青少年因下鄉問題與父母發生衝突時,年輕的農村婦女卻因進城問題與父母吵得不可開交。政府將農村女孩送到哈瓦那的安娜.貝當古學校(Ana Betancourt School)去,讓她們在這裡學習縫紉、閱讀並接受政治教育。這所學校是旨在教育(或再教育)婦女的更廣泛計畫的一部分。其他學校將女傭和妓女重新培訓為司機、會計和打字員。新學校的農家女被安排住進那些前往邁阿密的古巴人留在身後的米拉馬區的豪宅裡,她們還會在著名的豪華國家酒店會議室裡上課,該酒店曾接待過約翰.韋恩(John Wayne)、溫斯頓.丘吉爾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等名人。現在,它將幫助政府重塑農家女的形象,同時也讓農家女在遠離父母的環境中重塑自我。要培育新人,讓她們遠離革命前的年代成長的父母將容易得多。
正如革命試圖塑造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一樣,它也希望塑造丈夫與妻子之間的關係。革命對古巴男性的一切期望──在保衛革命委員會中任職、參加民兵或志願勞動,這些事項也同樣是對古巴女性的期望。但是,隨著婦女在家庭以外的活動越來越多,傳統的家庭角色在新義務和新期望的重壓下變得不堪重負了。
古巴婦女聯合會成立於一九六○年,這個組織的任務是監督一項旨在讓更多婦女加入勞動力大軍的大型社會運動。它的目標是每年招募十萬名新女工。事實上,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間,有超過七十萬名婦女加入了勞動大軍。但舊有的社會價值規範阻礙了她們成為勞動力。在這一時期開始外出工作的七十萬人中,只有約二十萬人在第一年後繼續工作。對於大多數離開勞動力市場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她們認為外出務工與家庭義務有所衝突。這是一個大家都熟悉的糾葛:婦女在家庭以外的有償工作和家庭中的無償工作之間的轉換。但在革命的古巴,婦女不得不面對一些人所說的「三班轉換」,也就是再把政治工作的義務加入進來。這種「三班轉換」成為革命電影和報刊的主旋律,常常引發人們熱烈討論新出現的革命現實與頑固的性別角色的舊觀念之間的鬥爭。
也許這就是切.格瓦拉之前就已經預見到了的衝突,是過渡時期的副作用,在這個時期,新秩序已經開始出現,但舊觀念尚未消亡。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在兒童問題上一樣,國家進行了干預。國家設立了為期十八週的帶薪產假,隨後是為期一年的無薪產假。免費的日托中心部分是為了讓婦女騰出時間工作。職業婦女還能享有其他的福利,包括在商店購物時可以不排隊。儘管如此,政府知道這些制度變革是不夠的。古巴男性也必須做出改變。
革命政權並不迴避實現這一目標的努力。在一九七五年成為法律的《家庭法》就是最顯著的例子。該法的目的是在「男女權利絕對平等」的基礎上鞏固家庭。它將婚姻定義為「建立在雙方權利和義務平等的基礎上」。這意味著雙方都有權外出工作(或學習),並有義務在工作中相互支持。該法明確規定,外出工作並不免除夫妻任何一方在家庭中的工作。它還補充說:「根據社會主義道德原則」,雙方都將參與操持家務和撫養子女的工作。
為了確保這種平等不僅僅是一紙空文,在《家庭法》成為法律之前的幾個月裡,國家號召對其進行廣泛的討論。在一次又一次的會議上,在工作場所和街區協會中,幾乎沒有人願意公開反對婚姻平等原則,也沒有人公開質疑政府在個人關係立法方面的特權。但許多人表示自己的為難。婦女將信將疑地認為這項法律永遠不會成功:國家永遠無法執行這項法律;她們的丈夫永遠不會改變。她們預言,古巴男人不會平等地分擔家務和養育子女的重擔。男人們在會上提出的反對意見無疑加劇了她們的疑慮。一些人說,雖然他們願意「幫忙」洗碗和做其他家務,但他們不願意在院子裡或陽台上晾衣服,因為鄰居會看到他們在做家務。儘管有社會主義道德,但男人們往往認為在公共場合做「女人的工作」是有損尊嚴和丟面子的事。
這種情緒揭示了挑戰的艱巨性。為了賦予法律更多的權力,國家下令將《家庭法》中的「丈夫和妻子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條)納入國家婚禮儀式中(當時幾乎沒有人會去教堂舉行婚禮)。在這個島上的每一個合法的婚姻儀式上,每對伴侶都大聲宣誓平等地分擔家庭、家人和社會主義的責任。隨後,應政府的要求,男女雙方在進入已婚身分之前所說出和聽到的最後一句話,就是要確保家庭內部的平等的誓言。
然而,國家對性別關係的干預並不總是站在解放的一邊。對創造理想共產主義個體──也就是新男人或新女人的關注,有時也意味著一些人需要接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改造。尤其是古巴的同性戀者,這些人成為了最惡名昭彰的革命改造對象之一。關於性別角色和男子氣概的傳統觀念與僵化的社會主義道德觀念相融合,將男同性戀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女同性戀者)視為社會異類,視為舊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殘餘。他們被清除出了大學和其他機構,被禁止加入共產黨,並被普遍譴責為革命之外的人。在一九六五年,政府在農村建立了集中營,將同性戀和其他被視為「反社會」的人改造成「新人」。改造的主要手段是勞動,這也是集中營名稱的由來。它的官方名稱叫作「軍事生產援助單位」,簡稱UMAP。這些集中營由軍方管理,工作人員包括社會工作者和心理學家,他們將強迫勞動與激素和談話治療等做法結合起來。據稱,這是一種為社會主義革命服務的強制性轉化療法。國際譴責和國內的壓力最終導致了該機構於一九六七年被關閉。
革命政府熱中於干預家庭和兩性關係,但它在另一個人際關係領域,即種族的問題上卻步履維艱。在歷史上,種族隔離在革命前的古巴並不像在美國那樣猖獗和僵化。儘管如此,私刑事件還是時有發生;三K黨(Ku Klux Klan)的規模也不小,公共場所有時會出現試圖將人們按種族分開的實體痕跡。在我母親長大的農村小鎮裡,人們會用繩子將唯一的舞廳分為黑人區和白人區,但白人男子可以隨意無視障礙,與有色人種女子跳舞,或確保他們的非白人女兒與白人男子跳舞。在省會聖克拉拉,中央公園的長廊分為白人區和黑人區。種族歧視也是結構性的。私立學校拒絕黑人兒童入學。就業中心刊登的招聘廣告上會要求「相貌端正」的工人,這個詞就是白人的委婉說法。幾乎所有的社會學指標──教育、收入、預期壽命都表明,非洲裔古巴人遭受著制度化的種族主義的影響。
當革命者在一九五九年上台後,黑人活動人士和知識人堅持認為,革命不能僅僅透過擱置來解決「種族的問題」。革命需要大膽而明確的反歧視政策。他們的許多要求由來已久,但一九五九年的黑人活動人士們希望革命政府能夠和以前的政府不一樣,能夠實現這些要求。起初,革命領導層似乎對此表示同意。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剛剛掌權的斐代爾.卡斯楚在一次勞工集會上直接談到了這個問題。他長篇大論地反對就業中的種族歧視,認為這是最殘酷的形式,因為它剝奪了人們謀生的權利。但隨著演講的深入,斐代爾開始闡述社會生活中的歧視問題。他提出的解決方案與切.格瓦拉提出的解決方案如出一轍,就是透過教育,都是為了消除過時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如果所有古巴兒童都能在良好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那麼他們就能在課餘時間一起玩耍。事實上,國家希望所有人都能在一起玩耍,進行社會交往。因此,國家還將建立社交俱樂部、娛樂中心和其他場所,讓古巴人──無論其種族如何,都能一起娛樂。看起來每個人都鼓掌了。
然而,集會結束後,許多古巴白人表示反對。很少有人為工作歧視的做法辯護,但許多人質疑斐代爾為何要在這樣的基礎上談論整合其他更私人或更社會化的空間。社交俱樂部是私人事務;決定孩子和誰一起玩是父母的事。批評者似乎暗示,在私人領域,種族壁壘沒有問題,當然也與國家無關。卡斯楚的講話引起了強烈的反彈,以至於他不得不收回成命。僅僅三天後,他又在國家電視台上發表講話,以紓解部分不安情緒。在譴責種族歧視的同時,他現在似乎接受了批評者提出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區別。「我並沒有說我們要開放高級俱樂部,讓黑人去那裡跳舞或娛樂。我沒有這麼說。人們想和誰跳舞就和誰跳舞……想跟誰社交就跟誰社交。」執政三個月後,更重要的是保持團結,而不是過於明確地堅持古巴社會一直以來的棘手話題。
這一時刻決定了政府在未來幾十年中處理種族問題的方式。自始至終,國家都在所謂的私人領域迴避種族問題。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它奉行有利於窮人的種族盲目政策。由於窮人中的黑人比例過高,這些政策將使非洲裔古巴人受益,而國家無需關注種族問題。為了解決工作場所的歧視問題,古巴摒棄了種族配額的想法,並於一九六○年建立了一個全國求職者登記冊。登記冊不僅包括潛在工人的技能訊息,還包括其家庭收入、經濟需求等訊息。有職位空缺的雇主不會直接招聘,而是會通知勞動部,勞動部會根據登記冊提供的訊息填補這些職位,而不會了解求職者的種族甚至姓名。為了解決公共場所的種族隔離問題,政府重新設計了空間,以消除實體上的隔板。例如,聖克拉拉主要公園長廊上分隔白人和黑人的花槽就被拆除了。改變物理空間將改變人們的習慣,而改變人們的習慣最終將改變他們的態度和價值觀。
作者在古巴出生,在美國長大,自1990年以來,她定期前往古巴進行研究,現擔任紐約大學歷史學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研究教授。她是《叛亂的古巴:種族、國家和革命,1868–1898》(Insurgent Cuba: Race, Nation, and Revolution, 1868–1898)的作者,該書獲得了2000年的伯克希爾圖書獎(Berkshire Book Prize),是該獎項在歷史領域中首部女性著作;以及《自由之鏡:革命年代的古巴和海地》(Freedom’s Mirror: Cuba and Haiti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該書獲得2015年由耶魯大學頒發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獎(Frederick Douglass Prize)及美國歷史協會的多個獎項。她也定期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山丘》(The Hill)、《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等刊物發表專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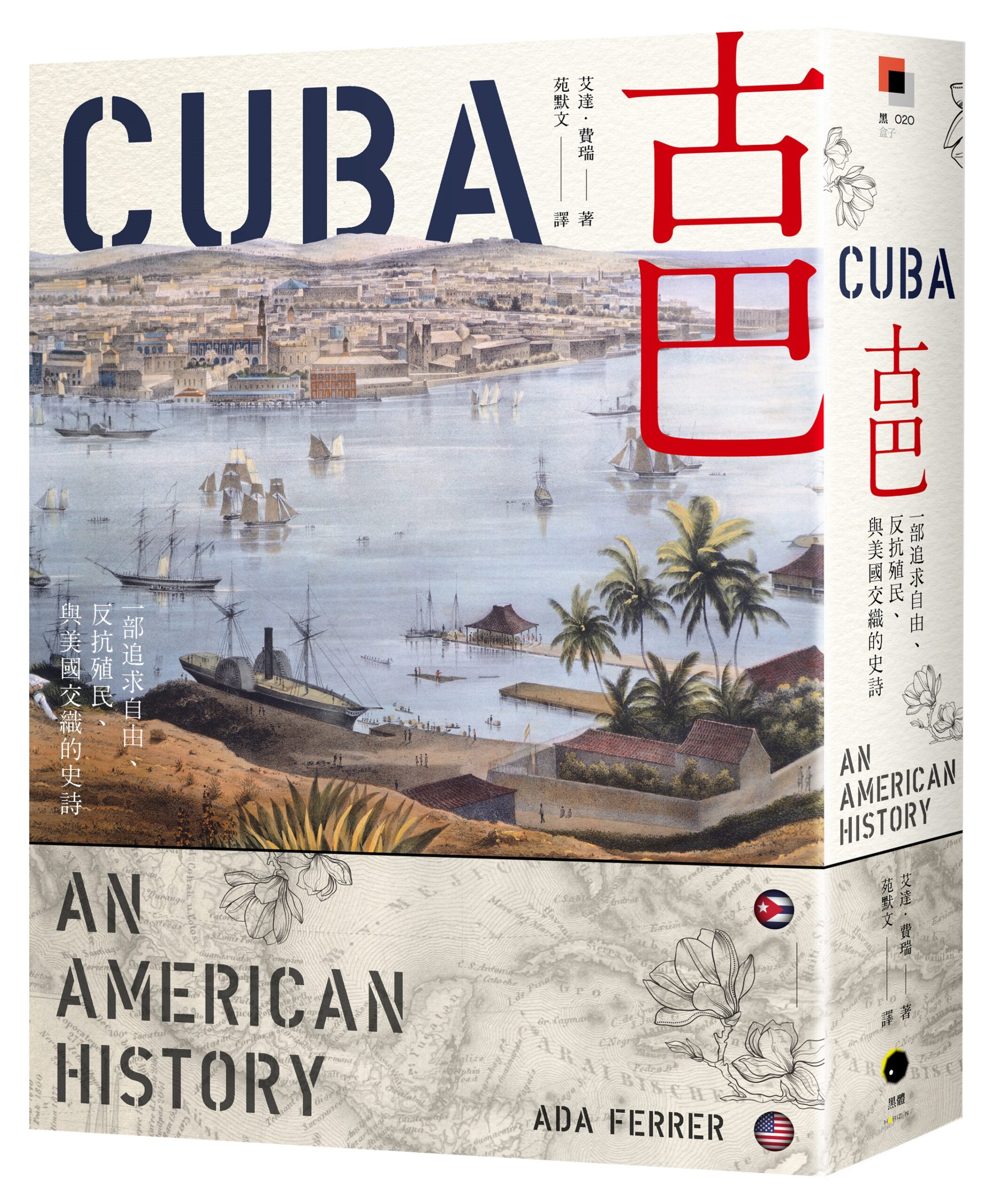
書名:《古巴》
作者:艾達.費瑞(Ada Ferrer)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1月
- 【書摘】《絕不讓步:龐培歐回憶錄》 - 2024 年 5 月 9 日
- 【書摘】《民族的虛構:建立在想像上的集體認同,如何成為現實的族群矛盾?》 - 2024 年 5 月 3 日
- 【書摘】《拆解反動修辭的大師:赫緒曼思想傳記》 - 2024 年 5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