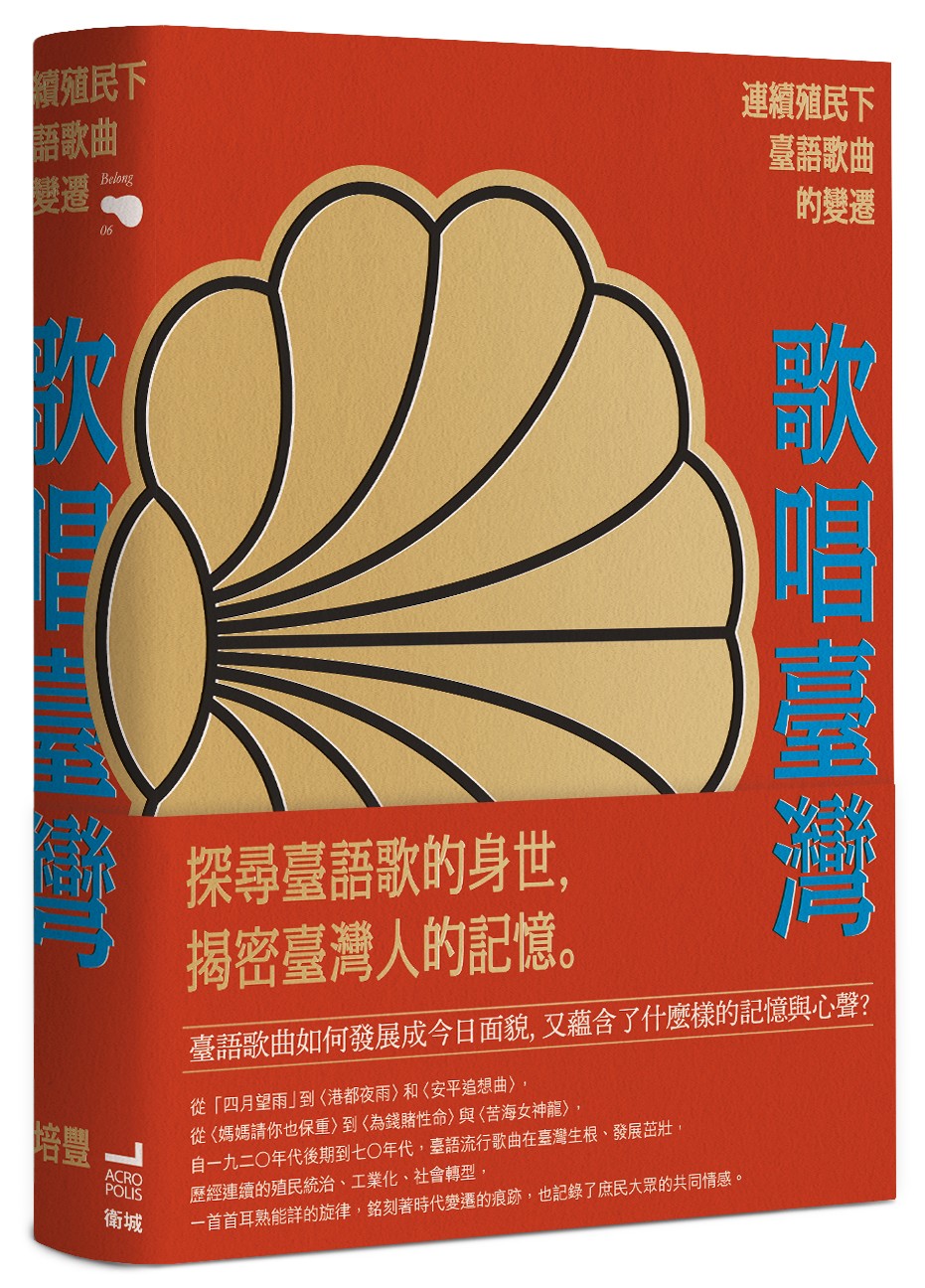
五、陷入崩壞狀態的臺灣農村
(一)農地改革、農村凋零與〈思念故鄉〉
1950年代初期在臺語流行歌曲空窗期即將進入尾聲,流行歌曲工業正好要復甦之際,臺灣又出現了別一個重大社會變遷。這個社會變遷發生在占臺灣人口數最多的農村,起因乃是國民黨的農村政策。
日治時期官方將殖民經濟定調為「工業日本、農業臺灣」,臺灣總督府為配合日本產業所需,大力發展米糖經濟使得臺灣農業不僅能自給自足,並有餘裕維持出口景況。不過到了戰後,曾經是日本帝國富饒寶庫的臺灣,竟然開始缺糧(柯喬治2003: 83)。除了前述二二八事件之前的掠奪,以及為了因應中國內戰之需的輸出外,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失利所陸續帶來約120萬外省人,幾達當時臺灣人口數20%,也是戰後臺灣缺糧的關鍵因素。為了解決這些激增人口和食糧壓力,國民黨政府進行了一連串的農村改革。而這些改革政策包含1949年的三七五減租、1951年的公地放領以及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等。
臺灣生產的主要農作物為稻米、蔗糖;而農家身分有三種,亦即自耕、半自耕及佃耕。整體來說,三七五減租實施後佃農對地主繳納的地租,以全年收穫量的37.5%為上限,為此其負擔的租稅確實降低了不少;但縱使如此,佃農支配所得卻反而大幅下滑。不僅如此,「戰後全體農家平均可支配所得從戰前的178.74 圓降為155.63元,且三種農家也都下滑。」(原文照引)而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其主要因素之一是耕地面積的縮小所致。在1948年之前,台灣農地的供需大概維持在平衡的狀態,但是當地主們聽到要進行減租政策時,便開始拋售土地。土地的供給量一下子變成是需求量的兩倍,這造成農地價格的暴跌與農地移轉的增加。而大量拋售土地的結果,更導致土地的零碎化以及農民耕地面積的縮小(葉淑貞2017: 72-84)。耕地面積的縮小也影響農場的技術效率及配置效率,進而影響農場的經營效率。
總體來看,三七五減租之後佃農的生活水準並沒有提高很多,但負債的佃農比率反而自18.7%升到20.2%(王宏仁1999: 23)。
第二階段的改革是公地放領。在1947年政府擁有超過全臺可耕地的20%,這些土地大部分是沒收日產而來的,其中台糖公司更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從1949到1953年,政府賣出了34.7% 的公有地,不過這公有地放領政策的規模並不大。相較而言,對於農家或臺灣社會的影響有限。
第三階段的改革則是所謂的「耕者有其田」政策。這項被認為對臺灣造成非常巨大之職業結構變化的政策,其實施的背後潛藏著掃除地主階級在鄉村地區所具的威望和影響力,把農民納入政治上的盟友以避免共產黨的滲透等政治盤算。只不過以結果來看,耕者有其田政策雖然幫助農家取得土地,但佃農在轉換為自耕農的過程中必須先償還十年的貸款,尚需負擔全部水租和土地稅。這讓原本便貧困的佃農其財務負擔更為加重,為此領地農民總負擔反而超過領地前的三七五地租(鄧文儀1955: 380-381)。
耕者有其田立意甚佳,然而由於財政拮据等問題,1950年代政府在收購這些土地時,並不是以現金來向中小地主給付所收購的土地價格,而是以債券及股票來抵付。但問題是因法令制度規定,這些債券及股票在當時並無法進行交易變現。為此,一些中小地主只好私下拋售債券及股票,而這又致使債券及股票的價格低落,造成中小地主生活困頓(薛化元2016: 73-101;洪紹洋2016: 103-148)。
戰後初期,臺灣社會基本上存在著外省籍軍人/官僚、外省籍資本家、本省籍地主與資本家、佃農與自耕農、雇主與自營商、勞工等數個階層。在耕者有其田政策中受到最大打擊的是中小地主。因為對本省籍大地主來說,日治時期其經常擁有因經營產業或銀行等獲得其他收入而不單靠地租過活,因此農地改革不會對他們造成致命性傷害。但中小地主階層則不然,在三七五減租實施前,農地價格暴跌。耕者有其田實施後,這些中小地主又無法像大地主般擁有其他收入。因此,當這些僅依賴收租來維生的中小地主,在土地被徵收之後,生活便頓時陷入困境,其收入甚至可能低於大佃農。在一連串農村土地改革下,許多地主只好賣掉土地不再經營農業。
就如同1950─1951年政務委員蔡培火,在巡視全臺向行政院提的報告書中提到:「小地主自三七五減租後,不能收回自耕,向日猶可經商,今則經商困難又無田可自耕,生活極為艱苦。」(張炎憲2000: 323)而這個結果也造成原本在這些農地上工作的農業工人失業(王宏仁1999: 28)。由於可耕地不足,加上人口的壓力,耕者有其田政策施行後,有越來越多的農民成了農村的剩餘人口,這些無法只依賴農業過活而必須成為工資勞動者,只好找尋非農的工作以補貼家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1955: 54)。
進入1950年代後,除了大地主之外,大量的佃農、自耕農、半自耕農、中小地主等都因為收入減少而成為隱形失業者。根據統計,1950年代的臺灣有70%以上的農家背負債務,他們除了離開農村前往都會從事勞動之外,別無生存之道。而由於承領土地需要十年繳還地價,且地價是以現穀繳還,因此,許多原為佃農的農民便被限制在農村耕作以償還債務。這些人只能透過打游擊的方式從事非農的勞動。根據1952年的調查,有半數的佃農甚至必須出外謀職以求得生計維持(王宏仁1999: 27-28),這一方面使得臺灣社會的職業結構產生巨大變化;一方面也意味著離鄉背井將成為農村的常態。
1950年代農村生活由「平穩」開始走向波動,日治時期原本和緩的人口移動現象開始動搖。這個社會變遷牽動臺語流行歌曲,促使其萌生出新型態的離鄉作品。有別於日治時期那種局限在牛郎織女分離苦痛之表達,新型態作品雖然同樣以離鄉懷鄉為主題,但卻轉而蛻變為一種讓家鄉具像化、美好化,讓思念對象也聚焦在家庭或農村原貌的創作模式。而呈現這個變化的代表性作品無他,即前述1954年曾在白色恐怖中劫後餘生的〈思念故鄉〉。
〈思念故鄉〉
作詞:周添旺
作曲:楊三郎
我騎水牛你來飼鵝山頂吃草溪邊坐
談情說愛好七逃為何失戀心糟糟
可愛的故鄉可愛的山河今日離開千里遠
啊……啊……何時再相會啊……啊……何時再相會
我來播田你來擔秧秧那播落心頭酸
春來秋去日頭長為何你不知田中秧
可愛的故鄉可愛的田園今日離開千里遠
啊……啊……何時再相會啊……啊……何時再相會
我來有情你來有義不驚訕赤不驚柔
只為職業打未成為何心情未分明
可愛的故鄉可愛的家庭今日離開千里遠
啊……啊……何時再相會啊……啊……何時再相會
不同於戰前那種無病呻吟、虛無飄渺的離鄉歌曲,〈思念故鄉〉中的家鄉不再僅因是愛人的居所而令人懷念,形象也不再蒼白模糊,而是一個有山有水、可騎水牛、飼鵝、播田、擔秧等的具體農村。只是如「秧那播落心頭酸」所示,如今農村不再好生活,這些過去美好的田園生活、「可愛的山河」、「可愛的家庭」己「離我千里遠」。
歌詞中的主角深切想要回去那個曾經美好的故鄉農村,但離鄉後依然貧窮的我,卻總是因為職業不順遂而徬徨躊躇。
〈思念故鄉〉出現的時間點和內容暗示我們,1950年代初期經過一場農村土地改革後,農村不再是「平穩」得可以讓農民一輩子安居樂業的地方,而是許多被迫離農另謀生計者之思念對象。雖然不像戰前朝鮮流行歌曲般的痛心悱惻,但〈思念故鄉〉中的鄉愁對於當時的臺灣社會來說,卻是一首有血有肉確實存在且可以引起許多底層民衆共鳴的共同遭遇和感受。
〈思念故鄉〉打破了原本臺語流行歌曲中臺灣人的離鄉樣態,投射出離農者對於家鄉的不捨。然而這首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卻仍充滿著未解之謎,當時被槍決的原作詞者到底是誰,至今仍然不明。縱使在1989年楊三郎仙逝前都已解嚴了,但他終生不再提起這件事。這個事件對他衝擊之大,可想而知。
(二)農村人口的外移和階級的定型化
其實就如〈思念故鄉〉的歌詞所暗示,1951年臺灣的勞工人口為73,7000人,至1960年已達到122,2000人,這急遽增加的近50萬名勞工,多數是農民及其子女。從1956年到1961年間,工資農業工人從農業總人口的0.7%增加到4%,這顯示了當時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在自家的農地耕種,而必須外流出去工作(王宏仁1999: 24)。到了1961年時,農業部門裡頭約有100萬的剩餘人口,這相當於整個農業人口的44%(劉進慶1992: 353),而這些人口為了生活只能離鄉往都市移動。
然而,二二八事件後的臺灣社會百廢待舉,欠缺資本以及全方位要素的生產性、進步技術等條件,因此經濟成長和人口移動並非相輔相成。在一連串農地改革政策後,由於都會並未作好容納這些大量流入都市之農民準備,所以無法提供這些出外人良好的生活條件。為此,流入到城市的人口中有許多是舉家遷移,其大多只能在鄰近的市場勞動維生,當中約有50%的人從事攤販業、理髮業、雜技藝人或被雇用於幫傭、清潔工等第三級產業,能夠找到安定正職者不超過整體流入人口的一半。也由於多數工作屬臨時性質,因此在沒有生活保障的狀況下,1950年代流入都會的至少25萬名臺灣人,被迫過著不安定、顛沛流離的生活,甚至落入到社會邊緣人的預備行列(王宏仁1999:25-29);直到60年代當臺灣經濟起飛後,這批「職業打未成」的剩餘勞動力才逐漸被工業部門所吸收。
事實上,農地改革後的一些資金並沒有大量轉投資到工業、成為工業發展的後盾。三七五減租之後得到好處的佃農由於背負了新購土地的債務,因此他們將大部分增加的所得用在消費上。對於原先就是自耕農的人來講,他們同樣面臨政府租稅增加、土地不足、戰後臺灣人口增加的問題,要轉向其他行業也不是很容易。換言之,不管是原先為自耕農,或是佃農,在農地改革之後的1950年代並沒有相當多的機會往上流動(王宏仁1999: 23-25)。
國民政府來臺之後所進行的農地改革,受到最大影響的則是小地主與佃農。因為在這過程中,大地主由於原本就有相當的專業,也通常是本省籍的資本家,因此他們的地位並沒有多大的變動。中地主也沒有很大變化,因為他們本身在都市地區大都有如農漁會幹事的白領階層工作,所以農地改革只是讓他們更早脫離農村生活。但小地主受到的影響最大,一方面他們保留的土地不足,另方面土地移轉出去的資金又不知往何處投資,只能當成生活的資金讓它逐漸消失。而由於這些小地主缺乏商業技能與資金,要轉業從工、商相當困難(王宏仁1999: 30)。
戰後的農村改革政策讓日治時期原本平穩的臺灣人口狀態,開始出現明顯的流動,而一連串離農、離鄉背井的現象意味著農村開始出現崩壞現象。只是臺灣人口的流動雖然讓職業結構產生變化,但階級幽閉化的現象卻沒有因此而被打破,而教育問題是其中癥結。
教育是促成社會職業及階層的流動的最好途徑。但由於戰後這些小地主與佃農陷入貧困化的困境,而政府對於其子女並沒有實施類似像對待外省人般的教育優遇政策,農村子女甚難有機會得以透過接受較高之教育,以改善其階級地位。因此,戰後外省人的教育程度往往被認為高於本省人。當然,這些家庭也不可能提供資本或工商業的學習環境,讓其子女有機會往另外的方向發展(王宏仁1999: 29)。他們必須等待大環境改善時,才有能力逃脫邊際勞動力的命運。
接受教育的成本包含兩種:支付的教育費用以及接受教育的機會成本。事實上個人的教育成就,除了反映自己努力的結果之外,也投射出接受教育的成本條件(Gary Becker 1975)。如前所述,戰後國民黨政府對於外省人居大多數的軍公教等家庭,進行了許多優遇或補貼措施,這往往被使用來解釋造成本省、外省兩族群在教育成就上差異的原因。
事實上,不同省籍的社經地位之差異,對下一代的教育與職業之影響,卻遠比國家教育補助政策來得更重要。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治政策廣泛影響到各個階層、個人家庭的「市場機會」或「生產工具的擁有」,它影響了大多數本省人的家庭社經地位,並將這些代內與代間的社會流動固定化(王宏仁1999: 4-29)。
進一步地說,1950年前後在前述公務員考試制度的設計、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辨法的制定、社會福利的實施以及一連串農村改革政策下,臺灣的各個階層在國家的政策下不但被形塑出來,並成為各個階層的原初條件(initial conditions)。而這些家庭社經地位的原初條件,決定了戰後本省人、外省人政治經濟地位的差異,並將這些階級結構定型化。這種階級移動的管道的幽閉、僵化現象,明顯的表示在國民黨政府來臺不久後,臺灣社會的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並不十分自由與平等(王宏仁1999: 4)。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階級移動停滯,占人口大部分的農民或女性,也就是一般庶民則像是在牢籠中,過著「平穩」的生活,較缺乏離鄉漂泊的生活經驗。相對於此,戰後初期的1950年代,臺灣社會階級移動停滯的現象依然如故,甚至更為嚴重,但在人口移動上卻發生了重大改變。受到戒嚴令等管制,知識分子離開臺灣到海外發展的機會變得更少,但原本日治時期在自家土地上生活的臺灣農民,卻被迫開始大量流向都市。雖然這些人不像戰前的朝鮮人般,必須離鄉渡海到異國去勞動。換言之,其移動的範圍依然是在臺灣島內,但由於工作機會的缺乏之故,他們必須過著辛苦且不安定的日子。
六、結論
戰後臺語流行歌曲的空窗期,濃縮了戰前戰後臺灣政治、社會、文化變遷的複雜性和重層性,讓這個島嶼詭異的歷史發展和人流軌跡表露無遺。具體地說,臺灣唱片工業的停滯,說明了臺語流行歌曲工業作為殖民時期的大眾文化,是一個壓縮式近代化的產物且充滿著依賴性。而閨怨、文明女系列歌曲的式微,取而代之的苦戀和表達貧困失業作品的出頭,更投射出戰後臺灣人災難式遭遇。
戰後,臺灣人原本以為回歸祖國是場成真美夢,但是二二八事件、戒嚴令與白色恐怖的壓制、殺戮、掠奪、迫害,以及接下來國民黨政府一連串以族群作為國家資源分配的政策,卻將臺灣人推入更深的惡夢—「再殖民統治」。
即便殖民統治之形態具有多樣性,很難一概而論,但其基本上便是少數在軍事上擁有絕對優勢的統治者,對轄下的多數被統治者進行經濟上的榨取、社會上的歧視或政治上的壓制和差別待遇。壓制和差別待遇經常導致被殖民者的階級移動幽閉停滯,而從被殖民者身上榨取來的經濟利益則往往會流用到殖民母國身上。由此觀之,戰後臺灣並沒有解殖民,而是陷入祖國的再殖民統治的政治情境(陳芳明 2011);而這個政治陰影也投射在臺灣農村。
1950年左右在沒有工業化基礎作為支撐的狀況下,一連串農村土地改革的實施,讓本省農民遭受貧窮以及離農的衝擊。臺灣農村崩壞的前兆暗示著我們,類似戰前日本支配下朝鮮人為了生活必須過著離鄉背井生活的情境,將可能出現在臺灣。而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農村變遷,剛好出現在下一波臺語流行歌曲工業蓄勢待發,即將在臺灣社會登場的時候。
作者為臺灣臺北市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日本語日本文化碩士、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博士。曾任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專攻臺灣語言思想史、文化思想史、文學史以及日治時期國語同化政策。著有《「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東京:三元社及臺北:麥田出版社)、《想像和界線: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日本.東京:三元社及新北市:群學出版社)。書名:《「日本人」的界限》
書名:《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
作者:陳培豐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0年12月16日
- 【書摘】《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與社會學觀點》 - 2024 年 4 月 26 日
- 【書摘】《鐵幕降臨:赤色浪潮下的東歐》 - 2024 年 4 月 25 日
- 【書摘】《美利堅國度:十一個相互對立的地區文化史》 - 2024 年 4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