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停留在單一民族國家的羅爾斯正義論

林布蘭這幅畫作原名《弗蘭斯.班寧.柯克隊長及威廉.范.勒滕勃奇副官的連隊》,創作於1642年,是以華麗的細節為特徵的巴洛克風格畫作。18世紀末才改為現在熟知的《夜巡》。不過,《夜巡》的名稱是錯誤的,因為連隊聚集在一起的時間是白天,是厚重的畫料讓其看起來像是晚上;此外,林布蘭創作此畫時,城市自衛隊已不需守衛阿姆斯特丹城堡,日夜都不需要了。這個連隊的集合,主要是要去參加社會活動以及體育比賽。《夜巡》如今成為荷蘭國寶,成為國家認同與團結的象徵,是後來荷蘭人外加上去的。

一、國際正義的艱難與可能
羅爾斯在1999年出版的《萬民法》結尾時,某種程度呈現國際社會合作的悲觀前景。他說:如果不可能有這樣一種其成員縮減自身力量以服膺於合理目標的合理公正之諸民族社會,而人類大致上又是不講道德的,那麼我們可能就和康德一樣,不禁要問「人類到底還值不值得存活在這個地球上」(Rawls, 1999b, p. 128)。而康德的原話是說「如果正義敗亡,那人類就再也不值得活在這個地球」。
事實上羅爾斯在這樣論述時,對於萬民法可以達成國際正義則退至期待政治家(statesman)。對比政客(politician)關心的是下一次的選舉,政治家則是關懷下一代子孫的幸福,為此羅爾斯對政治家如此定義:「應該說政治家是一位理念者,像一位誠信而有德性的個人。政治家們是總統或首相或其他高位者,透過職務展現其典範與領導風格,呈現出力量、智慧和勇氣。他們在混亂危世中帶領著人民」(Rawls, 1999b, p. 97)。在這樣論述之後,羅爾斯緊接著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英國與美國的作為而多所感嘆。或許是迫於希望戰爭盡快結束的期待,在對待可能就要戰敗的德國與日本,英美分別發動了殘酷的德國德勒斯登空襲與日本東京燃燒彈轟炸,以致平民傷亡增加數十萬。由於受限於當時英美政治文化,其對於德日平民沒有太多的同情心與同理心,也因此,期待英國邱吉爾(W. Churchill)與美國杜魯門(H. Truman)謹守戰勝國應有的人道標準,變成只能祈禱領導者的一念之間。而我們看到,羅爾斯的生命後期歷經蘇聯瓦解冷戰結束、成為超強的美國發動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以及紐約遭受911恐怖攻擊後的政治文化氛圍,羅爾斯畢生致力一國之內的公平正義瞬時變得不合時宜,《萬民法》結尾的悲觀透露出國際正義前景的無比黯淡,某種程度也預示了其2002年過世後,隔年英美聯軍攻打伊拉克的人間浩劫。
充滿人治色彩的政治家可遇不可求,但現實上一國之內的社會基本結構要推廣到國際之間的全球基本結構卻還是依舊困難重重。本文即是以晚期羅爾斯相關國際正義論述為基礎,嘗試回應羅爾斯未完成的國際正義論述,設想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期待這樣的「理想構思」可以提供「非理想現實」些許參考。
二、屬於二十世紀的羅爾斯國際正義論述
著名的羅爾斯思想研究者萊寧(P. Lehning)在2009年出版的《羅爾斯政治哲學導論》裡,詮釋了羅爾斯思想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轉變(Lehning, 2009, p. 9-10)。第一與第二階段都是設定一個不與其他世界聯繫的自給自足社會基本結構,其如何達到理性的正義;第三階段才邁出西方社會,思考各個國家之間如何達成國際正義。
第一階段完成於1971年的《一種正義論》,主要討論收入與財富如何公平分配,其理論重心在差異原則(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即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容許,是以如何讓最弱勢者的福祉可以提升為原則;第二階段完成於1993年的《政治自由主義》,羅爾斯認為既然理性多元論是無可否認的存在事實,那麼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如何將各種相互衝突的學說教條、宗教信念,透過公共理性的愈趨成熟,達到共享的政治正義架構。這是從第一階段的道德自律拓展到第二階段的政治自律。而第三階段的《萬民法》,則是期待一種自由與正派人民的國際社會如何達到和平共存的目標。書中還設定「卡贊尼斯坦」(Kazanistan,一個正派的層級制穆斯林民族),如何在國際間理應受到尊重,這是羅爾斯設想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如何繼續向外拓展到與其他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的民族和平共存。
(一)《一種正義論》的自給自足社會基本結構設定
羅爾斯在《一種正義論》第二小節「正義的主題」裡,即設定一個與其他社會隔絕的封閉系統社會基本結構如何公平正義。其文本敘述是這樣的:「首先,我關心的是正義問題的一種特殊情形。我不想普遍地考慮制度和社會實踐的正義,也不想考慮國際法的正義和國際關係的正義(只是在第58小節順便提一下)。……對於國際法來說,也可能需要以多少不同的方式達到不同的原則。如果可能的話只需做到下一點我就滿足了:為一個暫時被理解為同其他社會隔絕的封閉社會基本結構,概括出一種合理的正義觀來。這一特殊情形的意義是明顯的,無須解釋。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推測:我們一旦有了一種對於這種情形的正確理論,藉助於它,其他有關的正義問題就能比較容易處理。只需做出適當的修改,這樣一種理論便可以為別的一些正義問題提供鑰匙」(Rawls, 1999a, p. 7)。
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要旨是,我們現代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應該依據一個公平正義的標準,來制定社會基本結構法則,這個標準是現在與未來的公民代表們,在「無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下一致同意的。而其正義論著述被稱為平等之書,主要在羅爾斯主張的差異原則,強調個人的天賦才能不應屬於個人應得,而應視為社會的共同資產。
而在權利(right)優先於善(good)的契約論傳統下,羅爾斯最終推導出(自給自足封閉社會)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兩原則:第一原則——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原則——社會和經濟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1)在與正義的儲蓄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並且,(2)依繫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為此,羅爾斯為「自由平等博愛」總結表示:自由相應於第一個原則中對自由的最優先強調;平等則是相應於第一個原則的平等觀念,即擁有機會的公平平等;而博愛則落實在第二個差別原則的追求。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把傳統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具體落實在正義兩原則的民主解釋上(Rawls, 1999a, p. 91)。
羅爾斯認為在證成正義兩原則過程中,可以不再需要借助神學或形上學來支撐正義觀念的各項原則。在書中羅爾斯表示︰由此可以看出,諸如柏拉圖《理想國》中的「高貴的謊言」金銀銅鐵(第3卷第414-415頁)這樣的方法被排除了;為支持一個信仰否則就不能存在下去的社會制度宗教辯護,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那種辯護也同樣如此(Rawls, 1999a, p. 398n)。事實上,當羅爾斯非常有自信地說著「不需要借助神學或形上學」時,他卻嚴重輕忽了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國際間往來直線上升,特別是網際網路幾乎連結了整個世界。
因此這個屬於二十世紀的羅爾斯《一種正義論》是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它主要總結1960年代歐美平權運動經驗的正義論觀點。而此一屬於西方社會時空的觀點,首先遭遇挑戰的是非西方社會對第一原則「自由優先性」的質疑。因為對許多東方人來說,經濟上的溫飽要比政治上能否自由更重要。自由優先性對許多東方人口稠密的國家,像是天邊彩虹雖中看但卻不能當飯吃。近600萬人口的新加坡,其人口總數都超過芬蘭與挪威,因此該國政府對政治自由的管控,竟被多數新加坡人所接受。
1973年哈特(H. L. A. Hart)在〈羅爾斯論自由與其優先性〉提出對羅爾斯「自由優先性」的商榷。哈特的質疑其實也正是人口普遍眾多的亞洲社會對自由優先的質疑,社會穩定與經濟溫飽在許多東方社會被視為最重要議題。以新加坡李光耀的執政經驗,其所形成的所謂新權威主義論述,某種程度正是哈特此一觀點的實例。
羅爾斯對哈特的回應,主要訴求對理想「道德人」的期許。在1990年新版的《一種正義論》序言裡,對於人的平等自由優先性,羅爾斯訴諸人之所以為人的兩項道德能力,分別是:正義感的能力(capacity for a sense of justice)與善觀念的能力(capacity for a conception of the good)。羅爾斯的回應對東方社會來說仍是理想與現實的擺盪。對此作者認為,應讓這兩原則並列,由各個社會設定哪一原則優先、哪一原則在後,或者兩個原則同時並行;但不能在經濟一定溫飽後,無限期地推延政治自由民主化。然若以新加坡與中國的經濟優先發展為例,我們發現主政者(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與中國共產黨)到目前為止都無意落實另一自由優先性原則的趨向,反而透過經濟發展的成果鞏固其未來得以繼續長期執政的數位極權政策。羅爾斯堅持自由優先性的道德人論述,於今看來更顯其深思熟慮。
(二)《萬民法》中不接受全球差異原則的說明
羅爾斯的《萬民法》充滿著對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作為與至今國際作為的深切反省(Rawls, 1999b, p. 53, 95)。不過,面對博格(T. Pogge)在1994年提出的全球平等主義原則,主張將分配正義推到國際社會;羅爾斯卻依舊堅持只能在一國之內,並認為因為各國徵稅與人口成長率不同,將會造成國際間無法相互接受的後果(Rawls, 1999b, p. 115-118)。
根據萊寧的整理,羅爾斯是基於以下三個理由拒絕了「全球差異原則」:第一是,在國際層次上的「原初立場」(the original position)中,不會達成任何針對全球差異原則的協議。第二是全球差異原則錯誤地假定,會有一種立足於全球基本結構的全球性社會合作體制。第三是,各國政治文化的不同,將使全球差異原則無從落實(Lehning, 2009, p. 201)。而本文將分別以人性、政治人性以及宗教信仰嘗試進一步闡釋萊寧整理的三個理由,並清楚理解推行全球差異原則將會是何等的艱難。
首先是人性中階層主義(支持右派政黨,如美國共和黨選民中有一定比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凌駕於平等主義(支持左派政黨,如美國民主黨選民支持黑人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的傾向,依舊是人類社會的大多數。雖然近幾年一國之內的平等主義呼聲日益升高,但要在國際層次上的原初立場中,達成國際平等主義協議是相當困難的,以平等主義的巴黎氣候協定為例,依舊是沒有拘束力的國際輿論呼籲。反觀階層主義的國際貿易協定,其強制規定則強而有力許多。
階層主義以大自然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論述依據,認為扶持弱勢等眾多福利政策是違反自然法則,終究助長不勞而獲風氣反而妨害人類長遠的進步。另一方面平等主義則雖以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彰顯人之所以為人的可貴,但從1960年代以來平等權利要求總是高於平等義務的自許,正如早先1906年托爾斯泰在其〈論俄國革命的意義〉指出的,西方民族代議制運作的結果是,他們只看到自己要的權利,而最終甚至將自己民族利益建立在其他弱小民族的痛苦剝削上。也因此,西方普選制的結果是,以前要供養的是少數王公貴族,而今卻是一整個資產階級的成千上萬小帝王(汝龍譯,2000(15),頁503)。
其次是政治人性的幽暗,讓全球性社會合作體制幾乎仍是漫漫長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全世界最能理解被迫害的民族莫過於猶太人,納粹集中營的煉獄幾使他們種族滅絕。然而今天由猶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卻在近70多年來,殘酷對待其境內與周遭的巴勒斯坦人。一個最近才遭受有計劃屠殺的悲慘民族,理應最能體會家破人亡的痛苦,沒想到在達成自己建國目標之後不到幾年,受苦者瞬間變身為加害者,苦難的一方換成巴勒斯坦人。讓人難以相信的事實是:發生衝突的地方,幾乎全都是原先聯合國劃給巴勒斯坦人的約旦河西岸、迦薩走廊與黎巴嫩南部邊境。而這些區域在國際協定中,是明定給巴勒斯坦人合法居住的僅存區域,但卻也在1967年後被以色列非法佔領至今。
第三則是宗教信仰的差異,讓原本語言不同的多元政治文化更難以促成國際合作。中世紀十字軍東征,讓整個大基督教世界團結起來對抗伊斯蘭教,而這也是歐盟長久以來拒絕以伊斯蘭文化為主的土耳其加入的根本原因。
而當少了共同的宗教敵人之後,大基督教世界在冷戰期間明顯分為羅馬公教(包括曾宗教改革的新教)與希臘正教兩大分界。長期受到蘇聯掌控的芬蘭首都赫爾辛基,有著路德派新教的赫爾辛基大教堂與希臘正教的烏斯佩斯基大教堂,兩個大教堂相距不遠,但卻是最北的兩大流派分界起點。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與蘇聯在歐洲冷戰的分界線,正是沿著這分界起點從北往南分為美國勢力範圍的西歐與蘇聯勢力範圍的東歐,一直來到巴爾幹半島的前南斯拉夫。
而冷戰以至最後蘇聯的瓦解,正是從非希臘正教的波蘭團結工聯的抗爭與東德柏林圍牆倒塌起始,而波羅地海三小國(希臘正教占少數的蘇聯管轄區)的立陶宛於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布獨立,隨後引發多米諾效應,其他加盟國紛紛響應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而目前的烏克蘭東西分裂情況與俄羅斯普丁(V. Putin)直接控制克里米亞,某種程度依然呈現歐洲兩大宗教流派的內在緊張情勢。
除了以上萊寧整理的羅爾斯不接受「全球差異原則」的三個理由進一步說明外,近十年由於敘利亞戰亂引發的人道危機,更加深西歐對外來移民的恐懼,原本西歐政治上的左右派政黨紛爭,如今重新洗牌成左右派聯盟起來抗衡反移民的極右派新政黨。
(三)從康德永久和平論延伸的反對世界政府論述
羅爾斯依然秉持著康德〈永久和平論〉的反對世界政府觀點(政府之規模越是擴大,法律失去的力量就越多),因此世界政府「要不是變成全球性的專制統治,就是變成一個脆弱不堪的統治帝國」(Rawls, 1999b, p. 36)。然而,在今天網際網路愈加讓世界成為一體的趨向,排除世界政府選項似乎愈來愈不切實際。特別是今天世界貿易組織(WTO)推動的國際貿易,已經來到人與人跨國移動的服務業之後,事實上當前許多迫切課題,早已不是任何單一國家所能獨立面對。然而我們卻看到現實世界的發展是,最像世界政府的聯合國在1973年成立了「聯合國跨國公司研究中心」(UNCTNC),希望能對跨國企業進行追蹤研究;然1993年卻在美國政府的要求下,聯合國關閉了這個研究中心。
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曾經說了一個故事──亞歷山大大帝擒獲了一個海盜,問這強盜說:「你怎麼有膽子在海上興風作浪?」那海盜居然反將一軍回答:「那你又怎麼有膽量在整個世界興風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稱為海盜;而你有一支海軍,所以被稱為皇帝。」因此法學者格倫農(M. Glennon)曾表示:整個國際法體系只不過是一大堆空話,想使權力統治服從於法律規範,只能算是一種偉大的嘗試(Chomsky, 2004, p. 13)。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英國首相邱吉爾即認為未來世界的完美藍圖是,世界政府必須為富足國家所管理,因為這些國家想要的東西都已經不虞匱乏,反之若落入飢荒國家則會造成永久危險。因此,在後來成立的聯合國除了確立五大強權國家的安理會否決權外,其入會是有資格限制的選擇原則。但選擇原則最後變成普遍原則的原因是:1953年韓戰結束後,美蘇兩大超強為爭取亞、非、拉丁美洲新興國家支持,紛紛積極同意新興國家加入聯合國。1955年,同意讓16國入會,總共達到76個會員國;1960年,又有17國入會,數目來到100個會員國;一直到1960年代結束,又共有25國入會,聯合國的總會員數在那時就已經來到125國(中央社,2002,頁605)。
從以上過程看出,由於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加入聯合國之後,其在數量上掌握聯合國的多數優勢。他們在聯合國裡要求國際間更公平的對待,更可說是對原來西方強權的挑戰。顯然這時的聯合國已不是如邱吉爾所說的由富足國家管理,反而是由他所認為的飢荒國家掌控,而處於危險狀態之中(Chomsky, 2000, p. 7)。於是往後的發展是,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國家開始亟思反制:一方面由美國帶頭長期積欠聯合國會費,讓聯合國處於財政赤字運作困難;另一方面則以G7能掌控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如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邊緣化聯合國的角色。
不過,聯合國轄下的荷蘭海牙國際法庭,其歷次判決結果雖沒有強制力,但對形成中的世界輿論,卻愈來愈有重大指引力。
我們看到早先在二十世紀八零年代,國際法庭做出譴責美國對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的裁決時,當時雷根政府的回應是:一方面進一步升高戰爭層級,對尼加拉瓜非軍事目標也進行攻擊;另一方面則告訴大家,國際法庭已成為對美國充滿敵意的論壇,它本身的公信力已經玩完了(Chomsky, 2000, p. 3-4)。2002年8月美國國會甚至通過「美國公務人員保護協議」,這個被稱為「入侵海牙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在有美國人受到國際法庭審判時,以武力入侵荷蘭。不過即使有此「入侵海牙法案」的插曲,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國際法庭在引導國際輿論的影響力明顯與日俱增。2004年國際法庭做出釋義:主張以色列區隔約旦河西岸的「隔離牆」違反國際法,而且所有國家都有義務不承認豎立此牆帶來的不合法局面。2016年7月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下,仲裁庭宣布支持菲律賓在南海相關問題上的幾乎全部訴求。仲裁庭一致裁定,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中國對南海自然資源不享有基於「九段線」的所謂歷史性權利。仲裁庭還認定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陸,帶給環境不可挽回的損失,要求中國立即停止該活動。另外,2020年11月5日川普頒布行政命令,向部分海牙國際刑事法庭人員實施經濟及旅遊制裁,以阻止其對涉入阿富汗衝突的美國軍人進行司法追究;而歐盟立即回應,對美國的制裁令嚴重關切。
由於目前世界僅存的超級強國美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會定期改選的民主國家,因此美國選民的選票抉擇是天秤上最重要的砝碼。特別是在世界政府尚未成立之前,美國選民究竟是選擇單邊主義或多邊主義的總統,對接下來四年的國際政治走向實為重要關鍵。
作者為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學士、輔仁大學西洋史碩士與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在新聞界擔任記者多年。
1999年2月起在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擔任政治學的教學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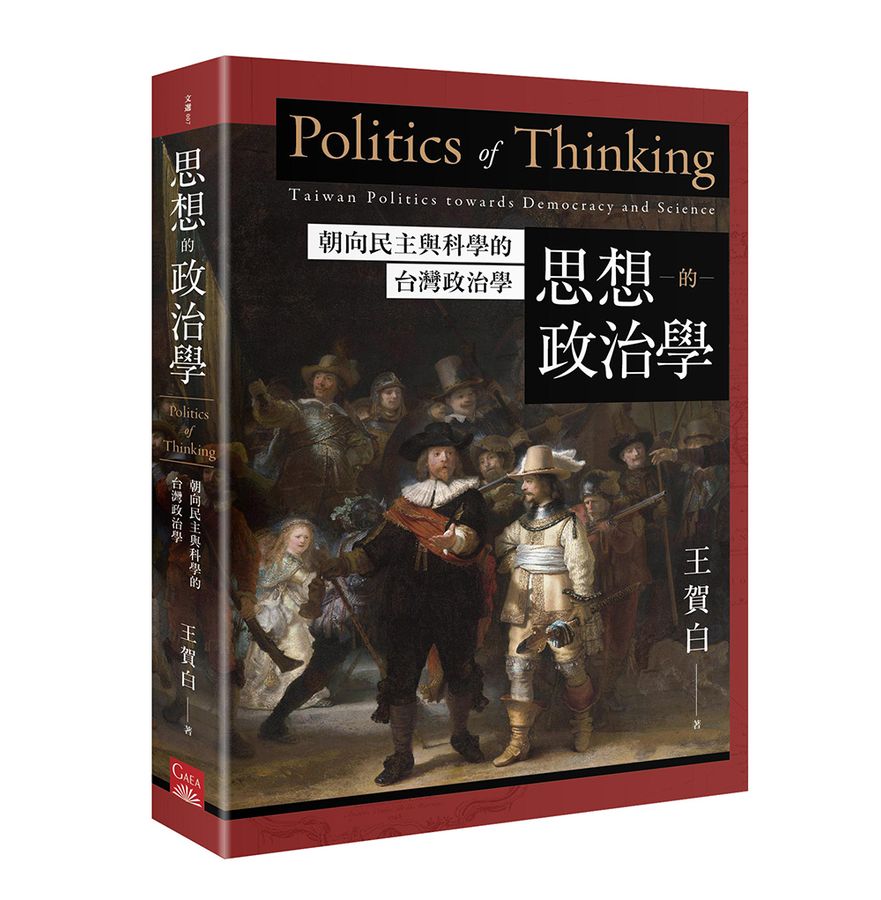
書名:《思想的政治學──朝向民主與科學的台灣政治學》
作者:王賀白
出版社:蓋亞文化
出版時間:2023年10月
- 【書摘】《思想的政治學──朝向民主與科學的台灣政治學》 - 2023 年 11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