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重述臺海紛爭
臺灣的地理與戰略重要性
表述:臺灣對北京為何重要?
很大程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功傳播其所喜好的言論和概念尺度,藉以表述臺灣地位問題。主導的官方敘事源自一套民族主義觀點,強調「一個中國原則」至上,這套國家與國土統一的表述,反映出中國共產黨自我正當化的努力,要在帝國主義導致中國分裂之後,成為統一中國的政黨。因此,該黨反對臺灣「獨立」建國,因為不論中共享有何等威望和權力,臺灣的自主國際地位都損及中共將其統治正當化的國家統一觀念與敘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宣示盡全力實現「臺灣與祖國統一」的決心。實際上,1982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陳述:「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北京暗示其一切意圖都是為了防止中國國土分裂,因此不能容許「一中一臺」、「一國兩府」或「兩個中國」持續存在,這些都意味著兩個不同國家各自占居並治理中國國土的一部分。考慮到北京將中國主權視為不可分割,他們也不承認中華民國仍一直作為獨立國家而運作,並(選擇性地)拒絕接受中華民國仍在運作的證據。北京一直扮演著受害方,自認為意在防止臺灣島上「分裂主義者」從事「分裂主義活動」改變現狀,違背他們所認知的歷史事實與國際法授權,並堅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國家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別無選擇,只能繼續作為中國的一部分。
這套敘述某種程度上一直有其說服力。當前普遍通行的學界觀點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極力要讓臺灣降伏於中國主權,是以下諸多因素混合所致:對中國國家認同的憂慮;統一國家的內戰因冷戰開始而中斷;決心捍衛過往曾被帝國主義強權束縛的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在大眾民族主義取代共產主義,成為統一和動員人心之意識型態的時代中,對政權合法性的不安;由人們隨口稱呼的中國民族主義「崛起」所助長的收復失土要求;也是防止臺灣堅持自主在西藏、新疆、內蒙古產生骨牌效應的一種方式。
的確,這些觀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料中都能得到充分支持。很少有分析者會質疑民族主義、歷史冤屈,以及對政權合法性的焦慮均在在影響北京對於如何與臺灣打交道的盤算。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信念並非鐵板一塊,即使同時受限於暗示與明示的制約,其政治論述中仍可讀出某種程度的多元。在臺灣地位問題上,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料讀到多種不同論證,為防止臺灣「獨立」辯護,同時鼓吹統一的重要性。對臺灣相關問題的不同敘述,所強調的起因與作為或不作為後果各不相同。實際上,不同的專業或機構觀點似乎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分析者傾向於凸顯爭議的不同面向。
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部門對於臺灣的官方聲明都由一套特定敘事與詞彙支配,該國分析者和學者發言及著作符合那套概念的程度卻各不相同。某些人幾乎毫不偏離,其他人則運用專業造詣與知識洞見大加闡述,得出的基本結論等於完全相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與此相左的舉動皆應予以制止。
從中國境外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立場的分析者則以自身的國家、專業和智識取向切入這個問題。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有著多樣意見,旨在解釋北京對臺灣的立場,中國境外也有眾多分析者試圖這麼做。因此,關於臺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何以重要,並未形成共識。
有鑑於臺灣問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階層的高度敏感性質,以及支配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階層組織文化的保密習性,確實只有極少數人(中國人或他國人)能以官方權威表明驅動北京對臺政策之力量。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階層推論方式的許多說法看似無庸置疑,但仍是推測。官方聲明並未搭配指引解讀方式的可靠註釋,政策所產生的行動也未搭配清楚明確解釋國家何以如此作為的指南。不僅如此,政策也非內部始終一貫的單一實體之產物,而是來自有決策權的群體之折衝與爭論。這個獨占群體的成員無疑共有某些目標,卻也可能會優先以不同理路達成。在這些條件下,要權衡諸多被推定為影響政策的因素,或許就是一種知情推測(informed speculation)的運用。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對這個問題觀點不同的倡導者所提出的理路,或許也因應著對國內與國際脈絡發展的見解而轉移。
因此,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及臺灣的立場,人們推定的「已知」多半只是普遍認知,未必能密切符應分析者所確信的事實。某些分析者尋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90 年代中期以來增加強制措施運用、拓展軍事選項範圍的理由,他們將北京策略的「硬」面向說成回應臺灣內部的政治轉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分析者和學者口中都能聽到這種說法:北京決心藉由揚言動武嚇阻臺獨,乃是回應臺灣民族主義者1990年代以來大肆鼓吹臺灣獨立、中華民國明著暗著背離「一個中國原則」,以及臺灣多項政治決策被北京解讀為力圖漸進式促成臺灣永久脫離中國。總而言之,北京被描述為(他們經常以這種方式自我描述)挫折、憤怒,更無意與臺灣妥協,因為臺北的政治領袖以各種方式主動激怒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旨在影響臺灣的強硬決心、高壓外交、動用軍力示意,以及軍事能力迅速發展和部署,都被視為「回應」臺北的舉動。
這些詮釋有一定程度的解釋效力。正當臺灣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內部政治轉型解放了島上人民,讓他們競選公職並對政策表達理念,同時大半個世界的共產主義本身則多半被趕下台,在位期間被北京斥為與共產主義不共戴天的國民黨舊政權,也在臺灣被置之不理。隨著正式意識型態實際上退出臺海兩岸的等式,臺灣威權時期普遍存在的可預測性,由民主興起與政治不確定性取而代之。北京對此感到苦惱,更重要的是,臺灣民主發展的獨特軌跡本身,正是北京惱怒的根源。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來,臺灣的政治領袖一直在炒作島上所謂「族群分裂」,以獲取選舉利益。尤其自從民主進步黨2000年取得中華民國總統席位並首度執政,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一直追悔即使可惡卻也可靠的老國民黨消逝。至少可以指望老國民黨支持臺灣是中國一部分,以及統一的實現,這些無論多麼遙不可及都值得嚮往。但這些論點就連國民黨內部都不流行了。
不僅如此,北京也為了在他們看來意圖將臺灣「非中國化」的政策,而持續抨擊民進黨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怒指民進黨2000年當選總統以來所採取的官方行動,抹除聯繫臺灣與中國的制度化象徵性言論與行為,同時促進源自「臺灣島為一單獨實體,有其獨特歷史與文化」概念的政治認同標誌。中華人民共和國痛斥,去中國化相當於促獨拒統。
因此,加速建立軍事手段對付臺灣的努力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合理化,成了對臺灣看似危及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統一的反應。它被描述為完全合理的回應,意在阻止北京絕不容忍的結果─「臺灣獨立」。
儘管說服力十足,將北京對臺政策稱作回應臺北觀感的詮釋仍有限制。首先,這種取徑將臺灣問題錯誤指稱為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雙方統治者之間的爭鬥,而忽視地緣政治與中國對美、日兩國感到不安所發揮的作用。這種推論模式所隱含的次要缺陷,則是把臺灣地位的相關衝突表述為肇始於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卻忽視此前中國與臺灣關係的角色。
最後,若試著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臺策略何以多變,北京又何以訴諸武力威脅,比較性的思考是有其好處。我們不得不好奇,為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需明擺著訴諸武力,就能解決其他持久敵對的領土糾紛時,該國卻認為武力威脅或動用武力是對其無能解決臺灣地位紛爭的理智回應。
正如保羅.胡斯(Paul Huth)所認為,或許政治領袖受到的國內壓力,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挑戰者國家(challenger states),傾向以對抗回應其所認為的目標國家(target states)之背離現狀。倘若胡斯所言屬實,我們還是得問:對挑戰者國家的政治領袖釋放出這種壓力的現狀改變又是什麼?揆諸事實(ipso facto),對現狀的任何改變,似乎不太可能都有必要訴諸強制性軍事手段。某些行動等級必定催生出比其他行動更強烈的憂慮感,促成胡斯所指稱的「國內壓力」。倘若某些條件的聚合,激發出運用包括軍力在內的更多高壓手段之迫切要求,這些條件又是什麼?
換個說法:究竟臺灣「獨立」是以何種方式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覺得這樣的威脅夠嚴重到足以讓中央領導人認為動用軍力是理智選項?他們並非一直強調自己動用軍力威脅或傷害臺灣的能力,對其他領土糾紛也並未一律如此。
實際上,要說北京投注在實行其對臺宣示的政治資本,遠超過其與鄰國解決大多數領土糾紛之所需,這個論述幾乎沒有引起反駁之虞。同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將其強硬的「中國對臺灣擁有主權」觀念注入對他國關係,但其他未解決的領土爭議卻幾乎不曾如此舉足輕重,這個命題也不太會有人爭論。
比方說,人們不會經常讀到或聽到這樣的說法:中國「崛起」與發展的前途,決定於收復釣魚台、南海諸島,或印度收入阿魯納查邦(Arunachal Pradesh)治理的那些土地之主權。即使中、印兩國在邊界東段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以南爭議的土地面積大致與臺灣相當,也並未激起中國人普遍要求收復失土的情緒。反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料,卻充斥宣示統一臺灣攸關中國普遍發展目標的陳述。
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的羅援大校,就表示臺灣是中國前途的關鍵所在。他寫道,統一臺灣島對於中華民族的發展極其重要。他所陳述的理路是地理上和經濟上的:
只有臺灣以東的部分洋面是我國能夠直接進入太平洋的唯一戰略通道。如果這一出海口被他國控制,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將嚴重受阻。而兩岸一旦實現了統一,就猶如打開了一扇走向太平洋的快捷之門,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將蓬勃興起,臺灣與大陸也將因此而在二十一世紀開發海洋的過程中共享利益,中華民族也將因此加快復興的進程。
羅援大校絕非唯一提出這套論證的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派外交政策菁英認為,地理與戰略的交集─地緣戰略是至關重要的視角,應當用於思考臺灣問題。實際上,羅援的觀點代表一套將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發展、經濟繁榮,乃至中國前途聯繫起來的文獻體系。有段浮誇的文字斷言:「如果臺灣獨立,中國失去的不僅僅是36,000平方公里的島嶼,而是整個太平洋、半個新世紀。」
即使說得更有分寸,支持統一的論證把臺灣降伏與國家未來福祉及安全保障聯繫起來的方式,仍凌駕於其他領土目標業經公開宣告的重要性。例如,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天安門廣場上立起巨大的電子時鐘,一座顯示1997年香港回歸的倒數時間,另一座電子時鐘則顯示1999年澳門回歸的倒數時間,北京的志得意滿卻並未搭配以下觀點:對這兩處飛地「收復主權」,將在下一世紀發揮提升中國地位的作用。
這倒不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來都以不帶感情的平和方式處理所有領土紛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許多事關領土的爭議場合,都曾敲響刀刃或舞動干戈。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涉及領土控制的軍事化事件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藏(1950年)、印度(1962年)、蘇聯(1969年)和越南(1979、1988年)的武裝衝突也都牽涉領土糾紛。
儘管這些衝突每次都引出宣揚爭議領土主權之重要性的憤慨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以異常的態度描述臺灣地位問題。只要有人解釋何以如此,斗膽提出一套敘述,將國家的優先事項與領土本身被認知的價值聯繫起來,就會招來譴責;即使統一的地緣戰略理路一直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與大眾出版品討論多時的主題。
誠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以軍事手段對付臺灣的決定,也可以從不受地理或領土重要性拘束的概念視角分析。例如胡斯和其他學者認為,李登輝訪問康乃爾大學、美國對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試射飛彈的回應、2000年陳水扁出人意料地當選總統,或2004年陳水扁更加意外地連任所產生的政治「衝擊」,都影響著挑戰者國家對目標的戰略與戰術。
自1990年代以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進展相關,和國際權力結構構築方式之根本轉移不謀而合的更大範圍戰略因素,都影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世界觀。這些轉型在在質問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戰略環境的關係,並促使北京實行更新後的大戰略。但在作為不可預期且突發之獨立事件,並被認為對早先的風險與機會盤算意義重大的這方面,這些轉型卻非「衝擊」。它們是漸進且易變的發展,其方向與意涵都成型得很慢,也很難融入對中國能力與目標的既存憂慮之中。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世界觀演進,於內於外都喚起人們以新的眼光再思考該國與既有或潛在戰略對手(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引人注目的是,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出兵確保控制臺灣的可能性預作準備之際,該國整裝待發準備一戰的首要敵人卻連臺灣都不是,而是得到日本協助的美國。這令人不禁疑惑:在北京看來,臺灣問題的圓滿解決究竟是被當成「目的」,還是實現更宏大戰略野心的手段。同時也讓人們看到,北京反獨促統的理路,大多由官方文件和宣言表述為一套中國對臺灣關係的敘事。提供地緣戰略視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分析員,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述臺灣地位問題。這也就意味著有必要望向官方敘述之外,才能找出臺灣重要性轉移的線索。
作者為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SAIS)美方主任、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主任、塔夫茲大學佛萊契法律與外交關係學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國際政治學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外交關係、中美關係、臺灣研究及臺海關係,並連結外交史及當代國際安全。著有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Why Taiwan?: Geostrategic Rationale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及相關期刊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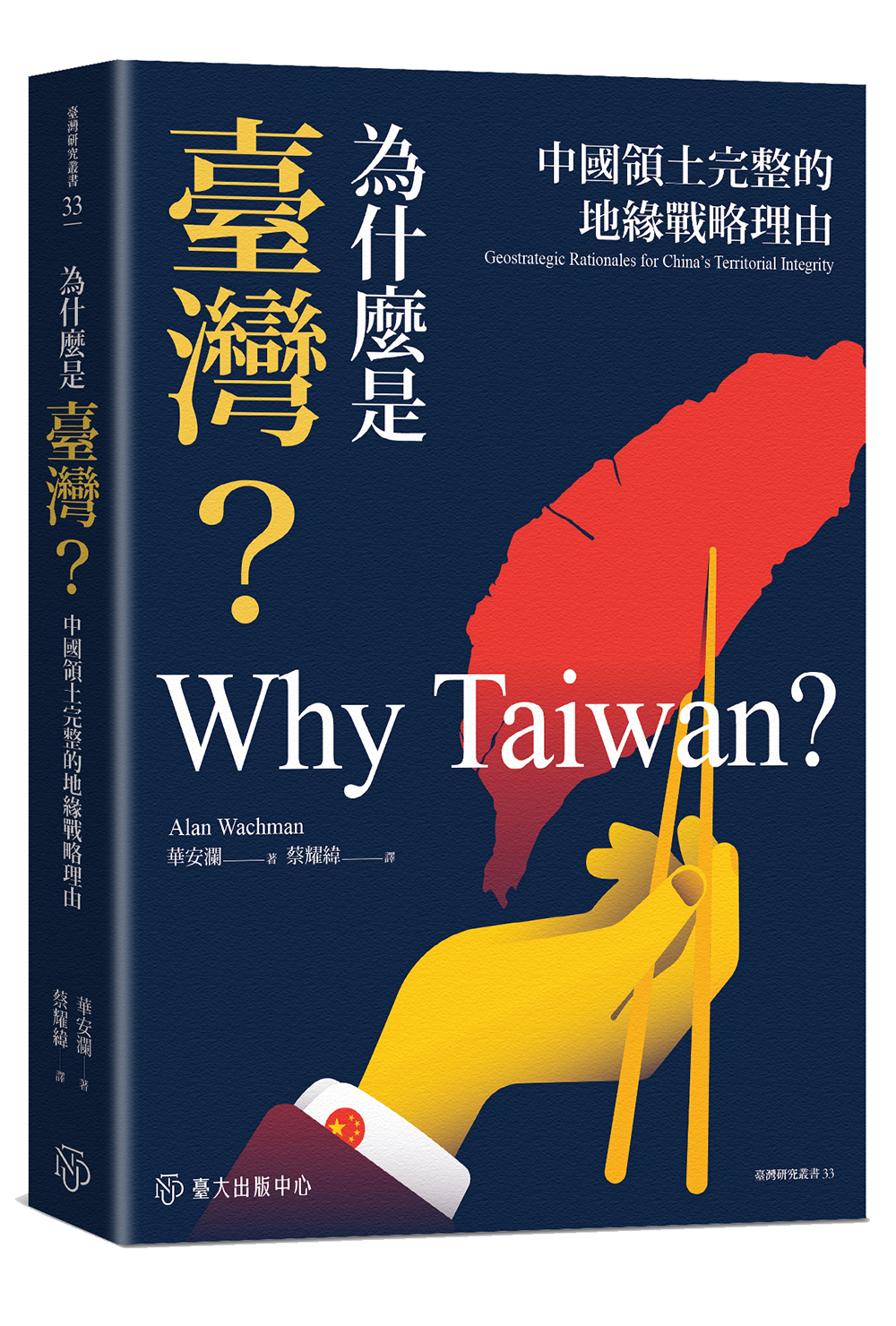
書名:《為什麼是臺灣?》
作者:華安瀾(Alan Wachman, 1958-2012)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23年12月
- 【書摘】《民族的虛構:建立在想像上的集體認同,如何成為現實的族群矛盾?》 - 2024 年 5 月 3 日
- 【書摘】《拆解反動修辭的大師:赫緒曼思想傳記》 - 2024 年 5 月 2 日
- 【書摘】《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與社會學觀點》 - 2024 年 4 月 2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