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左到右:李弘祺、梅原郁、鄧廣銘、斯波義信、柳田節子。1985年五月在杭州召開中國第一次國際性宋史會議。圖片來源:李弘祺提供
幾天前,唐獎公佈頒授今年的漢學獎金給斯波義信和宇文所安(Steven Owen)兩人。作爲一個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我自然替他們感到很高興,也認爲唐獎遴選委員會做了很好的選擇。我認識兩位已經都超過40年,當然覺得「與有榮焉」。宇文所安是我在耶魯讀書時的學長,不過因爲他的研究是文學,所以我不是很熟悉他的貢獻。但是斯波先生是以宋史起家,所以我們比較常聯繫。我每到日本,差不多一定都會與他見面,而這一次的唐獎,我又是推薦他的學者之一,所以很樂意在這裡簡單闡述他的學術,並回憶我與他交往的一些瑣事。

唐獎公佈頒授今年的漢學獎金給斯波義信和宇文所安(Steven Owen)兩人。作爲一個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我自然替他們感到很高興,也認爲唐獎遴選委員會做了很好的選擇。我認識兩位已經都超過40年,當然覺得「與有榮焉」。圖片來源:唐獎官方網頁
當我還在研究院讀書的時候,芮沃壽(Arthur F. Wright)老師就已經讓我們讀斯波的成名著作《宋代商業史研究》。當時這本書才出版不久,但是受到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的鼓吹,所以在英文的漢學界很受重視。不久以後,伊懋可(Mark Elvin)以縮節的方式把它翻譯爲英文,影響就更爲深遠。當時正值宋史研究在美國興起,很多人都讀過斯波的名著。當前著名的鮑弼德(Peter K. Bol)、伊佩霞(Patricia B. Ebrey)、賈志揚(John W. Chaffee)、 戴仁柱(Richard L. Davis)、韓名士(Robert Hymes)、萬安玲(Linda Watson)等人就是這一些人的代表。他們的作品主要是在1980中葉出爐(我的《宋代教育與科舉》出版於1985年),斯波的地位也因而水漲船高。事實上,斯波就曾經寫了一篇書評,討論了我、賈志揚和韓明士等人的書,說這是新一代崛起的美國宋史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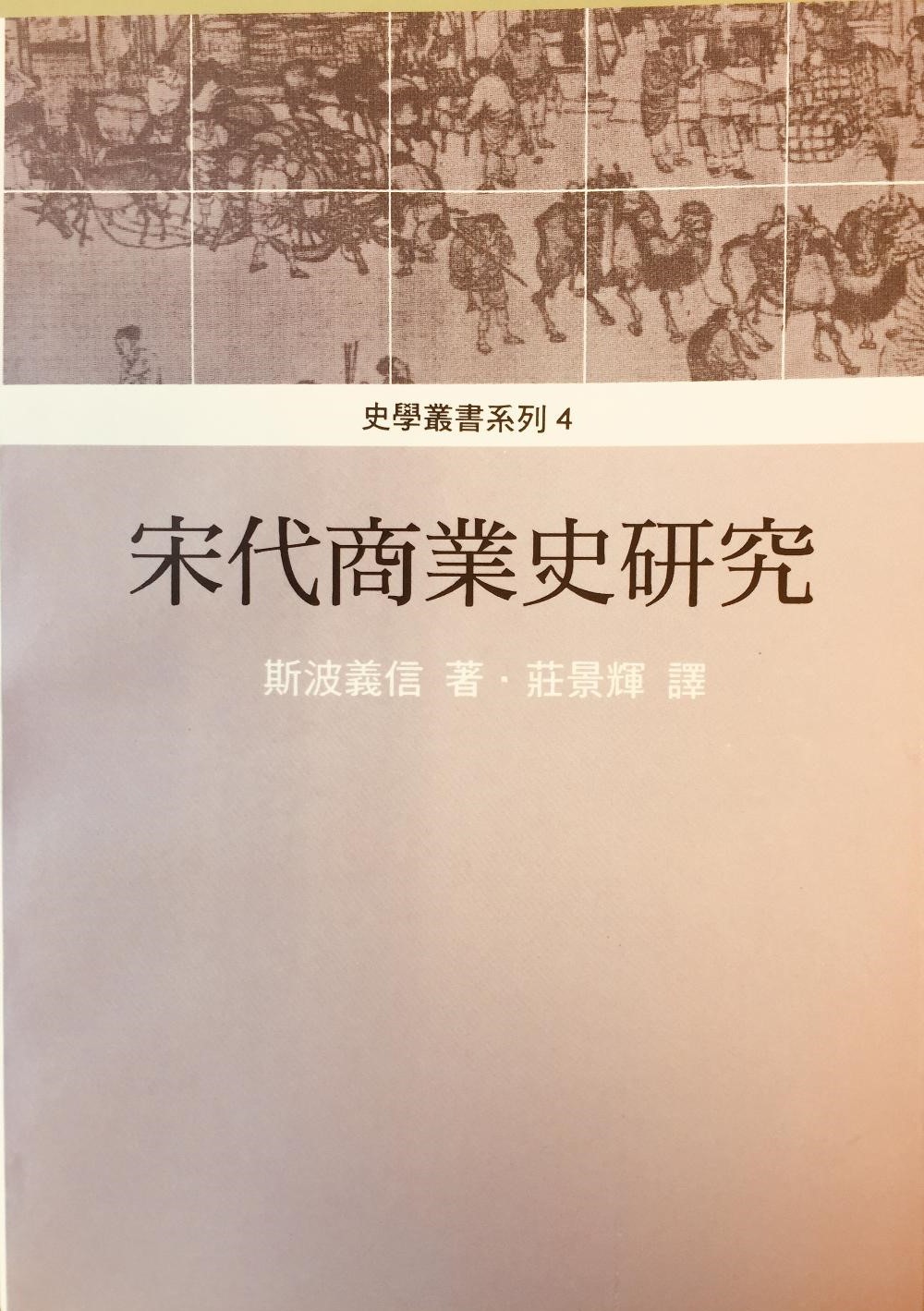
斯波義信的成名代表作係《宋代商業史研究》。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由於《宋代商業史研究》這本書不在身邊,我僅能就記憶所及,提出簡短的討論。我最記得的就是他提出的「宋代已經出現全國性的商業網絡」。簡單地說,宋代各地物產的產銷已經抵達全國各地,而商業活動也以國内的市場為基礎,即使是與遼、金、元的種種茶、馬貿易也不是商業活動的重心。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論點。在這之前,學者們一般只是就宋國是一個政治體,經常受到異族的入侵,把政治作爲宋朝歷史的想象基礎。但是斯波卻讓我們看見宋朝是一個充滿了經濟活力,生活富裕的國家。宋的對外貿易其實以東南亞貿易爲主。這些都讓我們對宋朝生命的活力有了新的認識。
我記得的第二點就是斯波能用西方商業史的方法來看待中國的史料。在他之前,系統地使用《宋會要》這套大書的人還很少(日本人編的《宋會要食貨引得》當時還沒出版),至於採用私人文集中所提到的商業、物價、經濟的記載的,更幾乎是絕無僅有─像陶希聖雖然很早就開始從事中國經濟的研究,但多採用制式的官方紀錄(正史、類書等等),還無法大規模耙梳文集等著作,因此借用西方研究的方法來檢索中國的史料,這是重要的發展。例如他對宋代的内河及海船的大小,收集了十多種材料,這是前此沒有人做的工作。我查對現在各種資料庫,其完備仍然令我們佩服不已。
1974年我得了博士學位,選擇去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第二年,我第一次與斯波先生見面論交,地點就在香港中文大學。原委是因爲他從美國囘日本,選擇經過香港(我猜想這是他第一次到香港)去看全漢昇教授。全先生是上一代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大師,所以斯波先生特地去看他。隨後,他就由全先生陪同來中大看我。兩位長者來訪,真是令我受寵若驚。他說在美國時,也跟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見了面。當時,郝若貝離開何炳棣所任教的芝加哥大學,去賓州大學,地位還不是很穩定,所以還沒有教出太多學生,影響力不是很大。漢學界的主流學者仍然接受柯睿格(Edward Kracke)和何炳棣的論點,認爲中國社會(宋代到明清)有充分的上下流動。郝若貝發願要把這個説法推倒,因此利用70年代初王德毅教授所編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這套書得到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CLS]的資助,所以我雖然只是學生輩,也獲贈一套六冊)全面收集宋人家族關係,提出新的觀點,認爲要計算中國人的社會升遷,一定要同時看各人的旁系,乃至於姻親的家族背景,這個看法因爲很新,所以不爲人馬上接受。大家對郝氏收集材料的全面性及解讀也有保留。我記得我和斯波先生談到這件事,斯波先生也笑說他聽説郝氏用的是卡片,翻閱卡片,十分不便。他還比手勢形容用手指翻卡片的樣子,就好像算鈔票一樣。我們不覺大笑。
1980年代以後,斯波先生開始注意中國沿海各地的區域經濟史,從福建開始,但後來集中研究所謂的「江南」地區。於1988年出版《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就創新的角度言之,這本書容或不如《宋代商業史研究》,但是他把許多地方方志的材料放在歷史社會發展的平臺上面,使得這些材料活了起來,例如浙江蕭山的湘湖,斯波先生算是第一個用地域發展史的觀點研究它與地方經濟發展關係的歷史學者。從此,充滿了神話色彩的地方名勝(勾踐臥薪嘗膽的地方!)也就成了歷史學者可以除魅的客觀存在。
斯波先生從東京大學得到博士學位之後,並未被留在母校,而是到熊本大學、大阪大學任教。這一段時間或許可以説是斯波先生沉潛勞心的時代。由於地近京都,所以他的學術不免有所謂「京都學派」的氣息。我這裡故意提出所謂的「京都學派」,目的是要順便批評日本學界使用「學派」來替學者定位的辦法之荒謬。
日本人習慣把師承關係作爲「學派」的標準,因此也有人把斯波先生説是「東京文獻學派」的學者。從師承來看,這個説法是不錯的。但是東京大學的中國研究(戰前説是東洋研究),光就傳統中國歷史來説,從白鳥庫吉開創以來,已經呈現出各種不同的風貌和方法上的特質,例如仁井田陞就不被認爲是屬於這個學派。但是他畢竟是東大的畢業生,又在東大教書,所以往往也被稱爲是東京學派。於是什麽是「東京學派」?它與「東京文獻學派」又究竟是不是同為一個,這就引發了很不同的爭論。
「東京學派」又往往被拿來與「京都學派」對比,用來解釋兩方面(特別是周藤吉之與宮崎市定)對宋代田制的不同解釋,並廣及其他學術風尚的不同。這兩個學派的分立甚至影響到美國的漢學。以專門寫很長的書評把學問的對手或後輩罵倒的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便曾指控狄培理是屬於「京都學派」。這個是因爲狄培理的思想史一方面盡量接受傳統中國人的解釋(不重視「現代性」),另一方面強調根據文獻的根本意義,而不天馬行空,望文生義。如果從第一方面來看,這個的確比較接近京都學派的特色,但是就第二方面來看,那麽這豈非比較接近「東京學派」(有如仁井田陞)?
兩派的不同事實上只呈現在師承上面,其他就五彩繽紛,各擅勝場,對我們認識一個學者治學的特色完全沒有幫助。例如師承周藤吉之的柳田節子後來便部分接受宮崎市定的説法。有一次我訪問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與專研究宋代官制的梅原郁交流。他拿著仁井田陞的《唐令拾遺》,指出裡頭好幾處在他看來是誤讀的地方,直斥仁井田不能閲讀中國古文。這豈不等於說「東京學派」或「東京文獻學派」不以能善讀文獻令京都學者折服?
仁井田陞以善用二十世紀經濟學理論而名於世,雖然他的學術是建築在文獻的搜羅考證上面,但是他問的卻是經濟制度的法律和社會背景及其運作的問題。或許京都學派的學者們不鼓勵推論、聯想的功夫,所以覺得東京學派常常顯得有過度想象的缺點。
斯波還在大阪的時候,當然不免會讓人家覺得他應該會與京都學派有所往來。但是他的治學方法顯然與所謂的「京都學派」互有扞格。另一方面,如果說他是東京文獻學派的一員,那麽就他重視方法論的特色言之,他又似乎沒有反映出「東京文獻學派」的特質。怪不得他在2015年應邀在華東師範大學演講時,完全抛棄「學派」的架構,而就法制史及社會經濟史來討論日本的東洋史學。對他來説,史學研究當然能不能不講「實證」(就是蘭克Leopold von Ranke 的史學),建築在文獻的考證上面,但是顯然這只是基本功夫,史家一定要進一步使用專門的學問或輔助科學,來處理諸如法制、社會、以及經濟的發展歷史。總之,把斯波畫入「東京文獻學派」不是合宜的做法。
1988年,日本中國史學界發生了一件爭議。京都大學退休教授佐伯富以《中國鹽政史研究》被提名學術院賞。結果東京大學教授(也已經退休)藤井宏跳了出來批評,說佐伯富的巨著是抄襲他更早的一些文章(主要是有關明代徽商的研究)而成,根本不是原創的作品,更是剽竊藤井自己的作品云云。這件事引發了不小的風波。1989年我正好去了東京,到東大東亞文化研究所去看斯波。由於我並不知道這件事的原委,竟然在他的辦公室當著東大的一些學者學生面前問起這件事。
當時斯波顯出局促不安的樣子,顧左右而言他。事後他請我去吃飯,才告訴我說這件事背後有兩校之間長久積累的矛盾,所以我提起它,他會一時非常尷尬,不知從何說起。坐在東大辦公室,當著東大的同事學生面前,斯波並沒有直接捍衛藤井,可見他對學術分野的公正態度。那一年,佐伯先生依然獲得學術院的恩賜賞。
斯波先生的學生很多,我沒有特別留意,但是知道現在東大中國思想史教授的小島毅就曾經受益於他的教導。由於小島教授後來跟隨溝口雄三研究思想史,所以他也受到斯波指導的事比較沒有受到注意。事實上,小島在2000─2005年間主持一個文部省支助的「東亞海洋文化交流與日本文明的起源」(大意如此,正確原名一時記不起來;常常簡稱為「寧波計劃」)大型計劃,獲得多過日幣十億以上的撥款,參與計劃的伊原弘教授得意的很,對我說,用一般手掌上的計算機竟然沒法運算。説時還手足舞蹈,可見當時獲獎的興奮。這個計劃便充分反映了斯波在學術上的影響。
我有幸受邀擔任這個計劃的國際顧問,每一年飛到東京去諮詢和接受報告。事實上,1985年,小島毅和夫人還在北京做研究時,便曾應斯波先生的吩咐到香港玩時要順便來看我。沒有想到今天小島教授已是一方之主,執日本中國研究的牛耳。我特別記述他與斯波先生在學術上的因緣,讓更多人 知道它的直接、間接影響。相信知道的人並不多。
2003年,小島毅給我寫了信,要我準備參加他計劃每年一次的大會,同時告訴我斯波先生已經膺選為學士院的院士,要在我到東京時用計劃的名義替他開一個慶祝餐會。我能參加這個餐會,確實感到非常難得而興奮。這時斯波先生已經是東洋文庫的「文庫長」。所以我也趁便去文庫(其實我早在1978年便已經去過,當時還在舊址)參觀,在那裡接受他親自招待。那天,我也再一次見到田仲一成先生。田仲先生曾長期在香港作田野考察,研究「中國的演戲」,是另一位我非常佩服的學者。
我記得陪我的小島先生指出文庫附近的一條街叫做「不忍通」,說這是出於《孟子》,並說日本許多街道、商店名都取材於中國的經書云云。我當然知道這個,但是取用「不忍」,恐怕連中國人自己也想不到吧。
斯波後來的研究又拓展到都市史。現在做中國(特別是唐代)城市史的第一把交椅的是中央大學的妹尾達彥。他就是斯波先生在大阪大學任教時的高足。
我最近一次與斯波先生見面是在2008年,他應臺灣國科會之邀來台作學術演講。當時我剛到交通大學。接待他,我自然不遺餘力。我們談起學士院種種,他說基本上他是接了江上波夫的遺缺。因爲按照學士院的規矩,員額控制在80人,所以沒有院士過世,就無法補人。可見其獲世人榮寵的理由和程度。有趣的是,江上波夫的名著是《騎馬民族史》,主張日本人種的起源來自蒙古、朝鮮或西伯利亞。斯波先生以研究中國文明如何往南移轉,以及中國東南海岸與東南亞的交流,這裡頭可能隱含的ニュアンス(nuance)就留待大家猜測了。
謹以此文恭賀斯波先生名至實歸的唐獎榮譽。
作者是國際知名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畢業於台南一中(1962),免試保送到成功大學攻讀電機,但是由於志趣不合,所以重新參加大專聯招,以全國文組第一名攷入臺灣大學歷史系(1964)。畢業後,到耶魯大學進研究所,攻讀近代西洋思想史和宋代教育及科舉史。1974年獲得博士學位,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往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並出任大學研究院歷史博士課程指導教授。2008年提早退休,囘台服務,先後在臺灣大學、交通大學及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創設人社研究中心、擔任人社學院院長等職。著有專書十數種,以《學以爲己,傳統中國的教育》(英文原名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為最有名,廣為中外論文徵引,並獲得鳳凰衛視國學成就獎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関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譽為「當今世界治中國教育及科舉之第一人者」。
- 我的季辛吉觀 - 2023 年 12 月 13 日
- 余英時先生的政治觀察──回憶與反思《民主與兩岸動向》 - 2023 年 10 月 13 日
- 真是一個有梗的、聰明過人的傳統中國讀書人 - 2023 年 7 月 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