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驗中的台灣
1980年代,在蔣經國逝世之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已經大約十年,我對於香港存在的意義漸漸有了比較真正的瞭解。當時我們中文大學來往的知識人大多是台灣受教育訓練的人,不少人雖然不是台灣的外省人,沒有國民黨籍,但是卻能被這個世界上大學教授待遇最好的地方聘用。他們來香港教書,大多事先並不知道香港的大學待遇那麽好,而是在台灣找不到教職之後,才來申請中文大學的。例如中大的政府與政治學系,只有六、七個教員,而其中竟然有三個是來自台灣的本省籍教授。他們的態度雖然不見得完全是反共或反國民黨,但是這樣的組合絕對不可能出現在台灣的大學政治系。
爲什麽會這樣呢?台灣當時的國民黨政治學者其實也不少,例如周陽山,張麟徵、楊開煌、趙春山等等,不過如我所説,如果你是國民黨員,大概黨會替你安排,不會選擇到香港。而況當時知道香港待遇那麽好的人,也很少。在港的外省人主要是早年選擇不跟國民黨來台灣的人,在台灣的立場來看,香港除了花點錢動員人們在雙十節到處去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之外,完全不是值得去關心的地方。
1973年,台灣還沒有發達到錢淹脚目的時候,蔣介石正在掙扎攝護腺重病,而香港戰後的繁榮也才剛剛開始。這一年余英時到了中文大學,他所瞭解的台灣與海外一般的「華僑」大概沒有二致。余先生願意到香港教書,這是不得了的消息。但是從1955年他離開香港到美國之後,他差不多沒有寫時論的記錄。前此他如果有寫到台灣的,大多與所謂的「第三勢力」是相同的,缺乏「同情的瞭解」,更説不上有「溫情」(錢賓四先生説要瞭解中國歷史,必須要對中國文化有「溫情」。當然,其他國的歷史應該是一體適用吧!)
在香港的兩年中,余英時沒有參加香港「各界」恭賀國慶的酒會。他也沒有爭取在新亞升中華民國國旗(反正香港政府是不會允許的)。但是他是認同中華民國的,特別是他遇到了這麽多未必認同國民黨的台灣學者。對於他,其實這種經驗是會加强他對台灣政治發展的認同的。
爲什麽這麽説呢?在美國已經17年的余英時大概很難遇到台灣的所謂「黨外」人士。雖然所謂的「費城五傑」就是在余先生到美國那一年開始活動的。但是就是到了1971年,尼克森也僅僅聽説「好像在台灣有些人對蔣介石政府不是很滿意。」(見季辛吉的回憶錄)所以余先生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一方面的訊息並不爲奇。我在1978年夏天在耶魯見到余先生的時候(我第一次與余先生認識是1972年在哈佛大學),他因此把我責備了兩個多小時,因爲他聽説我是一個「臺獨」分子。不管如何,我相信他是把所謂的「臺獨」放在一個很有同理心的視野的。
寄厚望於台灣
這時,余先生剛剛重拾停止了將近20年的政論寫作。我認爲他的決定有很大部分是因爲在香港的正面經歷和對國家認同的反思。我必須更進一步說:那兩年與他常常深夜暢談到天亮的朋友就是邢慕寰先生。我不能説我非常認識邢先生,但是我們在耶魯和香港先後相處了一共四年,我知道他對我是很好的。邢先生對於台灣政局的看法當然與國民黨的理念相同,但是他對於國民黨在台灣實行的「内政」做法顯然是跟後來的李煥是相近的(雖然李煥是出於政治的考量),認爲對台灣本省人不公平。這一點我非常清楚。我相信余先生在這一點上面應該是認同邢先生的。
因此,1975年,他在《中國時報》第一次發表類近於政論的〈中國的反智思想〉一文,算是他開始寄望於台灣國民黨政府的衷心發言。雖然像我們這些比較開明的知識人都很欣賞這篇文章,但是卻聽説王昇非常不高興,考慮要下令禁掉它。卻因爲聽到說作者是一個哈佛大學的教授,只得罷手。
再下來便是余先生積極觀察台灣政情,思考民主制度與兩岸關係的階段了。在這本題爲《民主與兩岸動向》的書中,我們看到的最早的文章卻是晚到1987年。我相信這一段的沉默應該是他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以及台灣黨外活動日趨頻繁的情形作緊密觀察和反思的時期。1977年發生了中壢事件,次年余先生代表美國漢學界去中國訪問。這兩件事情都對他產生了很大的震撼。我記得余太太在中壢事件(1977)時曾經對我們去看余先生的後輩們說同情黨外活動的話。我當時自然感到意外。同時,余先生剛從中國回來不久,他放映幻燈片給我們幾個學生看。我記得他特別强調沒有一張相片是有中國共產黨的標語或符號的。他的反共態度一點也沒有改變。
以上很長的囘憶是用來作爲余先生這本《民主與兩岸動向》的一個導論,因爲這是一本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忠實反映余英時政治觀點發展的實錄。余先生自從離開北京到香港(1950)以後就是堅定的反共志士,這一點終其一生沒有改變。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候,他認爲從此香港就會像中國一樣,由一個專制甚至邪惡的政府所統治,他因此不可能再回去香港了。1997年前最後一次經過香港時,他就是這樣告訴人們的。
但是余先生畢竟在1997之後,因爲看見香港並沒有馬上就崩壞,所以有了回來訪問之舉,不止一次,不止兩次,而是三次。這個反映了他對香港沒有即刻「族天下化」的高興期待的心情。不幸,這樣的期待沒有能維持太久。2014年的雨傘運動結束了這一個短暫的晴天。事實上,1989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慘案早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在這本書中,讀者很容易看到他在1989六四慘案時的心情和重要改變。首先,他在六四以前的1988年,雖然蔣經國去世,他仍然寫出像「群龍無首,民主之始」(1988/1),「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同上),或「開放、民主與共識」(1989/1)等等對於台灣的民主寄以希望的文章,甚且相信蔣經國提倡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中國能夠完成「周雖舊邦,其命維新」(1988/7)的可靠藍圖。事實上,在六四慘案爆發之前的半年左右,他還寫了一篇「大陸民主運動的再出發」(1989/2)鼓舞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囘去擁抱五四運動(1989/5),以及樂觀地在六四前夕寫下了「天地變化草木蕃…」的文章,來稱許「新五四」運動(1989/5),事實上,這篇文章是寫來稱頌「新五四」運動的「偉大成就」的。余先生的自信與天安門前的學生們真的是千里相映,海天迴響:「新五四」終於重囘到「五四」的主流,但是浩浩蕩蕩,波瀾壯觀,運動的流量已經擴到無可遏止的地步了。可見他當時擁抱中國的興奮之情。
天安門慘案:終極關懷的破滅
余先生對他所自出的國家的愛是完全的,是絲毫沒有自私的,所以他會在這幾年中寫了這麽多篇寄望中國可以重新擁抱五四,走入民主的康莊大道的文章。然而,六四的慘案令他徹底失望了。對於一個終生熱愛中國,卻又敬仰近代民主社會和價值,再半年就要耳順的讀書人來説,這種精神世界的破滅是非常難過的。田力克(Paul Tillich)說一個信仰破滅的人,看到他的「終極關懷」崩壞,那是極端痛苦的事情。余先生這時的心情顯然正是如此。
這就是他爲什麽轉回來思索台灣的政治前途的最大原因,也是要繼續做夢的必要契機。六四之後,他寫的兩篇文章都是嚴厲斥責中共的文字,而且是以諷刺的語氣來表述,說中共替死人服務,是「光棍」的政權(光棍這個用法一般人可能無法馬上會其意,請參看該文,p. 169)。
本來余先生在蔣經國去世前後對於中國的局勢(特別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及中國的未來是保有近乎興奮的樂觀的,所以他會引用朱熹非常隱晦的「硬相守」的話來說他心中仍然夢想的最後中國統一的憧憬。但是六四以後,鑒於台灣政局的發展,加上李登輝在海外台僑以及美國自由派政治家(Edward Kennedy, Stephen Solarz, Claiborne Pell 等)的支持下,台灣的民主化才走得比較順利,「虎口下的總統」在驚濤萬丈的風浪中成功打贏了所謂的「非主流派」,走上開放的途徑。
余先生在美國數十年,是少數華人能細心接受西方民主理想的出色學者。這個特別重要,因爲當年從台灣(以及其他自由地區)去美國讀書的,絕大多數是理工醫的學生,對於西方政治傳統缺乏系統觀察或認識的時間或能力,所以余英時的自由主義是非常獨特的。民主自由的理想和中國文化的教養之間,余英時是如何佈置其先後呢?這個可以在2006年他獲得克魯格獎,接受記者的訪問時,所説的話看出來:「我的人在那裡,那裡就是中國。」換句話説,他長期的思考早已經有了答案。那就是他的信仰就是他的中國。這就像他常常也說的一句出自布倫諾(Giordano Bruno)的話:「宇宙是無限的大,處處都是它的圓心」。余英時的中國早已經蛻變(或説蟬蛻)為一個心靈上的寄託,因是惟其如此,他的民主自由理想才能與隨處同在的中國沒有矛盾。
台灣民主發展與精神的升華
就是這樣,余先生才能在李登輝以後的台灣民主做出一種精神上的升華,即使他繼續對中國作爲一個國家懷抱由衷的感情。雖然中國已經出現「異化」的現象(參看頁81-189),他還是認爲台灣的發展(穩定,秩序)是與中國關聯在一起的,而在他看來中國共產政權的在2000年左右會發生「巨變」,它是「指日可期」的(p. 242)。在1991年替《天下雜志》十周年(1991)寫的這篇〈世界解構兩岸解凍〉是一篇有點奇怪的文章。或許應該説這是在台灣的主流與非主流力量發生惡鬥後的餘波蕩漾時寫的。中國結果並沒有發生巨變(這個月或許會,但這已經是余先生寫文章之後的32年了),而當前發生的兩岸經貿關係竟然是三十年「解凍」後的鮭魚回流了。余先生的政治思想不免有那種再能置身於無限、再能高瞻遠矚,卻最後仍然必須逃避不了他自己的歷史背景的困境:吾有大患,在吾有身。這也就是爲什麽他會在台灣開始有了總統民選的呼聲最高的時候,寫出反對黨擁抱的臺獨思想會造成「少數專制」,會破壞共識,是和民主原則相背反的話,甚至於說「台灣的社會秩序已經壞到了崩潰的邊緣」的話。這裡所反映的明顯是所謂的「非主流派」的説法。32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説所幸這裡余先生所説的並不完全正確;除了中國的威脅之外,台灣的民主是堅定而穩當地在進步當中。
國家與文化,民主與臺獨,理性的困窘
大體來説,他在人生最後的二十年左右,對於所謂的「臺獨」問題是有非常慎重的思考和同情的。這個地方我不能不説他真的是非常能做到「同情的瞭解」,是我所見到的非台灣籍華人中最深刻的。他反對省籍意識,認爲這是反對黨政治活動中缺乏理想性的最大缺點。他因此對台灣政局的發展,有一個很大的擔心:對中國文化的「疏離」(或乾脆可以説是「異化」)。這裡的擔心當然是出自他對中國的愛和信仰,但是這個愛或信仰在共產制度的摧殘下,只剩下了台灣。所以他對台灣的寄望是可以瞭解的,他懇切希望台灣人不要尋求獨立。
在他看來,台灣與中國文化相同,沒有獨立的必要。他每一次談到台灣問題的時候從來就是這麽說:「台灣人和中國人的文化本來就是一樣的,怎麽會獨立呢?」我當然知道這樣的説法無法解釋國家(以及政府)主權爲何存在的基本問題,不過我接受他無法從理性或邏輯的角度來解釋這個問題的内心之痛。
也許可以説他認同的是一種文化的中國。這種文化的認同卻又無法完全解釋他爲什麽對五四運動的認同。理性真是有時而窮!(這裡應該簡單說一句:余先生認爲五四運動不是一種「文藝復興」,這個完全是一個比較歷史的客觀説法;他主張中國史研究的中心任務就是發現中國歷史的獨特性。)他當然知道文化不以作爲國民為要件。但是如何可以説出來呢?這個是一種非常難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余先生當然也逃避不了這樣的困窘。
余先生是誠實的。他常常說世界上有三樣東西是無法用理性來談的:愛情、宗教、和政治。所以談「民主乎?獨立乎?」(pp. 094-100)這樣的題目,這個就需要他用非常大的勇氣來寫。須知,他寫這篇文章時,台灣正將舉行解嚴後的第一次選舉;許多積纍已久的問題都被提到選舉的政見上面,局面非常緊張(所以余先生會有「台灣的社會秩序已經壞到了崩潰的邊緣」的印象),所以他寫了這篇文章。他對反對黨政見的寬容態度時是後來余紀忠不再邀請在《中國時報》寫文章的濫觴(最後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是在1996年)。從此,余先生對台灣的評論就戛然而止。
李登輝選上總統之後,我們不再看到他對台灣政局寫有文章。在《余英時談政治現實》一書中(顏擇雅編,出版於2022年) 所收的政論或時評的文字差不多全部是在香港發表。大多數討論的都是有關香港的問題。香港的發展是他在臨終前最失望的事情,我這裡指的是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及推行(2020年六月),明年八月,余先生就撤手歸天了。
結論:
不能否認的是所有的知識人都活在規範性的理想和實存世界的邪惡當中;生命是不斷的掙扎。余英時作爲一個公共知識人,他的政治思想當然是厚植於他的學術基礎上面的。他的歷史學的訓練在他的時代是最爲優秀的。這個當然使得他對於自己的眼光和洞察的能力有極高的自信。他的西洋史知識(尤其是思想)是我們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所有華人歷史學者中的數一數二的。何炳棣常常自以西洋史訓練出身而自鳴得意。但是我從來看不到他曾經系統寫出或演講西洋歷史的東西。余英時則時時表現出他對西洋文化的開放態度,而且也常常徵引西洋思想來與中國文化做格義的功夫。
但是即使如此,余先生始終是一個中國人。在無限的宇宙裡,他不管逃到哪裡,那裡都是中國,他認同民主以及五四的價值,一直以為安身立命的「終極關懷」。不幸他活在馬克思以後的世界。雖然台灣的民主展現了難得的活力,但是民主卻和國族的認同無法和轍,雖然他因此提出文化的高貴理想,但是這個充滿「異化」的現實世界,卻不斷地挑戰知識人對價值的堅持。余先生一直沒有放棄他作爲知識人的自命,於是就不斷地痛苦面對將近百年的折磨。
讀完余先生當年的這些文字,我就更相信惟其實存的挑戰才會使得反思更爲深刻,而只有歷練才創造了理想的持久引人的活力。至少在政治思想上,這個就是我對余先生的瞭解。
(2023年9月28日於美東華萍澤瀑布)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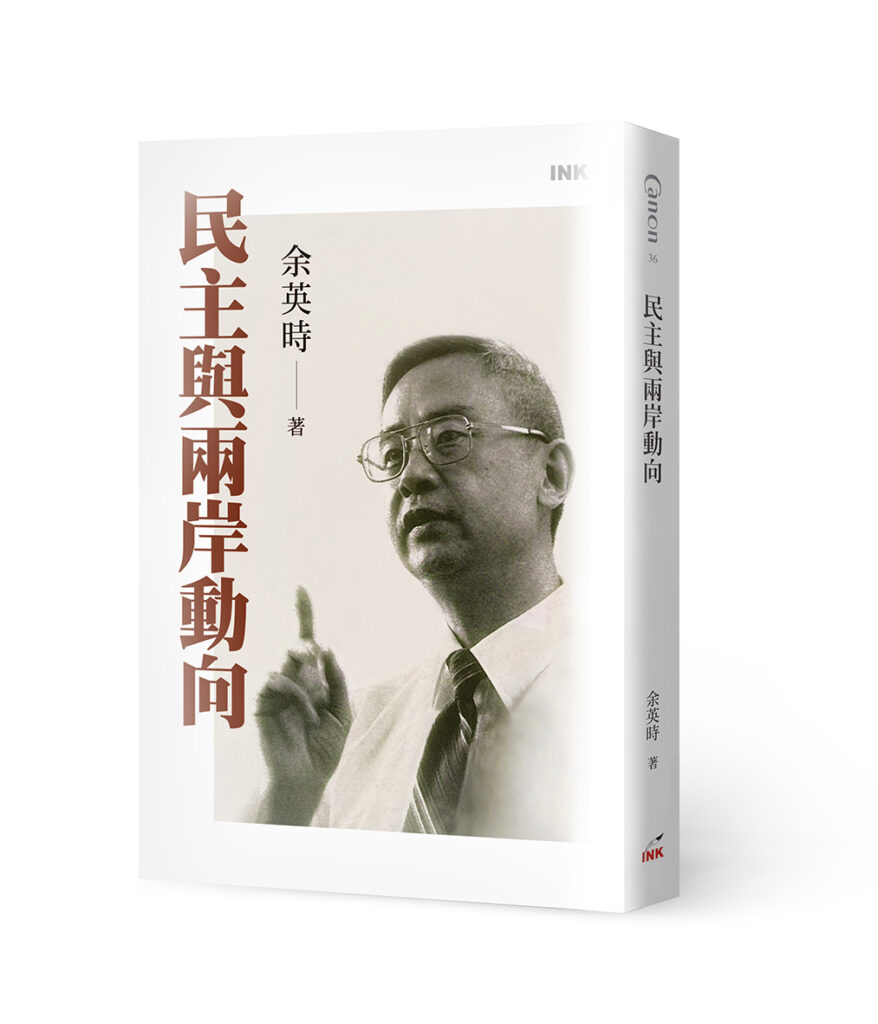
書名:《民主與兩岸動向》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印刻
出版時間:2023年9月
- 我的季辛吉觀 - 2023 年 12 月 13 日
- 余英時先生的政治觀察──回憶與反思《民主與兩岸動向》 - 2023 年 10 月 13 日
- 真是一個有梗的、聰明過人的傳統中國讀書人 - 2023 年 7 月 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