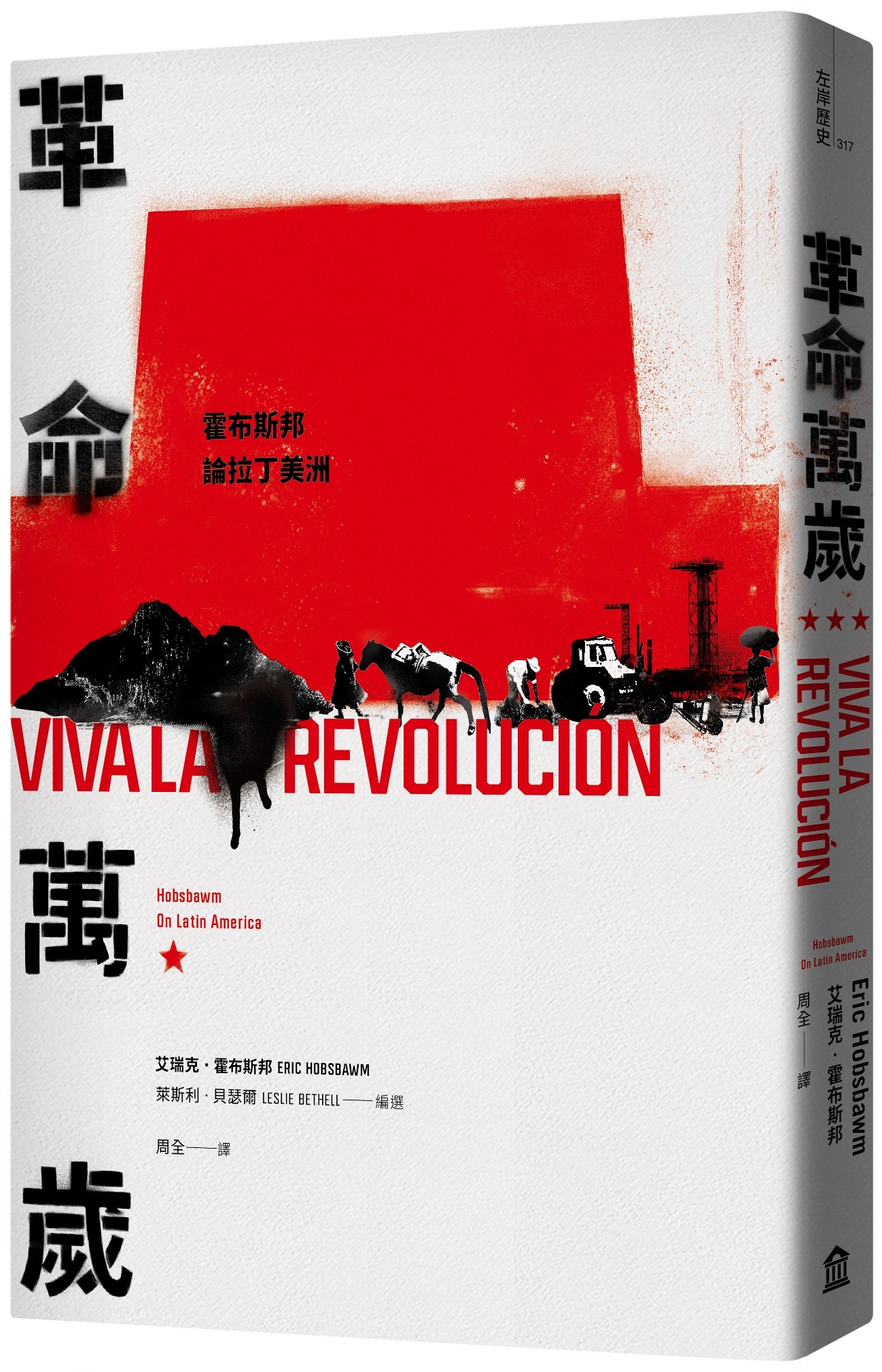
拉丁美洲的民族和民族性
民族主義在世界許多地區都是受到學術界密切關注的課題,因為它也是一個迫切的政治課題。本文所探討那個世界的民族主義,在這兩方面都有些異常:拉丁美洲。這乍看之下顯得相當奇怪,因為班納迪克.安德森曾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嚴正指出,現代民族主義真正的全球先驅是十八世紀西班牙美洲的克里奧人城市。然而,少數精英群體的民族主義不應與真正的民族主義混為一談。儘管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著歷史聯繫,但後者是以國族意識——或者依附於民族象徵或民族體制——的形式,而在人民之間擁有或產生了群眾基礎。它更不應與種族或宗教之類排他性較高的國族意識形式混淆。在這兩個方面,拉丁美洲都發展得比較晚。其實它直到今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現代種族/文化民族主義的影響。
讓我先簡單回顧一下殖民地時期以及獨立之初的情況。殖民者與主要城市及其居民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加劇,此外,在十八世紀後期的西班牙帝國和大英帝國,移居者的自治要求也甚囂塵上。我們不難在一些克里奧精英自治的代言人當中發現潛在的民族主義分子。在有可能實施克里奧精英自治的地區(例如新西班牙)更是如此,於是創造出了一些神話,宣稱當地的克里奧人和梅斯蒂索人於某種意義上代表著非西班牙的本土傳統(即便那當然已經被基督教化了),亦即延續著前哥倫布時代各個帝國的遺風。現代墨西哥民族主義的強烈阿茲特克風味,便是這種由克里奧人在十七和十八世紀「被發明的傳統」所造成之結果。
然而,這種潛在的民族主義受限於克里奧人對美洲群眾的嚴重不信任感,以及對其社會革命的畏懼——此種革命戲劇性地體現於一七八○年代秘魯的圖帕克.阿馬魯,以及一七九○年代海地的杜桑.盧維杜爾。正如同班納迪克.安德森所指出的,克里奧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西班牙王室明顯親原住民的政策而發,拉丁美洲的獨立則由於原住民公社對西班牙殖民政權的支持而受到遏制。除此之外,拉丁美洲和英屬美洲解放運動的真正意識形態來自啟蒙運動,而對啟蒙運動的意識形態來說,「國族」並非赫爾德式(Herderian)不具政治性的概念,也不是社會與文化方面的概念。「人民」是在擺脫枷鎖和選擇自由的過程中建構了自己的「國族」,而不考慮其先前的組成方式為何。根據西耶斯神父的說法,一個國族只是「生活在共同的法律之下,並由同一個立法機構所代表的人們之聯合體」。在美國和法國的經典案例當中,它除此之外別無限制。「國族」本身就意味著公開邀請加入。反正無論如何,決定要起而反抗西班牙,並不一定表示要排斥西班牙的一切。……
但是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有關拉丁美洲獨立——或至少是西班牙語系美洲獨立——的關鍵問題(巴西脫離葡萄牙的經過則相當不同)。為什麼北美十三個分離但結盟的殖民地能夠於一七七六年的獨立宣言和世紀末之間,明確而快速地形成為一個國家,在西班牙語系的美洲卻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難道說是因為西班牙帝國面積遼闊又成分殊異,使得像十三個殖民地那樣協調一致的反抗成為不可能?莫非帝國內部的重要地區反對獨立,而且其反對效果遠甚於日後美國的任何反獨立勢力?還是我們只需要提醒自己,十三個殖民地的白人人口雖然在一七九○年為數不多(略少於四百萬),卻幾乎肯定絕對比加利福尼亞至合恩角之間整個地區的白人總數還要多出許多,而且相對來說更是遙遙領先?據估計,當地在殖民時代末期(一八二五年)的白人總數還不到三百五十萬。此外不應忘記的是,拉丁美洲的主要城市比美國同類型的城市要大得多。美國在一七九○年舉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時候,沒有任何北美城市的人口多於費城的四萬二千人;墨西哥城卻已將近十二萬人、利馬接近五萬三千人,甚至連卡拉卡斯也即將突破四萬大關。但獨立帶來了拉丁美洲城市精英階層的政治地位衰落,還有鄉間大地主及其武裝力量的崛起。如此一來便意味著,西班牙語系美洲「政治國家」的天然支持者權力遭到了削弱,因為一旦在大莊園主的操縱下獲得獨立,地方利益和區域利益更有可能居於上風。這一切都是理由。但事實仍為:在那十三個殖民地,由其全體(白色和自由)居住者組成一個獨立國家的想法,早在宣布獨立之前就已經是其意識中的一部分(比起精英階層,或許一般大眾更是如此),而且它們彼此之間不可否認有某種團結一致感。在拉丁美洲很難發現這種感覺,只有巴西除外——葡萄牙帝國的那個部分已經整體脫離出去,成為單一國家。正如我們所知,就連較大規模組建區域聯合體的嘗試(例如大哥倫比亞),也都徹底失敗了。
由此觀之,從獨立戰爭中脫穎而出的那些拉丁美洲國家(或至少是西班牙美洲國家),都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國族」或「民族國家」,而且它們也不是民族解放運動所造成的結果。在該大陸的很大一部分地區,甚至連殖民地的行政區劃分都相對較新,並且──如同後殖民時代的非洲一般──多方面為新國家提供了框架。它們是西班牙王權在十八世紀(有時是十八世紀晚期)進行殖民地重組下的產物。在所有這些國家當中,或許除了智利(玻利瓦爾本人曾特地稱之為成功的國家),地方和區域層級的對立關係甚至遠比各地精英之間的共同點還要來得明顯。因此獨立後的最初幾十年間,內戰或區域性的戰爭層出不窮,即使像拉普拉塔盆地那樣具有地理連貫性的地帶也不例外。也因此拉丁美洲國家老是傾向組成正式或非正式的聯邦,直到國家的中央權力開始對國家領土建立有效控制為止,而且主要還是在二十世紀才逐漸完成。事實上,就連各個新國家的精英們也沒有太多的同質性或共同觀點。他們所居住國家的名稱往往是獨立後的發明,他們之所以認同國家,僅僅是因為這些新國家的機制──尤其是名義上自由的代議制憲法──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國家級的舞台,讓他們能夠在台上盡情施展自己縱橫捭闔的功夫。也許唯一真正有意讓這些國家成為「國家級單位」的團體,就是建立了這些國家的軍隊,或是在這些國家攫取了政權的軍事強人。一旦新國家的地位不再是個問題,地區分離勢力被排除於政治之外了(地方分離在一八三○年之後只是偶爾出現,而且是像阿克里和巴拿馬那樣受到外部影響所致),不管自己的首領再怎麼變,軍方都成為實際上涵蓋共和國全境的唯一機構。任何軍事獨裁者所渴望的權力都是全國性的。鑑於過去一百五十年來拉丁美洲國家的軍隊難得讓其他國家的士兵流血(顯著的例外是一八六四至一八七○年的三國同盟戰爭、一八七九至一八八四年的太平洋戰爭,以及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的查科戰爭),軍事榮耀在南美洲的國家神話中都扮演著不成比例的角色。
我們不妨一致同意地把平民百姓剔除在新國族意識的承載者之外,但巴拉圭和阿蒂加斯的烏拉圭或許是其中特例──兩國在爭取並捍衛獨立的過程中,對抗舊殖民勢力的成分較少,對抗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巴西的成分居多。墨西哥則肯定是圍繞著前哥倫布時期托南津那位神明的繼承者,瓜達露佩聖母,形成了真正的大眾意識。在伊達爾戈和莫雷洛斯的時代,男人們在瓜達露佩聖母的旗幟下揭竿而起。雖然瓜達露佩聖母崇拜無疑已經和墨西哥民眾的國族意識融為一體,伊達爾戈時代的黑面聖母與其說是國家的象徵,倒不如說是窮人的守護女神和保護者。那些窮人僅僅因為是墨西哥的貧民,才使得他們在過去或現在具有了國族意識。透過阿爾維托.弗洛雷斯.加林多在《尋找印加:安地斯山區的身分和烏托邦》(一九八六)一書的精闢分析,我們才發現以「印加千禧年主義」(Incamillennialism)形式流行於安地斯山區的意識形態,原來在一九二○年代之前與當地那些新的共和國根本毫無關係。
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期待一般民眾會對國族感興趣,甚至對它具有任何概念。那些國家的國族意識形態製造者若非對拉美大陸的大部分居民不感興趣,就是──而且更可能是──認為這些居民乃妨害國家進步或其他任何進步的主要障礙。巴西作家安東尼奧.坎迪多以敏銳的觸感比較了下列二者:著書譴責羅薩斯政權在阿根廷鄉間倒行逆施的多明哥.福斯蒂諾.薩米恩托,以及將近六十年後試圖闡明巴西巴伊亞州「塞爾唐」居民現象的歐幾里德.達.庫尼亞。薩米恩托《法昆多》(一八四五)一書的副標題「文明與野蠻」,也非常適合成為一九○二年歐幾里德.達.庫尼亞《腹地》的副標題。套用阿根廷詩人埃斯特凡.埃切瓦里亞的講法(一八二九年),對薩米恩托來說,這在一方面是由城市代表的「進步、自主和自由的原則」,在另一方面則是以農村為代表的「故步自封、愚昩無知和專制殘暴的反社會無政府主義原則」。薩米恩托時代的城市(但在達.庫尼亞的時代已非如此)不僅居於少數,而且在政治上遭到了邊緣化。
簡而言之,進步主義者需要培養出一種國族情操,藉以取代古老而強大的聯合體與社團(地方的、職業的、宗教的、種族的……),那些都是阻礙進步的頑固障礙。然而,這意味著對拉丁美洲平民大眾所珍視的一切進行正面攻擊。無怪乎當地精英會被實證主義那樣的國際通用意識形態所吸引,因為當握有國家權力、志在現代化的精英人士,面對堅定不移和具有敵意的群眾力量之際,這種主義會變得非常合用。巴西的國族意識形態成了孔德式的實證主義,而且要是沒有那場革命的話,墨西哥的國族意識形態也可能變得如此。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許多相信進步的人對於是否能讓群眾移風易俗深感絕望,以致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大規模移入「優等」人種(即歐洲人),並且將印第安人和黑人邊緣化————甚至連當地受到周遭野蠻作風腐蝕的克里奧人也比照辦理。只有墨西哥對此表現得並不熱衷,這不難理解,因為外國佬已隨著墨西哥大部分地區在十九世紀被割讓給美國而紛紛湧入。但儘管如此,換個角度來看,他們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影響受到了歡迎,正如英國的影響受到歡迎一樣。十九世紀的進步主義和中產階級民族主義並非針對外國帝國主義而發。他們隨時歡迎外國企業和移民,這完全符合他們的民族主義。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智利的政治統治階級一直覺得自己是智利人,即便我們想像得到的那些成員(除了一些無所不在的巴斯克人)都有著明顯來自外國的姓氏:愛德華茲、皮諾契特、弗萊、阿言德.戈森斯、亞歷山德里、馬爾馬杜克.葛洛夫、福克斯利等等。在另一方面,這種民族主義排除了所謂種族或歷史「民粹民族主義」的吸引力。讓我們回想一下阿根廷詩人何塞.埃爾南德斯的高喬人(gaucho)史詩《馬丁.菲耶羅》。菲耶羅吟唱道:
高喬人只能強顏歡笑逆來順受,
直到死亡過來將他吞噬;
或者我們得到一個克里奧羅夥伴,
按照高喬的方式來統治這片土地。
這種地方上的憤懣情緒,在裴隆領導下的民族主義新階段被利用得淋漓盡致,突顯出「真正的阿根廷」對布宜諾斯艾利斯港都人(porteños)以及外國人的敵意。裴隆主義的實際真相卻大不相同。裴隆軍隊中一半以上的將軍都是外國移民子弟,顯示出在拉丁美洲以外的世界所罕見的同化意願和同化速度。
所以截至二十世紀,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獨立後階段,儘管有著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和揮舞的軍旗,但此階段並不是很重要;另一個階段則實際上與反傳統主義幾乎不謀而合。「國家」意謂著進步(亦即經濟發展),以及在全國領土上建立有效的國家權力。只有那些爭取進步或至少願意接受進步的人,才可被視為國家的真正成員。
第三個階段則基本上開始於墨西哥革命,並且與俄國革命遙相呼應。其特點不僅在於各種群眾運動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在全國範圍內參與自己國家的政治,同時也在於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承認,國家是由人民所組成的──或許是除了熱帶雨林印第安人之外的每一個人。有三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首先是一九一八年開始於阿根廷的科爾多瓦,接著很快在整個拉丁美洲擴散開來的學生運動。它一直蔓延到秘魯、烏拉圭、智利、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墨西哥和古巴,並且明顯激發出新的民粹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像是日後秘魯的阿普拉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玻利維亞的民族革命運動黨、委內瑞拉的民主行動黨等等,或許也可納入其中。此類運動第一次從根本上反對帝國主義,並且將「人民」確立為知識分子政治活動的基本對象,所以就這個意義而言它們都是民族主義運動。第二個例子是一九二○年代的秘魯,當時「原住民主義」(indigenismo)──即承認印第安人是秘魯百姓的骨幹──成為秘魯國族意識的核心部分。這不僅被反對派知識分子(例如馬里亞特吉、阿亞.德拉托雷等人)表達了出來,甚至還體現於萊吉亞、普拉多,以及桑切斯.塞羅幾位總統的官方政策中。第三個例子是一九三○年代的巴西。在那十年間,有三本書無疑形塑了現代知識分子對巴西和巴西民族性的概念,分別是希爾維托.弗雷爾的《華屋與棚戶》、塞爾吉奧.布阿爾克.德.奧蘭達的《巴西之根》,以及卡約.普拉多的《當代巴西的形成》。三個例子的共同點是譴責種族偏見,將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種的後裔融入迄今主要以本地或移民白人為主的「國族」。簡而言之,它們的共同之處在於把「國族」的觀念延伸到在地的大眾。
這種延伸之所以變得比從前容易(至少對革命知識分子而言如此),是因為群眾現在似乎已經自己為革命行動做好了準備,並理所當然地認為,革命就是為了要創造一個致力於科學、進步和啟蒙,而且群眾迄今對之不怎麼感興趣的社會。阿亞.德拉托雷則至少和薩米恩托一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現代化主義者,而馬里亞特吉也是如此。秘魯歷史學家,同時也是人類學家的路易斯.埃杜阿多.巴爾卡塞爾寫道:「安地斯山區的農民在等待一位列寧。」墨西哥的革命已經證明,至少可以創造出一位薩帕塔和一位比亞。然而,不管「所有農村群眾在等待他們的列寧」這種假設具有多大的誤導性,此後不可否認的是,農村群眾當中的某些重要部分能夠被左派所動員。無論如何,左派的群眾運動從此不僅可以如同在南錐體那樣,存在於主要由移民組成的工人階層之間,更可如同在秘魯一般地與非白人無產階級同在。阿普拉黨已成為一個大型的勞工政黨,即便它對印第安心臟地帶的影響微乎其微。從墨西哥革命開始,美洲所有的國族意識形態都納入了群眾。
書名:《革命萬歲》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出版社:左岸
出版時間:2021年02月
- 【書摘】《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與社會學觀點》 - 2024 年 4 月 26 日
- 【書摘】《鐵幕降臨:赤色浪潮下的東歐》 - 2024 年 4 月 25 日
- 【書摘】《美利堅國度:十一個相互對立的地區文化史》 - 2024 年 4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