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80年代是分水嶺
郝倖仔:您說要我一定瞭解1980年代的重要性,除卻五年計畫增加員額的因,2000年之後成績爆發的果,還給史語所帶來哪些方面的變化?
黃進興:這就像登山爬到臨界線,可以看到上山的這一邊,也可以看到下山要走的那一邊。1980年的史語所,就是這樣一條臨界線,前舊後新。我先給你講個故事。有一次我在華東師範大學訪問,茅海建先生和我有一個談話,他說90年代他曾經來臺灣中央研究院訪學,有一天晚上,在院裡散步,看到史語所研究大樓燈火通明。這麼晚了,大家都還沒有回去,都還在兢兢業業的努力,讓他很驚訝。
郝倖仔:那是臺灣經濟騰飛的時代,整個社會普遍士氣高昂。學人對學術有著極高的想像,彼此之間互相砥礪。
黃進興:另一方面,史語所老一輩的人,以所為家的情感和氛圍在那一代是比較重的。我七十歲了,我講的老一輩,就是80歲以上的。所以80年代之前,老史語所的味道很濃厚,所裡就是一個家庭。大家早上就來,晚上也多數來上班。彼此關係很密切。
郝倖仔:林富士說,燈火通明是真的。他讀研究生班的時候和李貞德,還有臺大一位學長,三個人想讀左傳,因為都做古代史,到處打聽左傳誰最厲害,都說杜正勝最厲害,也不認識他,就寫信去問,杜二話不說,那就來吧。每個禮拜一天或是兩天,晚上去杜正勝的研究室,他不收錢的。所以晚上去所裡讀書很正常。我又拿此事向杜正勝求證,他說晚上念書的確會念到12點之後,念到不知東方之既白,或是趴在桌子上睡,或是躺在椅子上睡,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淩晨四五點,外面已經有早起的人起來活動了。他個人最懷念的就是史語所1980年代的十年,那是他人生最幸福的十年。
黃進興:不是所有人都來,管東貴、黃寬重,還有語言所的李壬癸幾位先生都來。和我同輩的幾位常來的,其中一位已經過世了,康樂。那個時候的學者好像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消遣,或者說是寄託,生活空間就是在這個所裡面,自然而然就會以所為家。不少人一天上三個班。早上班,中午休息一下再上下午班,吃過晚飯還有個晚上班,一直做到12點甚至淩晨才回去,第二天早上再來。
郝倖仔:丁邦新先生看到我寫的夜如白晝這一段,說他自己老早就這樣,從二十多歲進所到做所長,一直堅持三班次,這個是有傳承的。特別提到史語所的伯伯們及父親的「全天候上班」。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作為住在研究院裡的孩子群中的一員,從初中到高中,就感覺「他們老上班著呢?」因為住在院裡,所以早上八點就去了,到了中午回家吃飯、小憩,下午兩點又去了。晚飯後,七點多又回去上班,晚上十點、十一點鐘才回來。天天如此,也像沒有週末。晚上走在院裡唯一的一條大馬路上,常聽見這樣的對話:「嘿!某公,吃完飯了?晚上上班去?」「吃完了,您吃了嗎?」「吃了!吃了!」就這麼吃完飯,上班,下班,回家吃飯。一天三次,周而復始。這許許多多、日日夜夜的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是有目共睹的,有歷史記錄的,為中研院早期的,尤其是史語所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深厚基礎,造就一批中外傑出的史學人才。
黃進興:丁邦新、李壬癸、管東貴都是1930年代生,杜正勝是1940年代生,我和林富士分別是1950和1960年代初生。確實是一輩影響一輩。
郝倖仔:黃寬重先生回憶,自己當年決定用一整年的時間閱讀一本書。1980年寫完博士論文之後,即用整整一年的時間閱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200卷,邊讀邊做筆記。對自己後來的南宋研究非常重要,也是人生裡面很值得回憶但不容易再追回的一段。林富士甫進所時,在外面找房子,杜正勝說,幹嘛找房子啊?就睡研究室好了。當然他沒有真正聽話,那樣太累了,會留的比較晚,洗澡什麼都不方便。
黃進興:那時候中研院也沒有食堂,出了院門之外有一些小飯店,也沒什麼好吃的,形態跟現在不太一樣。
郝倖仔:恕我直言,時至今日好像也無甚改觀。院內也就是學術活動中心集中了微風集團的一些品牌速食,也就是拉麵、漢堡一類,最高檔的就是日料。院門之外是研究院路,沿街的小飯店們,看起來還像八九十年代一樣。想吃頓正式的大餐,至少要驅車五公里去南港車站的Citylink Mall。
黃進興:學術活動中心的微風速食還是2018年剛引進的,之前你來的時候都還沒有。我很愛吃裡面的一風堂拉麵,經常去,怕這家店倒閉。
郝倖仔:那時候有一位普林斯頓的學長就住在附近,一群年輕人裡就學長一個結婚的,林富士他們晚上讀完書就跑過去,大嫂給他們煮宵夜吃。平日裡就是很單純的讀書,偶爾進城唱唱歌、喝喝啤酒,一點小娛樂,就很開心。
黃進興:老史語所還是師徒制的階段,好像一個family,大部份都是老師學生、學長學弟的關係,可能更嚴肅、更正統一些。老所長屈萬里生前有一句話,大家都熟悉,說中研院是他「活養死葬」的地方。這其實是老一輩人的共同寫照。相形之下,現在三四十歲這一輩年輕人,可能工作和家庭是相對分開的,學術研究歸學術研究,另外還有自己的家庭生活。要求他們以所為家,未必會接受,會說我在家裡也可以照樣做學問呢。這就是時代的氣氛吧。從我個人來講,我倒覺得年輕一輩活得更輕鬆一些。
郝倖仔:我把您這個「史語所夜如白晝、燈火通明」的典故,拿到所裡逢人便講,多相印證。學人回應各異,很有趣。我揀兩個說給您樂一樂。劉錚雲研究員說,那個時候確實幹勁很大,做到很晚睡辦公室也很常見,不過「燈火通明」並不代表都是日以繼夜,每個人工作習慣不同,有人白天工作,有人說不定是白天睡覺晚上用功。邢義田院士則說,他年長一些,已然結婚,夫人管得嚴,沒睡過辦公室;沒結婚的有不少睡過,王明珂當年最年輕,也沒結婚,但有沒有睡過辦公室,不曉得。我又去問王明珂,他說自己都是準時下班,但回到家裡還是在看書,所以經常被太太埋怨,有時工作忙,也會選擇睡研究室。
黃進興:就是有這些學人實實在在的努力,史語所在國際學術界的能見度,才可能不斷向上提升。我舉兩個例子,關乎我的兩個朋友。一個是曾經擔任過東京大學副校長、並剛剛當選日本學術院院士的渡邊浩教授。他曾告訴我,他在日本遠距離觀察史語所,這十年來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真的是蒸蒸日上。另外一位是你剛才提到的美國漢學家田浩教授。他在大陸學術界交遊廣泛,態度積極。有一次他在美國碰到我,說他可以看到史語所這十幾年來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史語所大概在1980年開始,進入一個重新起飛的時代。有人笑我說:「你的名字不應該叫黃進興,應該叫『黃中興』。那麼史語所就可以在國際學術界更加頭角崢嶸了。」
郝倖仔:這個打趣是對您的所長任期的認可。
黃進興:這就是從事學術行政有時能給人帶來成就感的地方。學術行政人員常常是無名英雄,容易被疏忽。因為我自己長期兼任學術行政工作,所以深知其中相輔相成的道理:研究人員的學術成就是離不開行政的努力的,機構內部、同仁之間應該給予適當的鼓勵與尊重,要給人家一個credit。
郝倖仔:我聽您的秘書們說,您對基層的行政人員都很是客氣,佈置個工作還要給他們鞠躬。
黃進興:史語所今天的聲望和影響是所有史語所人一棒一棒跑出來的。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這個老字招牌,給我們這些晚生後輩今天的發展和創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當年語言所分出去之後,本來也有考慮是否要將原名「歷史語言研究所」改個名字。國際友人和大陸朋友都說,史語所這張名牌得來不易,千萬不要改。最後經過內部外部的一致反映,決定保持原名不變。以示感謝和紀念前輩同仁從1928年建所以來奠定的基礎。更希望能夠在老祖宗的庇蔭之下,堅持我們對學術的理想,繼續匍匐前進。
郝倖仔:名稱依舊,但是史語所的學風、師承、規則、走向都變了。
黃進興:史語所是個老所,舊規矩非常多,有好有壞。或者可以將1980年代之前看成是一個權威的時代。年輕人不要想講什麼話,只有聽的份,講論會上也是多來聽,少發言。那時候等級比較低的就是不發言。
郝倖仔:現在是所有人都發言,剛進所的助理研究員也發言。
黃進興:有一點要說明,80年之前用舊名額進來的那一撥人,像臧振華、何大安、黃寬重,還有一位已經去世的人類學組的宋光宇。他們當時進來的等級是助理研究員,就是講師一級的。沒有你說話的份,只是聽。以前都是學徒制,助理研究員要跟著所裡面的一位前輩,名義上你就是他的學徒,事實上這位前輩也不一定會管你。80年以後就不一樣了,為什麼呢?因為有幾年新體制還沒有產生,助研究員這一級還沒有用,一進來就是副研究員。到副研究員你就是一位獨立的學者了,你自己做研究就不會有人干涉你了。
郝倖仔:以1980年為界,前幾年和後幾年進所的人的心態是不一樣的。杜正勝說以他的理解,學徒制下的年輕人多少有小媳婦的心態。他1980年進來,當時的人類學組主任管東貴先生以副研究員聘他,他的心態就沒有小媳婦氣。許倬雲先生回憶更早十年二十年前的史語所時,也說自己當年實質上等於做學徒,而現在進所的同仁一則斷層,二則很多人到美國留學回去以後,按照臺灣文官制度,有了學位,一進所就當助理研究員,不是像做學徒。也就是說,在許倬雲先生心目中,那些1980年之前幾年進來的人,有了助理研究員的名頭,都已經不算是學徒了。而且他也認為,進所的人員開始兩年不許做別的事情,只許讀書—傅斯年先生在史語所留下的這個規矩,他覺得很好。
黃進興:1980年代的史語所可以說三代同堂。個人年代、背景不同,心態也不同。老史語所撤退過來的老前輩不少還在,中壯年的學者也已經成長起來,又應五年計畫進來一大批甫獲博士學位的生力軍,還有一些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助理研究員。最長者已逾九十高齡,新鮮人還有不到三十歲者,世代差異極大。學術背景更是迥異,老前輩多是早年北大被拔尖來的,亦有遷臺之後於本土養成之學者,更有剛從歐美、日本名校回來的,可謂濟濟多士。
郝倖仔:幾乎整個1980年代,皆為丁邦新先生任史語所所長,從代理到真除,做了八年。聊天時我感歎,新的舊的全揉在他任上,上面老輩還在,得供著;下面年輕人、新思想湧進來了。當時我話音未落,丁先生就提高聲調回應:「你這話讓我很感動,真正是我的知音!」在電話裡我都能感覺到他有一點小激動,好像事隔三十多年,那段分水嶺上的領導生涯還能讓他頗不平靜。他說假如屈萬里和高去尋做所長算第二代的話,底下就是他,他做的時候非常困難,因為老先生們很難伺候,哪個都是老師,至少是老師輩。加之他個人脾氣也不小,做了不少得罪人的事。得罪完了就算了,也沒辦法。他還特別強調,老先生大致都是相當有修養,說話也公平,但也有一兩位脾氣很大,比較尖銳,如周法高。丁邦新激動的語氣和他的點到為止,激起了我的好奇,我拿他的話去找王道還,希望挖深一點。王道還是1982年進所的,他說他親眼看到周法高拒絕退休,大鬧所長室,還寫有條陳,即不想退休的申請,其中一句:有大功於本院。我問何為大功?王說是參加過國際會議,他說周就是倚老賣老,因為當時的所長是丁邦新,周把丁當個小孩。我又問,語言組在董同龢與周法高二人之間,評價似乎更傾向董一些。王說,董同龢走得早,有時候人活得短也有好處,因為人的本性不到那個關頭是出不來的。我又讀到周法高早年的詩作,多次自言「疏狂」、「忤世」。當然可以理解為自嘲抑或是自傲,但是否也可以理解為,反正我自己都這麼說了,別人還能再說什麼。我又在《余英時回憶錄》中看出來,余先生很早就跟董同龢關係好。和丁邦新聊天,感覺他也喜歡董同龢。由此可以推斷董同龢是個比較純粹的知識分子,越是有事功智慧的人越容易喜歡他這一款。
黃進興:董同龢過世的時候是1960年代,史語所很平靜,沒有大事,那是歲月靜好的時候。
郝倖仔:還有一個類似的故事,就是李濟的養子李光周,在美國讀完考古學博士,準備回臺灣的時候,臺灣學界有一位比他年長的正教授打電話到美國去,叫他不要回來。張光直是從臺灣去美國的第一個考古學博士,留在美國沒有回臺;李光周算是第2個,但是回來了。所以在當時的臺灣考古學界,李光周就算是學歷最高的。李光周雖然沒來史語所,去了臺大,但與史語所也算是關係密切,臺灣學界就這麼大,故事都是相通的。
黃進興:李光周本不姓李,是李濟夫人家的人,李濟的親生兒子留在了大陸,在大陸為李濟出了全集。
郝倖仔:像這樣年輕人在圈裡受欺負的軼聞,還有類似像李濟剛一過世,藏書就等於是被人搶走,李光周打官司訴諸於法律,又把藏書拿回來,說到底因為他是李濟的養子,所以圈內不少人不把他放在眼裡。我特別向王道還求證一個問題:李光周有沒有沾到李濟的光?因為李光周是王70年代末在臺大讀書的老師,他乾脆的回答,沒有。我的問題就是個辯證法,很多時候我們認為沾了光的關係,事實上光未必沾多少,瓜落兒倒吃了不少。
黃進興:學術界其實與社會的面向很多元。尤其是臺灣社會,無論政界、商界、學界,通常都是在臺大等幾個本土名校,讀完基礎教育之後,再去歐美拿個學位回來,中研院這邊的研究人員又都在臺大這些名校兼課,所以臺大和中研院就自然而然成了人才集散地,但凡大陸聽著耳熟的臺灣籍名人,大多都有一點與之相關的履歷。
郝倖仔:王道還跟我聊了幾個丁邦新當所長時的小事。所裡有一位同事生活比較緊張,丁邦新跑去安慰他,還當面跟他講,你需要錢儘管開口。所裡還有一位同仁,一天到晚在研究室裡做研究,不肯回家或者說是忘了回家,夫人找到所裡來,丁邦新先把這位夫人勸走,再到研究室請這位同仁回家。這兩個例子是為了下一個例子做鋪墊—1985年王道還去哈佛讀博士之前,在所裡講論會上做報告,講唐代天文學,順帶批評了李約瑟,丁邦新特意來提醒他:「你這麼年輕,怎麼可以批評李約瑟?」—王道還自己也說,當然可以把這句提醒看成是愛護年輕人。但我感覺,他將這三件事情並置且排序的敘述邏輯,應該是不認同丁邦新用大家長的方式處理學術問題。作為旁觀者,我只能說,在這個分水嶺上,新的舊的揉在一起,這個所長真是不好當。
黃進興:總之,史語所是個老所,難免會有一種師徒之間學徒式的舊風氣。這又牽涉到史語所的另一個傳統,大家都知道傅斯年老所長提倡拔尖主義,即1937年之前,史語所只要北大的學生。當時他在北大教書,北大當然是最優秀。
郝倖仔:只有一個傑出青年是清華的,就是夏鼐。夏鼐考上牛津,要去英國學考古學,出國之前來史語所實習,被傅斯年派到安陽發掘現場。檔案裡有一封夏鼐1935年寫給李濟和梁思永的信,請教學業安排事項,因為留學期限僅定兩年,「如每校僅住一年,雖可廣泛受教於諸位大師,但對於學無根柢之人,恐漫無頭緒,所得反少;如專在一校攻讀二三年,從一名師遊,先讀基本科目,進而深求特殊研究,反倒更為系統。」梁思永給他的建議是,可先在倫敦大學攻人類學,以造成根柢,然後赴愛丁堡大學從Childe習考古學。這種計畫長在先求廣涉,熟悉考古學範圍內之各種學識,如欲系統研究,再以從學一校即可;並言赴國外習考古學之目的,一學田野工作,二學博物院保存古物之技術,三須注意人類學,四為參觀流入國外之中國古物。這些建議今天看來也是金玉良言,實錄以饗學子。(檔號:元545-2)
黃進興:夏鼐回國之後也是入職史語所,1949年沒有來臺灣,留在大陸創立了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周一良也類似。燕京大學畢業後來史語所任助理員,後被燕大推薦赴哈佛大學研究,臨行前也是向傅斯年請教注意事項及課程選擇。當然周一良和夏鼐都留在了大陸。這樣的例子老人們幾乎人人都有。所以說,史語所考古組的前輩們通過安陽發掘,發現和培養了一大批有田野經驗的年輕人,為兩岸的考古事業創造了有生力量。
郝倖仔:我看到您和杜維運先生合作編輯的《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選入周一良史學研究處女作—〈魏收之史學〉,此文首發於1935年的《燕京學報》,是周一良在燕京大學讀本科時的課程論文。
黃進興:老史語所裡有一個人才培養模式很有價值,現在沒有了。就是從碩士班在讀的學生裡,吸收優秀分子進所工作,培養兩年之後,送去美國讀博士,拿了學位再回來服務,成為大專家或者院士。年輕人進所確實有很多向老先生學習的機會。周一良在老史語所一年的時間裡,學問精進很快,因為得以與陳寅恪通信論學。當然了,後來周一良留在大陸,投身運動,批判胡適,又被陳寅恪寫諷刺詩,那就都是後話了。1999年,陳寅恪誕辰110週年學術會議上,周一良發表〈向陳先生請罪〉的發言。陳寅恪甫去世,史語所這邊也召開追思會,渡臺同仁共同緬懷。
郝倖仔: 於碩士進所的經歷,王明珂院士用「困學」二字來形容:因為是碩士畢業就進所,在所裡肯定是非常低的等級,也就是助理研究員進來。自己一邊做研究,心裡也知道,不出國讀個學位,是沒有辦法的。從進所直至出國之前的這兩三年時間,是一個「困學」的過程,即知道自己的不足,到了國外,就知道讀書要讀什麼,所以就像一塊被榨乾了的海綿,拼命想修課,想學新的東西。這跟出去就是為了讀個學位是不一樣的。當然沉潛期的自省和自察,勢必伴隨著青春的困惑和迷茫,方才稱之為「困學」。這個說法讓我很受觸動,採訪劉錚雲研究員時提及此說,劉幾乎是咬著牙說,他那是碩士就給挑進來的……。感覺潛臺詞好像是,「困學說」聽上去艱苦勵志,其實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因為碩士進來是天大的好事。
黃進興:碩士進來確實都是拔尖的。像王汎森、林富士,都是這個路子進來的。事實證明,也確實沒有看走眼。至於「困學」,在於個人的自我要求。
黃進興:關鍵是聽話。聽話是「學徒制」的表現,但也是惺惺相惜,是人與人的信任。年輕的時候,要跟對人,要聽話。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博士,美國史丹佛大學訪問學者,中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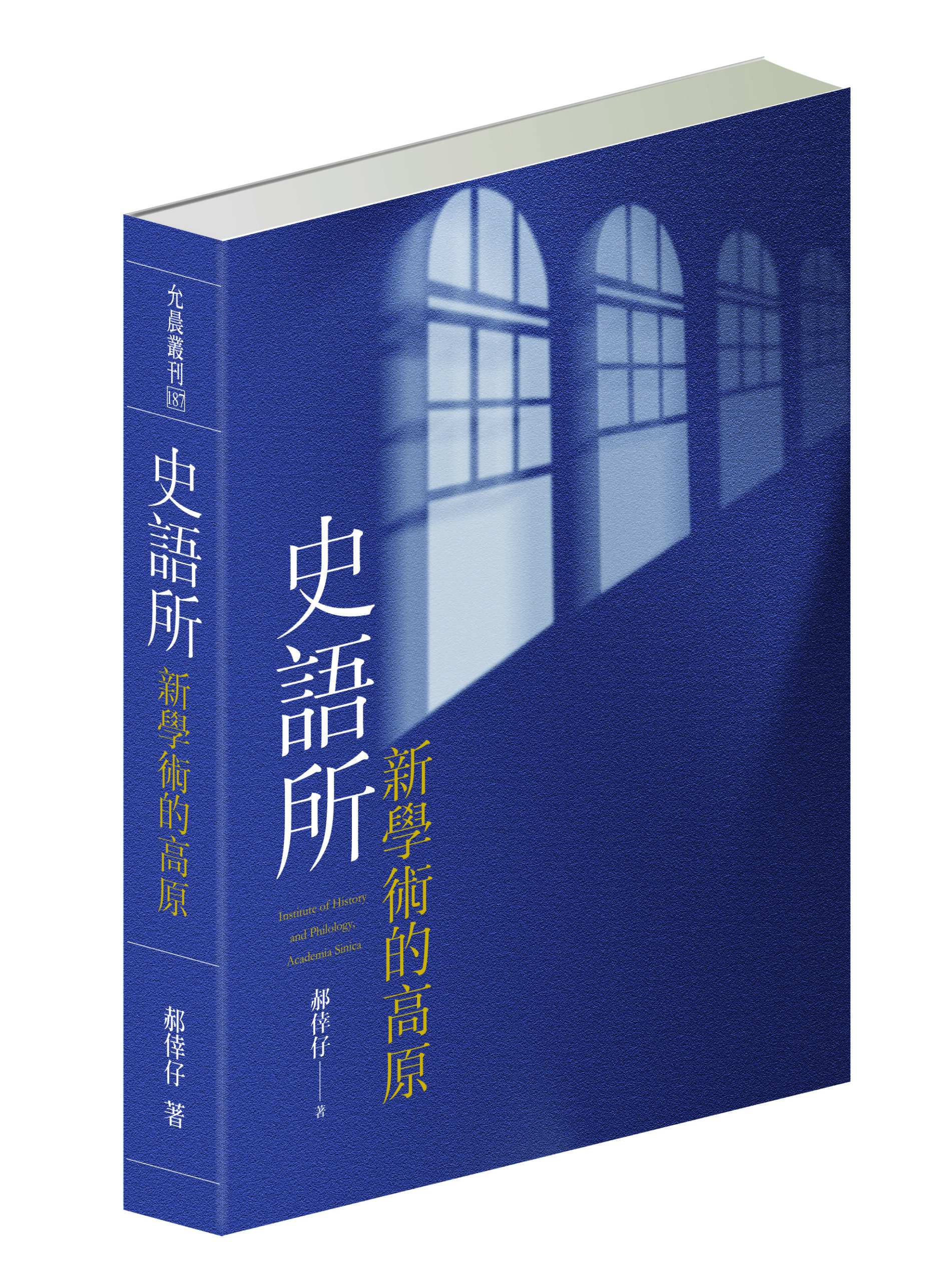
書名:《史語所:新學術的高原》
作者:郝倖仔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3月
- 【書摘】《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與社會學觀點》 - 2024 年 4 月 26 日
- 【書摘】《鐵幕降臨:赤色浪潮下的東歐》 - 2024 年 4 月 25 日
- 【書摘】《美利堅國度:十一個相互對立的地區文化史》 - 2024 年 4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