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政策三十年,從禁絕到依賴
我一直沒有真正離開第一廣場。
有段時間,我又搬回這棟大廈,因為我想瞭解更多移工的故事。有些移工即使努力也沒有擺脫自己命運,因此他們的聲音被忽略了,因為媒體上呈現的都是為了那些追求英雄故事的讀者而寫的。可是我聽過的移工敘事,很多人還在個人野心與僵固制度中,苦苦掙扎。
當時任職的媒體對此做出慷慨安排,允許我以中部特派身分繼續報導。於是,我再次搬進第一廣場,這次換到一個更小的合租房,一戶被隔出三個房間,一間住著行動不便的老女人與她的印尼看護,另一間是一對年輕情侶與剛出世的寶寶,我們的房間僅隔一道牆,在半夜經常被尖銳的嬰兒哭聲驚醒。
還有一個我沒說的原因。當我搬回臺北後,我發覺自己已習慣一廣的生活節奏。每個星期六,早上八點,陽光橫斜地灑進我的房間,移工便陸續聚集在一樓廣場,他們都在等待十一點,等大廈的鐵捲門拉起。
大廈透不進光線,裡頭的人很難感受時間的流逝,只能依靠人潮判斷。這裡像是慢熱的鍋爐,熱鬧程度不斷遞增,在週六晚上達到第一波高峰,這晚有些移工不必回宿舍,得以享受整晚的夜生活,大廈的不同角落傳出電音舞曲,有專屬菲律賓人、印尼人的舞廳,也有少數的移工同志酒吧。週日中午是另一波高峰,菲律賓移工在十三樓的教會做禮拜,其他國籍的移工趁機與四散各地的親友見面,約在一廣吃頓家鄉味,互訴思念。
重回一廣以後,我和店主們一同領略著變化。有段時間,市府文官頻繁造訪,他們認為挽救這棟凋敝大樓的唯一解法是招商,找到臺北來的商人買下四樓與十二樓,投資五億元,將四樓規劃成中高價位的商務旅館。
當時大廈的胡總幹事跟著瞻前顧後,我們在樓裡碰過幾次,他似乎不喜歡有記者四處探聽,生怕我攪局,「市政府跟我們有心想要做啦,我們要讓第一廣場再現風華。」他見一次說一次。
財團買下大樓的消息,很快在店主圈傳開。在三樓經營東南亞超市的柯姐,指對面賣衣服的攤位告訴我,「一件賣一兩百,外勞生意就是要很便宜啊。」經驗告訴她,「外勞的消費就是這樣子,要做中高價的比較困難。」
來自越南的阿萍,她的生意遍及六樓酒吧、二樓越式餐廳,及延伸至電梯口的茶水攤,已經在一廣開店超過十年。當她知道有財團預計買下大樓後,沉默了幾秒問:「那我們租金會不會提高?」「如果有變化的話,這家餐廳我就要收起來了。」「我講真的,沒有辦法做了。」
類似的開發案,其實有跡可循。臺北車站的二樓商店街是典型案例。
一九九◯年代臺北車站曾是著名的外勞商圈。一九九三年時,臺鐵與承租人金華百貨發生租約爭議,在爭訟期間,金華百貨不願遷出,臺鐵也無法招商轉租。在這段過渡期,經營移工生意的店家得以以低廉租金進駐車站二樓。
直到二◯◯五年,法院判決金華百貨敗訴,微風廣場取得地下一樓至二樓的經營權,兩年後美食街重新開張,改造得明亮晃眼,再也看不到移工身影。
「他們本來好好的,你來做高級化的規畫,很多東南亞配偶的店家就會被擠壓出去。」臺大城鄉所教授王志弘,他觀察過好幾個東南亞族裔商圈的改造案,指出這類故事的結局。
我希望他的說法是錯誤的。短租一陣子後,由於新聞工作調度,我必須搬回臺北。每次再回到第一廣場,我感覺自己趕不上周圍的變化。原本十三樓的菲律賓教會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家近年如雨後春筍出現的創業孵化器公司。柯姐的東南亞超市也迎來最大的競爭對手,擁有菲律賓(EEC)、印尼(Index)與越南(Vnex)三家貨運品牌的集團,在專營東南亞移工的行業裡,貨運量、食品進口量與薪資轉帳金額都是業界第一,他們在二樓開設占地三百坪的東南亞超市旗艦店,裡頭還附設免費的與休息室。
大樓改名成東協廣場以後,商圈日益蓬勃。一年以內,周遭十坪店面的租金,從兩萬漲到四萬五千,只要有人退租,馬上有人承接。
某天,當我回到一廣,想再品嘗最道地的越式烤豬肉時,阿萍的兩間越南餐廳、複合式KTV,與二樓電梯口最熱鬧的茶水攤與理髮鋪,全都消失了。
我悵然若失。
廣場中央的金字塔,過去是移工席地而坐、等待朋友的地方,如今四周也圍起鐵欄杆,只留下一側改裝為木棧階梯。不久以後,網路上有段影片,當幾名移工坐在階梯聊天時,十幾名警察無來由地驅離他們。
當土地開發、城市拉皮等計畫出現,就會有人想要把這些移工,連帶他們聚集的隱蔽空間清理乾淨。「就像核電廠一樣,每個人都需要用電,就是不要蓋在我家隔壁。」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比喻。
不過,移工在臺灣的故事最好從頭說起,透過對於歷史的簡單回顧,或許能讓我們對移工能多理解一點,說教意味也會淡一些。
缺工困境:產業轉型與升值壓力
移民工增加是全球化的現象,臺灣需要外籍移工的原因可以從很多角度說明。找不到工人,是一九八◯年代臺灣老闆共同難處。一九八七年,行政院主計處對勞力短缺進行調查,製造業平均有六成五的廠商表明缺工,營建業則有七成六的廠商勞力短缺,總共缺少約三十二萬名勞工。
缺工問題是社會結構轉變的結果。一是臺灣從戰後嬰兒潮的高出生率,轉為低生育率,勞動人口規模縮小。其二,一九六◯年代以來,臺灣維持近二十年的經濟高成長,資本湧入服務業,讓許多年輕人離開工廠,投入光鮮亮麗的服務業,致使製造業面臨嚴重的產業缺工。
美方壓力讓臺灣的產業發展雪上加霜。一九七八年,美國懷疑臺灣長期操縱匯率,以致連年對美貿易順差,也批評臺灣對於勞工保護不足。在美國堅持下,臺灣在一九八四年通過《勞動基準法》,保障工人最低工資與休假等權利。一九八六年,臺幣大幅升值,嚴重打擊臺灣以廉價勞動力為美國工廠代工的獲利方式,加上勞工對薪資福利待遇要求提高,造成大量中小企業工廠關廠歇業。
部分工廠業主設法生存,私下引進非法外勞。這裡有個地方要釐清,儘管報紙用「非法外勞」指稱,但所謂的「非法」指的是他們使用旅遊觀光簽證在臺灣工作,並不是他們從事非法工作。總之,這些主要來自泰國、菲律賓和其他東南亞各國的外藉勞工,通常持十四天的觀光簽證入境,然後逾期居留。透過旅行社員工中介,雇主只需以當時最低工資的六成給薪,在缺工情況下,這些雇主也願意提供外勞住宿與來回機票。
沒有確切的數字可以得知當時臺灣有多少外勞。一份警政署的估計,一九八八年逾期居留的外國人約有一萬三千人;如果根據經濟學者張清溪的估算,該年年底臺灣至少有四萬名移工; 如果採媒體報導,市井傳言以觀光名義留在國內的外籍勞工已有七萬人。
無論如何,在一九八◯年代,正式立法引進外籍移工前,工廠偷偷聘僱外勞並不希罕。不過,當時政府的態度是強力查緝非法外勞,勞委會重申不引進外籍勞工,觀光局對非法引進外勞的旅行社施以停業處分。
「政府對引進外籍勞工,自始至終都是採反對姿態,不會因任何因素而改變想法。」時任勞委會主委趙守博,受訪時不斷舉西德為例,說明引進外籍勞工恐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臺灣應該引以為鑑。
德國所建立的移工制度可以追溯至二次大戰以後,歐洲大陸景氣快速復甦,工作機會不斷增加,在當地很快就找不到工人可用。西德很快發現附近的國家可以提供更多勞動力,於是開始從義大利、土耳其等國招募客籍工人(guest workers),並從法律上做出區隔,稱呼為「客工」在於他們不具備長期的移民權利,只是暫時性的補充勞工,而使用這些外籍移工的最大好處,就是他們招之即來、呼之即去,在亟需人手時招募他們,在勞力過剩時立即遣散。
歐洲這波戰後招工熱潮,一直到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爆發後才停止。當歐洲經濟發展放緩,各國逐步停止招募移工。按當初移工政策的設想,德國政府認為這些移工不能歸化成移民,不久後就會返回母國。然而,移工在沒有工作以後,並沒有離開,由於歐洲人權公約保障移工家人團聚的權利,許多土耳其移工甚至帶著親人返回德國定居。
一份報告顯示,當西德一九七三年終止移工政策以後,隔年土耳其移民的人數增加了二十萬人。在出口衰退、就業低落下,社會瀰漫反移民的氛圍,抱怨外來工人搶走工作,甚至引發嚴重的種族歧視。當時德國一份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八成民眾都反對再聘僱移工。 時至今日,當時引進移工的政策仍影響著德國,政府不得不花費更多金錢鼓勵土耳其移工返國,或設計一連串服務政策,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除了德國的前車之鑑,臺灣政府也有意引導產業轉型。一九八◯年設置新竹科學園區,選定資通訊產業為重點發展工業後,政府逐步減少給勞力密集產業的補貼。這是因為在資本發展過程中,如勞力密集的紡織業、成衣業是典型的夕陽工業,這種只需簡單的科技,仰賴便宜工人的產業,從歷史上看是各國工業化的先鋒,也是在國家轉型成富國後最早被割捨的部門。
外交打擊,臺灣產業更形困頓
臺灣政府起初拒絕外籍勞工的態度看似斬釘截鐵,後來為何會開放引進移工?重要轉折與外交上的接連打擊有關。在一九七◯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改變外交策略,打算聯合中國以制衡蘇聯,逐步向中國靠攏。失去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七一年自願退出聯合國,一九七八年正式與美國斷交,隔年,美國與中國人民共和國建交。成為軟性威權的國民黨當局擔心,經濟衰退可能從而影響統治的正當性,於是開始拉攏居領導地位的臺籍企業家,允許他們組織的工商團體介入政治。
「政府不能再否認國內已有不少外籍勞工的事實,應該要務實處理,而非刻意忽略。」豐群水產董事長、時任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的張國安多次向政府呼籲。
逐漸對社會失去控制力的黨國,在一九八七年宣布解嚴,兩年以後完成立法委員增額補選,民進黨拿下二十一席,近三分之一席次,他們得以透過質詢施壓政府。當時,臺灣政府一面強力取締外籍勞工,一面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此條例帶有強迫傳統產業自動化的構想。但對許多中小規模的公司來說,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昂了。如果他們不能僱用外籍勞工,只有關門一途。當非法外勞被遣送回國後,業者因缺工被迫關廠,上百家傳產業者進而成立「全國廠商缺工聯誼會」,積極向剛通過補選的民進黨立委陳情,主張合法引進外勞,來彌補不足的人力。
臺灣缺工的狀況,並不是在充分就業下,有些工人還是沒有工作做,為什麼資本家仍經常施壓國家開放勞工市場?對此,遷移學者以「分割勞動市場」(segmented labor market)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後期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一種是有保障、有技術、待遇又好的工作,還有一種沒保障又辛苦,在英文裡被形容為(Dirty, Dangerous, Difficult,亦稱)的工作。大部分本國人都想做有保障的好工作,可是勞累的工作還是需要人力,想要有人做,雇主當然可以提高底層工作的薪資,直到有人願意接受為止。
但是,拉高底層工人的薪資,連帶地往上所有人的薪資都要調整,所以雇主會盡力維持這兩類工作的界線,創造出雙元就業市場。過去,這類不穩定工作經常由婦女、青少年或原住民來從事,但當勞工意識抬頭,開始跟著要求提升待遇或福利後,最終雇主願意做出的調整,就是僱用不挑剔工作、也不會斤斤計較的外籍勞工。
臺勞被描述成投機的人
於是,資本家把臺灣勞工描述成投機的工人,不是資本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大約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由於民間社會的游資浮濫,有些民眾為求一夜致富,沉迷於大家樂這類數字遊戲中。當時中國力霸工程經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說,「目前受大家樂影響,建築工人經常無心做『黑手』的勞力工作。」這種說法直接把缺工的原因歸咎於工人不肯腳踏實地、只想投機的心態,根本是錯誤歸因,實際上是雇主不願拉高底層工人的薪資待遇。
把臺灣勞工塑造成好逸惡勞的對象,可能也與解嚴後的抗議活動有關,這時的抗爭以環保運動與勞工運動為主,前者集中在自力救濟的反公害行動。一九八六年反杜邦設廠成功以後,成為後來反公害運動的範本,被繼續運用在「反五輕」、「反六輕」、「反李長榮化工廠」。這類抗議經常造成企業停工、做出補償,對石化產業影響最大。
臺灣工人比以往更注意自己的權利,懂得以法條跟工廠老闆斡旋,或運用罷工、怠工等「順法抗爭」的方式,得到法律內的勞動保障。根據社會學者吳介民的調查,一九八八年是解嚴後勞工運動的高峰,此前平均每年五十件左右,當年暴增至二百九十六,議題都集中在爭取年終獎金的事情上,又稱作「年終獎金浪潮」。因此,一些紡織廠在景氣平緩後,寧願將老舊設備淘汰,也不願繼續生產,他們指責如今的工人不再有敬業精神,而是只會跟老闆討價還價「勞工意識」。
「雖然勞工運動、環保運動在社會進步過程中在所難免,但我覺得現在好像偏差了,如果這樣下去,我看將來臺灣的經濟發展會有問題。」時任臺塑總經理的王永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忍不住抱怨。
資本集團將缺工論述成,臺灣勞工妄想一夜致富、勞工運動對企業允取允求,引進外籍勞工才是解方。「紡織業已經對一般勞工不具吸引力,面對工人不足的情況,業界希望政府能盡快引進外籍勞工。」
企業強烈要求、重大工程進度緩慢,加上非法外勞日益猖獗,到了一九八◯年代尾聲,臺灣政府已經有引進外籍勞工的想法。為了挽救低迷經濟,政府大筆投資公共建設來創造內需,規劃了臺北捷運、北二高等十四項重大建設,但工程一直延宕。當時勞委會的調查,攸關國家建設的重大工程,勞力不足高達一六%,之後的六年國建計畫如果同時動工,預估短缺四十萬名工人。最終,政府在一九八九年開放重要工程的承包商引進外勞,揭開臺灣合法引進外勞的序幕。
作者為南投人,臺灣大學新聞所畢。曾任《報導者》記者、《鏡週刊》人物組特約記者。傅爾布萊特學人(Fulbright Scholar)、中研院亞太中心、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獲臺灣卓越新聞獎、曾虛白新聞獎、亞洲出版協會新聞大獎、香港人權新聞獎。攝影作品曾獲新聞攝影大賽系列照片首獎。合著《廢墟少年》獲Openbook閱讀誌年度中文創作、鏡文化「華文創作類」年度好書。在書寫中平衡宏觀的社會分析與微觀的生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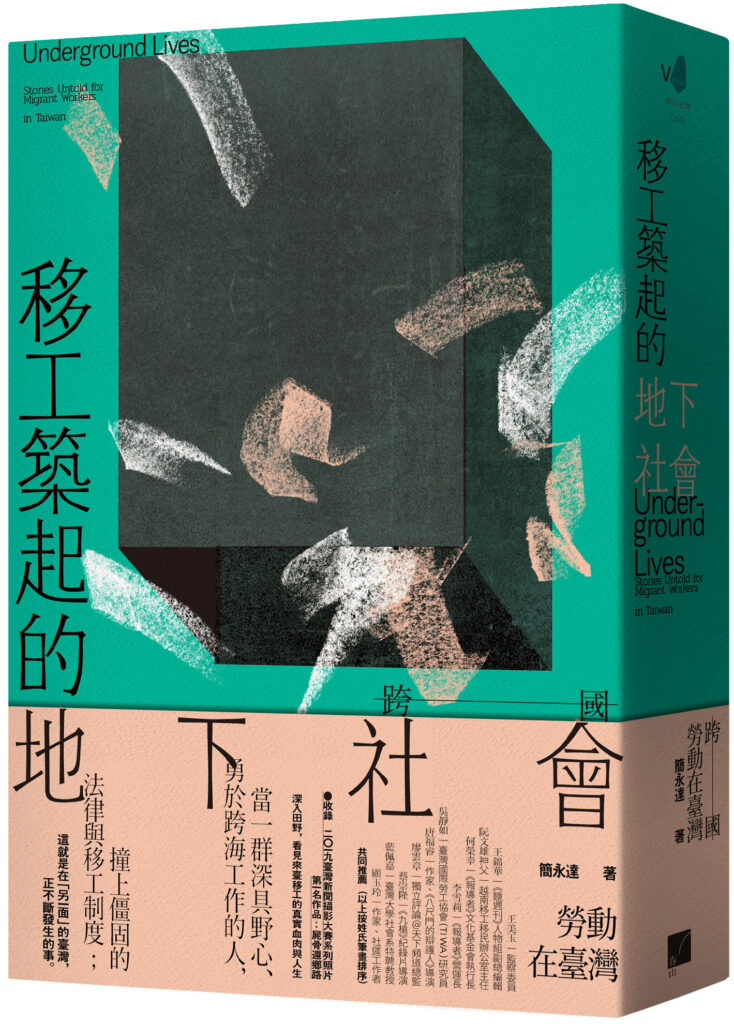
書名:《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
作者:簡永達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3年10月
- 【書摘】《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 - 2023 年 11 月 17 日
- 【書摘】《城中一座島》 - 2023 年 10 月 13 日
- 【書摘】《傅柯的多重人生》 - 2023 年 8 月 2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