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漩渦中去的。你一個人袖手旁觀,恐怕很無聊吧?我很同情你。對於歷史的動向,任何一方面你都無以為力。縱使你抱著某種信念,願意為一方面盡點力量,但別人卻不一定會信任你。甚至懷疑你是間諜。這樣看起來,你真是一個孤兒!──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1978年是美中臺關係正式進入轉折的關鍵一年。這一年,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否定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徹底掃除文革政治遺緒的同時也標誌著「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這一年,因水門案與福特落敗等等因素而延宕的美中關係正常化進程,也終於翻到結局一章,美國透過正式外交管道告知蔣經國政府,將於隔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與中華民國斷交。「斷交」消息傳出後,反對運動人士聯名發表了〈黨外人士國是聲明〉,主張「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來決定」。
「不受極權政權之統治」
早在前一年卡特政府宣布「一個中國」政策原則時,臺灣的長老教會就發表〈人權宣言:致美國卡特總統〉以為回應,其中聲稱「面臨中共企圖併吞台灣之際,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面臨地緣政治變局,有別於蔣經國政府「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的被動回應,臺灣民間社會不約而同以「住民自決」的呼籲來正面回應。
《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以美國政府、國民黨政府以及臺灣社會三方的互動進退為織理,交織出臺灣在戰後直至李登輝開展民主化,重塑中華民國政權的複雜政治歷史,而住民自決則始終是個連貫各方,或隱或顯的主軸。它的初登場始於1949年,彼時國民黨在內戰中敗象已露,而臺灣島內的臺獨運動又不成氣候時,由於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對於臺灣的主權歸屬,美國開始考慮《開羅宣言》之外的方案,也就是說以住民自決的方式,由美國或盟國暫時託管。
儘管隨著韓戰爆發,加上臺灣本地並未出現如波蘭人、芬蘭人意欲脫離帝俄統治的反中強烈獨立意願,《開羅宣言》以外的另一種方案不了了之,但在這個過程中,依然留下了臺灣主權歸屬未定的伏筆,其中所預設的中華民國政權與臺灣人民並非一致的政治框架,更是在美中關係正常化後成為美臺關係的基調。1950年,彼時是杜魯門外交顧問的杜勒斯,在與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討論臺灣歸屬問題時說「開羅及波茨坦協定並未設想台灣人民應受極權政權之統治。此種可能性實非當初所能預料。美國政府……深感臺灣人民對於此事,應有表示其意願之權利。至於臺灣人民是否將棄絕國民政府,美國政府不能提供任何保證」。
不只表明國民政府與臺灣人民並非一致的國際法理基調,杜勒斯這段話也同時透露了美國在思考臺灣問題,從彼時的杜魯門到警告中國介選的拜登,所持的基本態度,也就是威爾遜在世紀之初對於門羅主義的重新詮釋,「每一個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身政治體制,有不受阻礙、不被威脅、不必恐懼決定自身發展道路的自由」。住民自決原則不僅僅是美國現實地緣政治的託詞,它也反映了美國從戰後全球冷戰格局到後冷戰全球秩序的重塑,一個根本的原則:只有所有的民族都「不受極權政權之統治」,這個世界才有永久和平的可能。
阿姆斯壯的預測
對於其身後的臺灣政局,蔣經國究竟有什麼安排?關於這個問題歷來多有爭議,持正面態度者將蔣經國晚年的解嚴與容許組黨視為其「推動」民主化的明證,持否定論者則主張蔣經國不過意識到自第三波民主大浪已無從逆轉。某種程度上,雙方的立論都因蔣經國比自己預期更早的離世,而無從驗證。
從近年公開的蔣經國日記可以發現,他本人對「民主」是沒有好感的。擔任行政院長任內,他在日記中批評代議士的問政「往往捉小放大」,並且質疑「這就是所謂『民主政治』的方式,把精力時間放在這裡,對國家人民究竟有多少益處,乃很大疑問」。
蔣經國也在日記中自問「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也覺得選舉是「勞民傷財卻又不得不辦」之舉。對於許信良的脫黨參選,他的反省是「各種選舉美其名曰民主,或謂為民服務,而事實上則為名利而爭也,並且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政治上最卑鄙和惡劣的方法,可以在各項選舉活動中看得最清楚。可悲!可嘆!」從蔣經國在日記中對民主的反感態度來看,他不可能是「民主推手」,只是,歐洲的民主化浪潮給了他警惕,這是他晚年既放任特務針對「黨外」特定人士進行過激行動,又在體制上相對寬容反對勢力,限縮打擊對象,看似矛盾態度的主因。
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蔣家黨國政權在臺灣的崩潰幾乎無可避免。近年來的臺灣政治研究,包括本作《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都指出美英情報與外交部門對於臺灣社會省籍衝突的掌握,例如該作所引,住臺五年的阿姆斯壯在調任前的報告中大膽預測「臺灣化」將侵蝕中華民國對本土臺灣人的控制,「1984年臺灣人將會得到真正的政治權力,中華民國將終結」。
1984年,蔣經國政權完全不顧美國在《索拉茲修正案》中所傳遞的政治訊息,放任特務部門發動「江南案」,美國偵察當局更是掌握蔣孝武涉入江南案的證據,對於蔣經國及其政權來說可謂沈重一擊。蔣經國不可能對80年代以來特務部門的激進行動完全不知情,他在日記上的沉默也並非難以預見,「領袖」在封閉決策圈中的角色為何,始終都是一個謎,而這也正好是極權主義政體的特徵之一。但蔣經國認定「黨外」、海外的台獨團體與中共是「三合一的敵人」的「政治路線」,決定了體制特務的「動手」對象。
回頭看阿姆斯壯的預測,1984年這一年臺灣人還沒有得到真正的政治權力,但江南案已經透露了蔣氏政權殘酷暴力背後的窮途末路。
豈管身後洪水滔天的蔣經國
如果蔣經國是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最起碼在美中關係正常化勢不可擋時,即應思考國民黨政權在其身後的處境。如果民主化不是蔣經國對其身後國民黨政權的選項,至少,本土化要是後蔣經國時代的合理選項。
然而,正如《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所解讀,蔣經國執政初期的「吹台青」政策,實際上是為了排除蔣介石留下的元老,建立自己政治班底,並同時以提拔臺灣人來獲取改革讚譽與民間支持的政治舉措;蔣經國也同時提防中央民代增額選舉成為反對運動者進入國會挑戰威權體制的機會。蔣經國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在態度上是消極,他在日記中心心念念的從來不是國民黨在他身後的未來,更多是發洩不如死去的悲憤情緒,他所謂「救國護黨」,從來不涉及對政權危機的系統性應對。蔣經國的早逝確實讓後人無從得知他到底會是容許異議勢力的卡達爾?還是堅持特務治國的何內克?不過,更可能的理由是他從來沒思考過,只求在世時平安過渡,豈管身後洪水滔天。
蔣經國對身後的缺乏意識意外讓國民黨政權沒有長成一個本土化的威權體制,若果如此,鑑於美中關係正常化後大國政治的現實考量,美國更大可能會接受一個威權但反共的體制,其威爾遜主義將無從施力。
70年代是人權理念蓬勃發展的期間,它有一個非常偶然的機緣,也就是美國總統卡特對人權論述的大量援用,這是民主黨在70年代初期「人權轉向」的後果之一。民主黨與卡特靠著人權的道德訴求贏得了大選,人權是一種幾乎無從反對的「政治安全」理念,美國因此在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外,找到了對付蘇維埃的思想武器。然而,將人權純粹化,因而無從提出治本政治或社會經濟方案,其「去政治化」傾向見於美國以此發動的各類國際援助,也成為批評者抨擊的要點。臺灣的個案於是顯得奇特,海外臺灣人的政治遊說成功掌握了人權理念躍上政治舞台的契機,開闢了《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所說的「第二戰場」,與島內透過地方選舉凝聚的民主壓力,分進合擊迫使威權當局不得不退讓。
從各種角度來看,臺灣戰後的政治歷程獨特的難以複製。住民自決在戰後詭異的地緣政治情勢中偶然成為臺灣主權歸屬的隱然選項,雷震的組黨運動從某個角度上可能會是緩衝其衝擊國民黨政權的政治方案,蔣氏父子對臺獨的戒懼,乃至於蔣經國豈管身後洪水滔天的短視,意外讓臺灣免於成為東亞尼加拉瓜。
《共產黨宣言》中的膾炙人口的「幽靈」比喻,本意指一切撲滅共產主義運動的激進手段都不過是向幽靈動手的徒勞之舉,在臺灣這個難以複製的戰後政治歷程中,住民自決作為遊蕩的幽靈意象,有著更複雜與深刻的意涵:既是自由民主大國無法以現實主義為由斷然捨棄的幽靈,也是威權領袖無能直視只能選擇無視的幽靈,當年〈黨外人士國是聲明〉申明「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其中的「強權」在今天的臺灣已經有了完全不同的想像,不變的是,住民自決依然還是驅動數代臺灣人在透徹自身孤兒運命後,欲使之道成肉身的幽靈。
一個幽靈,住民自決的幽靈,在臺灣遊蕩。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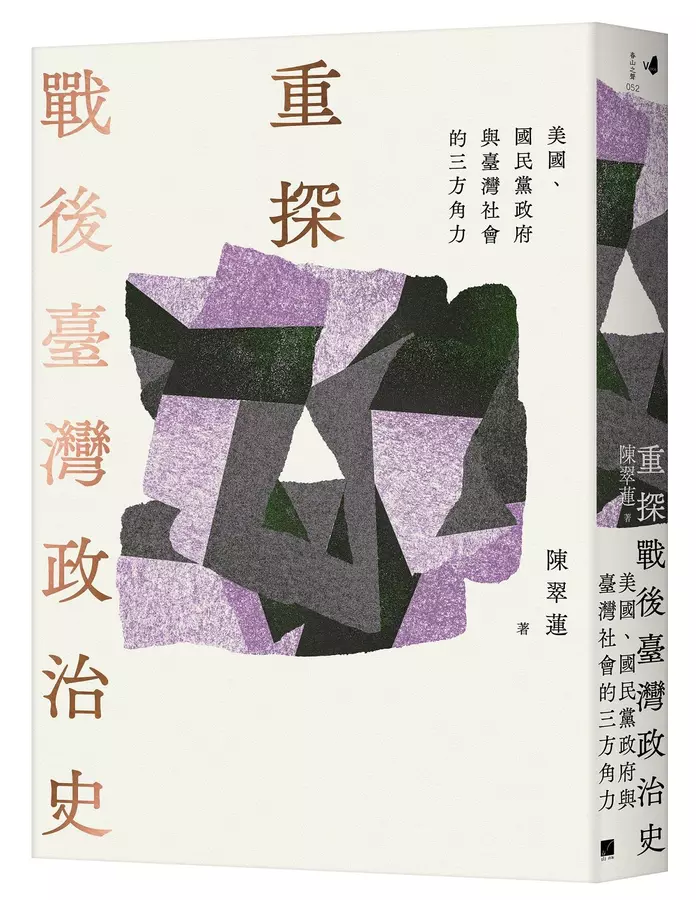
書名:《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
作者:陳翠蓮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時間:2023年11月
- 外星球與墓地:康德誕生三百年後的永久和平 - 2024 年 4 月 23 日
- 怎麼看《三體》才不會像小粉紅? - 2024 年 4 月 5 日
- 2014何以成為全球反中帝零年 - 2024 年 3 月 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