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人卻是一種高貴的動物,增飾其骨灰,盛大其墳墓,無論生死,都不忘舉行堂皇的儀式,使之絢爛莊嚴,以此表現其天性之醜劣。──托瑪斯·布朗爵士,《瓮葬》
後人對於《失樂園》的隱微教義有一個近乎共識的觀點:可愛迷人的反派角色撒旦,才是這個文本的真正主角。即便恩格斯的評語「讓我們不要忘記密爾頓,這位首先為英國弒君辯護的人」,其實是移花接木的結果,人們還是很難不被《失樂園》中那個膽敢反對上帝,在天上發起戰爭,在人間發起密謀的撒旦的風采所吸引。
「撒旦派」(Satanism)的解讀傳統其來有自,可能要歸功於18世紀的浪漫派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在他的長詩《天堂與地獄的婚姻》中,布萊克直把撒旦當成了解放英雄,「密爾頓寫天使與上帝時像是帶著枷鎖,而寫魔鬼與地獄時則自由奔放」,布萊克把密爾頓的顯白的情緒歸之於他「詩人」的氣質,「原因是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就會不自覺歸於魔鬼一黨」。
現代盜火者撒旦
布萊克當然不會知道密爾頓的原意肯定不是讚揚撒旦,他無視《失樂園》的神學道德教誨,無非是刻意的顛倒,撒旦的罪惡,他的欲望與反叛,成了浪漫詩人眼中高貴的「現代氣質」,在布萊克眼中,撒旦的叛逆是「通向智慧宮殿之必由」。這樣的解讀,乃至於往後把《失樂園》中的撒旦視為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的雪萊,無疑離經叛道,儘管密爾頓的描寫確實動人,但無論如何,撒旦都不可能是密爾頓筆下的正面角色。不過,沒有基督教傳統的社會,對於「撒旦派」的詮釋,就毫無心理障礙了,此即魯迅所謂的「摩羅詩派」,也即「歐人謂之撒旦」,魯迅指的是「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
事實上,撒旦被追捧為真正主角並非全是扭曲,全無來由。畢竟《失樂園》中充滿了「王治」的意像:上帝是天界之王,萬王之王;墮落的天使撒旦是地獄、幽冥世界(Pandemonium)之王,邪惡世界的王;而亞當是伊甸園的王。作為聖經的二創,《失樂園》描述了撒旦對於這個王治世界的顛覆,撒旦本是「天使群中,排名最前、最有能力、最受恩寵、超群絕倫」,然而卻對「聖子那日受其偉大天父之尊崇並宣稱其為彌賽亞、受膏抹者,懷有滿腔妒意,又由於驕傲自恃,見不得聖子所受尊崇,乃自忖受害」,在被上帝打入地獄後,撒旦將陰謀奸詭動到了人間,於是有了後來亞當與夏娃面對撒旦的誘惑而背叛上帝的情事。
撒旦之所以讓現代詩人傾心的原因,在於他顛覆了上帝的階層秩序,撒旦對於眾天使的宣講,堪稱現代的革命宣言先聲,他聲稱「階級、地位是不會跟自由衝突的」,並主張「就理性上還有權利上而言,有誰敢僭取王位而稱帝於我們這些生而與其平起平坐者?」。撒旦的訴求是平等,他對平等的呼籲來自於不滿屈居於聖子之下,然而,他希望從天界的戰爭中掠取的,卻遠遠不只平等,撒旦在向他的反叛軍喊話時說,「單單自由未免索要太少了,我們要的更多:榮譽、主權、榮光還有聲名」。
撒旦是個充滿激情與欲望的角色,這讓他更能讓現代讀者認同。《失樂園》中的撒旦與亞當是「現代人」的兩種形象,如果現代讀者傾向用革命派的形象帶入撒旦,那麼《失樂園》中的亞當在現代讀者看來,難免是一種尼采式的末人形象,他成天漫談神秘學:他的受造與上帝造主,關注的是他的生命本身:身體的機能、睡眠、人獸之別以及來日的計畫,討論的是夢境與星辰大海,還有讚頌夏娃的美。《失樂園》的當代讀者如果更傾心於撒旦,顯然是某種現代價值的選擇,寧可為無盡的欲望至死方休,也不願像末世前的末人亞當一般「懷詠天堂的聖樂與人間的安適」。
失落的王治
然而,撒旦確實挑戰了王治的秩序,但他心中沒有任何「民主共和」的規劃,他的主張是「寧在地獄掌權,也不願在天國當侍應」。「撒旦派」的讀者傾心於撒旦不屈的壯志,然而亞當對寧錄的評論,可能是密爾頓對撒旦的宣判:
(寧錄)妄圖登上凌駕於同胞的地位,
強奪上帝所沒有給他的權利!
祂只給予治理鳥、獸、魚的
絕對主權;我們可以護持它;
祂卻沒有制定凌駕於人的主權。
這樣的尊榮,只為祂自己保留,
人與人之間,只授與平等。
撒旦並不是民主共和派,其實他像是當代世界中的民粹論政客,口口聲聲捍衛與挽救民主,訴求把政府還給人民,不過心中想的是成為人上人的王。密爾頓極盡描述追隨者對撒旦的尊崇,「他們向他卑躬敬畏的彎腰歌頌他,像是歌頌天界至高的神那樣」,而撒旦本人像是「帶著王者赫赫氣勢,高坐於寶座」,他是「憑著力量登上高位,意氣風發」。密爾頓的顯白教誨並不隱晦:如果撒旦意欲顛覆天主的階層秩序而重造之,那也是一個降格的王治,撒旦的王治需要卑躬屈膝,以及浮誇的儀式:
撒旦被抬舉,高高坐在屬王的寶座上,
那座之輝煌,使波斯奧馬士以及印度的
財寶失色,也教華麗東方最有錢者,渠等
撒落在其君王身上的寶石黃金黯淡無光、
粗野庸俗。因功勛而被擢升到那惡名昭彰
的顯耀處,因絕望而將自己高舉到超乎可
企及之處,撒旦渴盼之殷,以致非與天界
做無謂之爭,無以自滿。
這與亞當形成對比,密爾頓描述尚未墮落的亞當在迎接拉斐爾時的場景:
他前去,只憑自身圓滿俱足的儀態,
沒有任何儀式;其自身的威嚴,
即比王侯的馬隊,成行的侍從,
金光燦爛,徒使觀眾目瞪口呆的
那種盛儀,更加莊嚴、隆重。
榮耀並不假外求,人與生俱來的生命即是至高、無以摧毀的至高「主權」,撒旦在初見亞當時,也為了他那「額寬臉正、眉岸高聳」中所顯示的「絕對性支配」暗暗折服。對比之下,撒旦的墮落在於他需要外在的儀式,同伴的屈從才能滿足他心中的欲求。密爾頓在《失樂園》中隱然發起的「古今之爭」論題,也見於亞當的評詞:階層秩序與生命之間的某種平等狀態(「人與人之間,只授與平等」)並不互斥,天主的至高與生命的至善是一體兩面:
在祂周圍,侍立著天上的聖者,
密如群星,得親見祂的容姿,
都有無以言說的至高幸福。
而墮落後的人間王治秩序,都難免是訴諸力量的暴政,階層秩序的真正對立反面是撒旦,是僭越的暴政,一旦失落階層秩序的權威,人類就會發現自己無可避免屈服於暴力。密爾頓本人在《為英國人民申辯》中,已經表達過這樣的思想:
只要統治者是人中之極且能榮膺冠冕而無愧,則歷來許多賢明之士都曾稱讚王治;但如所得非人,王治很容易流於暴政。但如有人說王治本是「摹效上帝之治」,則試問世間有幾許人其才德能遠超同儕之上、直比上帝而堪任如此掌管世人之大權柄?
亞當的真情與撒旦的卑劣
某種意義上,「撒旦派」的說法確實有理,質疑王治的正當性可以說是《失樂園》的隱微命題,然而它所質疑者卻非天主的階層秩序,而是撒旦的暴政,它的暗示是,意欲在人間重建王治的理念,恐怕終歸幻見。
人們之所以有時候看起來更認同撒旦,是因為要成為撒旦非常容易,只要放下無謂的堅持,放膽追求無限的欲望即可,放下底線,即成撒旦,這正是撒旦「可愛迷人」之處。反之,要成為亞當,無論是墮落前還是墮落後,都並不容易,在發現夏娃之「罪」時,亞當想的不是切割,而是即便「我也跟著妳一起墮落了」,但「我決心與妳同死!確然無疑」,因為:
沒有妳,我怎能獨活?沒有妳
跟我甜美對話,沒有人心心相愛,我怎麼
孤獨寂寞的再活在這些荒涼的林子中呢?
….不管福禍、不論處境如何,我心心念念,絕不與妳分離。
讀者很少在撒旦身上看到他對於人際關係的真情,現代人可能更想成為無拘無束的撒旦,但肯定沒有人想跟這樣的撒旦為友。《失樂園》中亞當與夏娃之間真摯的情感,經常被掩蓋在撒旦的狂放之下,密爾頓被指責「異端」的其中一個緣由不在於撒旦,而是他對亞當與夏娃的描述過於「人性化」。密爾頓對撒旦的描述基本延續奧古斯丁的評價,撒旦的「曾經這種傲慢誘使他離開上帝而追隨自己。抱著僭主般的野心希望能對下屬發號施令」,撒旦式的驕傲是一種意欲取代天主,取得如上帝般的地位。
而細究之下,作為反派,撒旦也許也並不是那麼可愛迷人。像是特攝劇中的反派組織,撒旦的為惡毫無理由,彷彿僅僅只因反叛的念頭「在劇痛中從他頭顱衝撞而出,成為一個可與他分離的形體」。在天界的戰爭無果後,撒旦將腦筋動到伊甸園,打算去腐化那兩個從未傷害過他的上帝造物,此時的撒旦,已經再沒有正面決勝的高貴信念。他的作為,充其量不過給上帝找麻煩,想盡辦法惹惱一個他無法正面打敗的對手。
撒旦在《失樂園》中的反派形象,是一再降格的,從一個墮落的大天使,到地獄可怕的暴君,最後變成一個偷窺的「魔鬼」。如果撒旦真的是造反有理的「革命英雄」,他也同時注定是個卑劣的反派角色,除了在人類的墮落史中扮演一個角色外,以及影射現實中的可悲的君王以外,撒旦顯然全無正面意義。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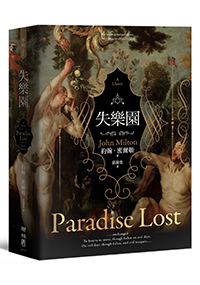
書名:《失樂園》
作者:約翰.密爾頓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3年9月
- 外星球與墓地:康德誕生三百年後的永久和平 - 2024 年 4 月 23 日
- 怎麼看《三體》才不會像小粉紅? - 2024 年 4 月 5 日
- 2014何以成為全球反中帝零年 - 2024 年 3 月 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