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鎖與日後的執行
封鎖大臣塞西爾形容他的工作是管理「世界上從來沒有人施行過的、全新形態的封鎖」。他為英國極力辯解,認為英國有權以攻擊性手段管理全球商品、金錢與資訊流通,塞西爾對美國報紙的讀者解釋說,英國必須能夠攔截跨大西洋的郵件與電報訊息。在一九一六年下半,他開始以更具體的方式考慮封鎖對國際合作前途可能造成的影響。該年九月,他就維護戰後和平的挑戰寫了一份備忘錄給勞合喬治的內閣。塞西爾在備忘錄中提出一個與事實相反的問題: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的升高,原本可以避免嗎?當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時,並非所有和平解決問題的選項都已用盡。塞西爾認為,當年如果透過大國會議或仲裁程序,便能夠協商出一套解決方案,平息這場危機。但要涉及爭議的國家們尊重這樣一項程序的結果,仍是難題。塞西爾寫道:
然而,如果能找到一種手段,既能對不守規則的一方施加巨大的壓力,又不會為使用這種手段的一方帶來過大的風險,或許就能找出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我相信,這樣的手段就存在於我們在這場戰爭所採用的封鎖之中。毫無疑問,要全面發揮封鎖效力,壓倒性的海軍力量是必要條件,但壓倒性金融力量的功效同樣不容小覷,而且一旦結合這兩股力量,沒有一個現代國家能抵擋它的壓力。假設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協約國能對德國與奧地利說,除非修改對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或召開國際會議,否則我們會切斷你們的一切商業與金融交流,同盟國是否還會堅持開戰,便令人非常懷疑。如果當年還能邀到美國一起做這樣的宣示,效果會巨幅提升。
這份備忘錄是首度由英國內閣官員提出、將封鎖轉化為和平時期防止戰爭爆發之機制的建議。塞西爾的構想日後將會影響一個國際組織的長程計畫,但他的機構只是一戰期間成形的經濟治理體制的其中一個分支而已,協約國還有其他動員全球資源以支持作戰的行動。自一九一五年初起,包括年輕的凱因斯在內的一小群財政部官員就設法讓協約國的經濟彼此連結在一起。到了一九一六年,在華爾街信貸的支持之下,英法在美國展開大規模的武器採購。英國文官沙爾特(Arthur Salter)與法國商人莫內(Jean Monnet)則成立了一個叫做協約國海上運輸理事會的新型跨政府機構管理運輸噸位,到了一九一八年,協約國海上運輸理事會已經取得許多全球商船的協助,為協約國的戰時經濟運送補給。
國際經濟合作也紛紛展開,在削弱敵國經濟的同時為協約國的盟友提供資源。這種雙重戰略有點類似拿破崙在一八○六到一八一三年的大陸封鎖政策,法國歷史學家索雷爾(Albert Sorel)曾經形容,這是一種搗毀英國外貿並打造大陸導向之新經濟體系的「兩大扳機」。一次大戰期間協約國的經濟國際主義以一種類似的方式運作:塞西爾、福斯特與瑟杜全力攔截運往敵國的資源,沙爾特、凱因斯和莫內則負責為協約國動員物資。
這種「兩面神」(Janus,古羅馬神話中兩張臉的神)似的全球策略相輔相成,但並不表示人們對它的發展方向或目的意見一致。許多人認為,對付中立國的違禁品管制制度如果過於嚴厲,以後就無法取用這些國家的資源。像瑟杜這類溫和派人士認為,應該拿捏好分寸,不僅要斷絕同盟國取得全球資源的可能性,同時還要運用這些資源供協約國使用。但克里蒙德勒與他身邊的法國干預主義分子等強硬派,主張協約國之間的進一步整合,並加強對同盟國的施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武器」的概念於一九一七年首次出現。克里蒙德勒的首席顧問、經濟史學者豪澤(Henri Hauser)在一份為法國內閣準備、供他們與威爾遜政府溝通之用的備忘錄中,解釋了何謂經濟武器。根據豪澤的觀點,協約國的經濟聯盟扮演著五大角色:第一,破壞同盟國士氣的「戰鬥武器」;第二,「和平談判的最佳保證」;第三,「對中立國來說具有說服力與吸引力的措施」;第四,「就協約國經濟復甦與發展而言,是一種相互援助的手段」;以及第五,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它是「戰後必須建立的新國際秩序的基礎,也是其最有效的保證」。
這樣的願景隱含著內在的張力。經濟武器可以成為一種謀求和平的公正手段,但也可能保有它的攻擊特性,破壞特定威脅(尤其是德國)的工業發展。難就難在如何將這兩個目標結合成一個機制,特別是在大戰結束後,要在多個戰敗國之間取得合法性相當不容易。法國國內的爭論不同於英國政府內部的分歧,他們有疑慮的不是經濟武器的可行性,而是它最終的目的究竟何在。應該用它繼續推動權力政治,還是用它超越權力政治?這個問題始終籠罩著施行制裁的戰間期,也是英法之間主要的爭論之一。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與英國官員的一次會議中,克里蒙德勒建議協約國實施一項全球原物料控制計畫,以迫使德國接受和平。他認為以戰後國際組織或仲裁之名實施的商品管制,是維護和平強而有力的手段。克里蒙德勒說:「在未來,歐洲、美洲和亞洲各國若能聯合起來運用這種原物料控制,就能達成過去用武力無法達成的目標,讓難以控制或侵略成性的國家聽話,維繫和平,這樣的約束難道不是邁向仲裁的最佳良方?」這番階級統治意味濃厚的言語,充分說明了他所致力維護的世界秩序。
希臘在一戰時的經驗顯示封鎖作為一種手段,還是離不開傳統權力政治的糾葛,仍有許多可改進之處。當時表面中立的希臘分裂成兩派,親協約國的一派以共和派總理韋尼澤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為首,另一派是以國王康斯坦丁(Constantine,德皇妹婿)為核心的親德派軍官。在一九一六年底,分裂的政局升高成一場實質的內戰。為迫使康斯坦丁加入協約國陣營,法國政府將
一般性的歐陸封鎖制度擴大,延伸到希臘皇家派控制地區,特別是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e),但沒有宣戰;英國也立即跟進,在協約國港口扣押希臘船隻。由於希臘居民仰賴食物進口,這場和平封鎖造成嚴重的饑荒,雅典民眾死亡率在一九一七年初暴增了一倍。六月,康斯坦丁退位,協約國於是結束封鎖,韋尼澤洛斯迅速成立新政府,加入協約國陣營參戰。對處於一戰邊緣的希臘來說,經濟壓力在政治上一直都能奏效,但這也突顯出希臘在國際秩序中的從屬地位。歐洲列強曾於一八二七年、一八五○年和一八八六年對希臘實施平時封鎖,因此當塞西爾與克里蒙德勒在一九一七年大談封鎖技術未來用途的崇高理念時,對同年遭到經濟封鎖的希臘百姓來說,這一切只是讓他們憶起十九世紀祖先們的悲慘命運而已。
金融封鎖
早期的協約國封鎖政策聚焦於實體商品的攔截與外國資產的扣押,隨著時間過去,對儲煤庫的管控將能源也納入封鎖當局控制的範圍,但這些都未觸及世界經濟最具動能的要素:全球金融體系。雖然德國與奧匈帝國跟中歐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貿易明顯趨緩,兩國仍能從海外找到資金來源,巨額資金依然透過中立國的金融中心,源源不絕地流入。以一九一六年二月到三月為例,根據英國財政部紀錄,從華爾街匯往中立歐洲銀行的匯款就超過一千一百萬美元。一份通報指出,「荷蘭與斯堪地那維亞半島銀行的生意無比興隆。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哥本哈根、克里斯蒂安尼亞(Christiania,挪威首都奧斯陸舊名)、卑爾根(Bergen)、馬爾默(Malmö)、特隆赫姆(Trondjhem)與斯德哥爾摩這類地方的小銀行,一天就能經手正常期間一個月才能做到的生意。造成如此龐大金流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與德國的貿易。」塞西爾的封鎖部想要切斷這些金流,但欠缺從倫敦取得系統性金融情報所需的人員和方法。
倫敦市銀行家戴維斯(E. F. Davies)懷疑,許多中立國銀行透過倫敦進行的交易實際上都是在替德國海外公司匯款回國內,隱藏德國的獲利。戴維斯建議封鎖部訂定一項針對德國的金融封鎖政策,在倫敦市招募有經驗的交易商,揪出這類可疑的交易。引入更多官僚體制與切斷一定數量的交易,會讓倫敦損失一些外匯生意,但戴維斯覺得因封鎖效率提升帶來的好處遠比這些損失大得多。他認為「有些人只重視眼前近利,沒有想到虧損六個月但打贏這場戰爭,要好過賺錢卻危及大英帝國」。
塞西爾任命戴維斯出掌新成立的金融處,他便從巴克萊銀行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找來一小群志同道合的銀行家與他共事。金融處針對中立國對中立國通過倫敦的金融交易,發展出一個以郵戳為憑的計謀。因為金錢與證券交易的指令得透過郵件或電報傳遞,金融封鎖實際上是通訊封鎖:能控制郵遞路線與海底電報纜線,就能控制支付金流,郵件檢查與訊號攔截於是成為切斷敵國銀行與全球金融體系之連繫的重要手段。為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金融處將執行封鎖的重擔轉交到金融機構身上。從一九一六年五月起,協約國各國境內銀行都得簽下保證書,保證他們的帳戶「無論直接或間接」,都不會被用來「做任何生意以協助與大英帝國或其盟國敵對的國家,或者為這些國家牟利」。就這樣,封鎖官員可以繞過民營銀行家,將銀行列入黑名單、起訴與強制關閉銀行。金融處還透過一個簡單的強制會報制度,建立本身的情報蒐集網路:根據英國法律成立的卓越銀行,必須報告它們與中立國每週的資金往來。銀行在貿易過程中扮演的中介角色,意味著金融處能獲知許多商業的動態。戴維斯在一份給塞西爾的備忘錄裡寫道,「每一批跨海托運的貨物,只要背後的資金是來自英國銀行於國內撥出的信用貸款,金融處就追蹤得到……包括發貨人與收貨人姓名、裝運港與目的港、輪船名和運輸日期等等。」
一九一六年夏末,布洛克(Adam Block)爵士繼戴維斯之後出任金融處處長。
布洛克是一名經驗老到的銀行家,在鄂圖曼帝國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曾擔任英國大使館的首席口譯與鄂圖曼公債局的行政人員。他上任後立刻建議制裁瑞士的銀行,認為這些銀行都是暗通德皇的雙面金融機構。在與法國封鎖官員的對話中,他還主張切斷所有經由倫敦匯往中立國的美國匯票,做法之躁進程度讓法國政府吃驚不已。法國的部際金融委員會主要由法國中央銀行官員負責,但其中也有像洪保(Octave Homberg)這樣的民營銀行家。洪保是一位殖民地金融專家,曾擔任印度支那銀行與巴黎聯合銀行主席,並參與一九一五年華爾街首次貸款給參戰各協約國的協商。在坦納利的法國經濟情報處分析師提供的情報協助下,部際金融委員會與瑟杜的封鎖部密切合作,共同推動一九一七年對中立國的局部金融封鎖。
拉丁美洲是歐洲工業原物料很重要的供應來源,但對英國與德國而言,它作為外資投資地的地位也同樣重要。對參與其中的銀行來說,在這個高成長市場為新公司提供資金的獲利甚豐。一九一三年,德意志銀行在拉丁美洲的分支德意志跨大西洋銀行,為它的母公司賺進了六分之一的營收與淨利;而在一八八六到一九一二年間,有五個德國銀行財團於拉美地區設立自己的子公司。只要德國在拉丁美洲蓬勃的銀行業務與生意持續下去,僅僅針對實體商品貿易進行封鎖便無法對德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形成重大的打擊,金融封鎖當局於是開始想辦法阻止德國將海外獲利匯回國內。然而巴黎與倫敦的官員在執行這類政策時碰到一個難題:他們在干預二十世紀初期金融體系的同時,也會傷及自身的經濟。一九一七年底,英法為阻止德國從阿根廷匯款而懲罰促成這筆交易的法國與荷蘭銀行,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這個例子的主角是十九世紀末法國金融業的成功代表—里昂信貸銀行。一八六三年以兩千萬法郎資本額創立的里昂信貸,五十年後成長為全世界最大的銀行,總資產高達二十八億五千萬法郎(一億一千三百萬英鎊)。作為一家版圖橫跨各大洲的銀行企業集團,里昂信貸為東歐與南歐、俄羅斯、中東、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公司提供短期貿易信貸與長期資金。它在拉丁美洲的業務是透過馬德里的分行進行,於拉美地區十分活躍的德國、荷蘭與瑞士銀行都是該分行做生意的對象。在這裡,對國家的忠誠無足輕重,德意志跨大西洋銀行的證券,就有部分以信託的方式存放在里昂信貸銀行中。
拉丁美洲大部分的金融業務都由歐洲大銀行的子公司負責處理。與里昂信貸有生意往來的其中一家銀行是鹿特丹銀行的子公司,創立於一九一四年三月,同年十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成立第一間分行荷蘭銀行南美分行,一九一六年於里約成立巴西分行。荷蘭銀行於一九一六年二月首次引起法國封鎖當局情報網的注意,當時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分行代表德國第二大銀行德國信用合作銀
行買進價值四百三十萬馬克的黃金。德國信用合作銀行為了替德國籌措戰費,這段時間以來一直在向阿根廷政府兜售黃金。由於那時候協約國還沒有建立統一的金融封鎖政策,荷蘭銀行與阿根廷都能隨意進行交易,但歐洲銀行的拉美分行顯然即將成為封鎖當局對付的目標。
一九一七年夏末,美國加入戰爭,也改變了局勢。協約國現在掌控了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紐約、倫敦跟巴黎—於是可以運用更強大的金融壓力發動攻勢。該年九月初,在法國部際金融委員會於巴黎召開的會議上,英國封鎖部金融處處長布洛克呼籲對中立國銀行採取更嚴格的管控。他說:「經驗告訴我們,被列入黑名單與遭協約國斷絕一切關係的威脅,足以形成威力強大的武器;面對這樣的要脅,大多數的中立國銀行都會接受我們的條件。」布洛克主張,只要是與同盟國有任何關係的中立國人民,協約國人民就不得與他們進行交易。他的法國同僚洪保的態度則比較謹慎。洪保認為,對大型中立國銀行實施全面性的貿易禁令,可能會適得其反。一旦被迫在兩大敵對陣營之間選邊站,與同盟國商貿關係已經很深的銀行,可能寧可切斷與協約國的生意,也不願停止借貸給德國。他警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造出來的武器會反過來對付我們」。洪保認為協約國需要採取一種更加精細的做法:建立一個酌情裁量的類黑名單制度,只以特定可疑交易而非銀行整體為對象,打擊對協約國貨幣的套匯行為。
協約國很快就用這種比較精細的制裁方法對付拉丁美洲與歐洲中立國之間的交易。隨著協約國對巴西的金融壓力不斷增強,荷蘭銀行里約分行成為獲利匯往西班牙的管道,德國商人或許希望這間銀行的荷蘭關係能讓他們不被封鎖當局盯上。根據在地領事人員蒐集的情報,法國封鎖當局知道荷蘭銀行與德國貿易公司布隆堡公司有商業往來,要求將它列入黑名單。八月十四日,荷蘭銀行里約分行從德意志南美銀行持有的一個戶頭,匯了十八萬西班牙比塞塔(八千五百英鎊)到里昂信貸馬德里分行。九天以後,荷蘭銀行又付了一筆類似金額的款項,接著在九月電匯了五十萬比塞塔(兩萬三千九百英鎊)到馬德里分行。法國駐馬德里大使館在獲悉這幾筆付款紀錄後,認定荷蘭銀行將敵國資金匯往歐洲證據確鑿,於是要求將荷蘭銀行列入黑名單。
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關於荷蘭銀行的資料已經獨立建檔。荷蘭銀行使用五個不同的名字與德意志銀行、德勒斯登銀行、沙夫豪森銀行協會與達姆施塔特和國家銀行等大型德國銀行的拉丁美洲子公司進行交易,而它在阿姆斯特丹、里約與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三間分行也很快就被法國列入黑名單。不久,荷蘭銀行董事會裡有兩名法國人的內情曝光,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但對法國金融封鎖委員會的成員來說,最令人擔憂的並不是法國同胞在一家違反封鎖令的銀行擔任董事,而是他們視為國家之光的里昂信貸,竟然讓德國人使用它的海外帳戶作為掩護。
管制里昂信貸的馬德里分行則是另一個挑戰。在法國封鎖當局凍結馬德里分行與中立國往來的帳戶之後,西班牙法庭也被牽扯進來。由於里昂信貸的西班牙客戶指控它不付款,西班牙法庭於是下令里昂信貸履行合約義務。里昂信貸馬德里分行的董事們向法國金融封鎖委員會求情,請求委員會准許他們付清這筆欠款,但委員會不為所動地表示:「里昂信貸銀行作為一家法國公司,必須遵守法國法律。面對西班牙法庭,這項法律義務就是不付款最好的抗辯理由。」里昂信貸與荷蘭銀行的事件突顯出國家政府對全球化的民間金融領域究竟擁有多大管控權的問題,法國政府能為了國家利益,迫使世界上最大的銀行重新配置它的國際業務嗎?一九一四年以前,由於金融機構在歐洲、亞洲、非洲與美洲具有重大的政治影響力,西方政府經常在國際事務上協助銀行家,協約國之間的戰時金融就高度仰賴紐約、倫敦和巴黎的一小群銀行家。將封鎖的範圍延伸到金融領域導致這種關係的部分逆轉,任何與經濟戰的強度有關的政治決策都會影響銀行的營運。就法律層面而言,法國政府禁止法國銀行與敵國人民進行直接交易沒什麼問題;但當涉及「中立國銀行之間」的收付,由於協約國戰時金融的運作也得仰仗這類銀行,情況就會比較複雜。
儘管如此,金融封鎖當局這種對特定個案進行強力干預,但不建立永久性管控機制的做法,仍然樹立了銀行業者必須據以自律的行為守則。金融封鎖基本上是一種監督機制,不過根據法國金融封鎖委員會的觀點,這並不「以任何方式削弱金融機構應該謹慎自律的事實,最有能力監督他們的交易對象與機構的人,就是他們自己,政府沒有責任代他們完成這些工作」。配合封鎖政策是銀行自身的職責。即便全球經濟戰已經決定性地為十九世紀自由放任的世界經濟劃下句點,民間企業對於自身利益仍有很大程度的掌控權。然而,在之後數十年的制裁政策規劃過程中,政府可以干預到什麼地步的問題還會一再出現。
作者生於荷蘭,成長於比利時,先後畢業於荷蘭烏特列支大學、英國劍橋大學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年僅三十歲便成為康乃爾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是歐洲現代史、政治經濟史與思想史。
穆德長年對於國際組織中的主權問題感興趣,特別是較為中小型的國際行為者。這使得他得以跳脫大英帝國或美國的視角,看到瑞士、希臘、阿爾巴尼亞、香港、南斯拉夫或芬蘭等地的歷史經驗。以《經濟武器》榮獲美國對外關係史學會(SHAFR)伯納斯獎年度最佳圖書,目前正在撰寫他的下一本書,《大徵收時代》(Age of Confis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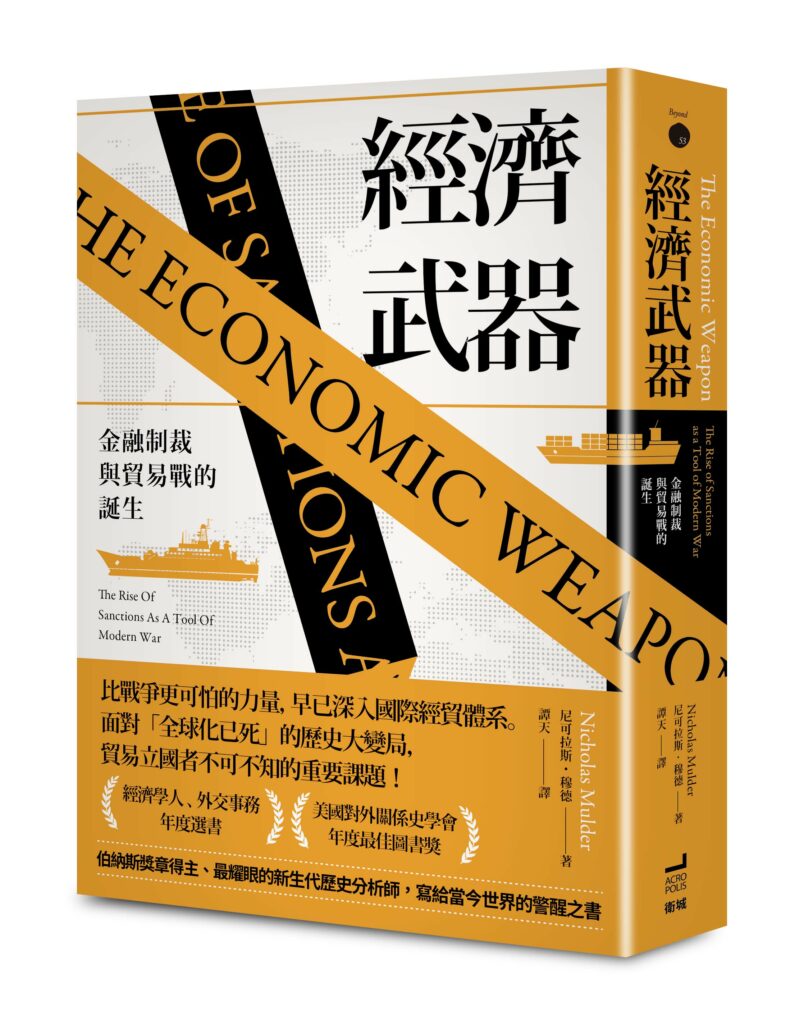
書名:《經濟武器:金融制裁與貿易戰的誕生》
作者:尼可拉斯.穆德(Nicholas Mulder)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3年10月
- 【書摘】《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 - 2023 年 12 月 1 日
- 【書摘】《經濟武器:金融制裁與貿易戰的誕生》 - 2023 年 10 月 20 日
- 【書摘】《送禮的藝術:從特洛伊木馬到動物園熊貓,50件外交禮物背後的世界史》 - 2023 年 8 月 1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