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絮絮叨叨愛情的作品都有一個類黑格爾的正反合辯證結構,先是承認愛情那體面的美好,就像世間一切善好的物事,誰不喜歡愛情?這個環節難免說教,在柏拉圖的〈會飲〉中,第一個發言的斐德羅(Phaedrus)一上場就主張沒有什麼比年少時就體驗愛情更美好的事,而一個人的幸福人生,不是靠家世、名望與財富等等,而是擁有愛情,因為感受愛情的美好,自然就能養育厭醜好美的高貴品格,沒有機會感受愛情的美好,「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都做不成什麼偉大美好的事」。多麼人生勝利組的發言。
愛情的反題則始於承認挫敗,不管是沒有節制的愛欲,還是人在愛情中的困頓。在斐德羅之後發言的保薩尼(Pausanias)嘗試剖析不同層次的愛欲經驗,因為認識到愛欲可能帶來的瘋狂與失控,他帶著一點理性審議的味道暗示,對於愛欲應當要有所規範,特別是男人與男孩之間的愛欲。保薩尼的發言可以跨時空接軌到當前各種提醒姊妹小心渣男與危險情人,避免暈船的愛情教戰。直到最後,似乎只有經過正與反的鋪墊,總是在愛情感到困惑的讀者們才能切入愛情的真理。
「我願,故汝在」
韓炳哲的小書《愛欲之死》(Agonie des Eros)也有類似的正反合結構。表面上,這是一個熱衷於談論愛情,自由實踐愛欲的社會,無論是還抱持浪漫想像的人們,還是殘破不堪的心靈,都可以在這個有著社群媒體與交友軟體加乘的世界找到一個人的胸膛,親身踐行「愛欲」(Eros)的本義,獲得、消費與滿足最強烈的快感。
然而,就像社會學家易洛斯在《為什麼不愛了》(The End of Love)中所說,在這個「超互聯」的社會中,販賣愛情無限美好的商業機制與無盡延伸的社交媒介,並沒有帶來上個世紀所鼓吹的,因為性的解禁所帶來的解放,反倒是加劇了親密關係在存在意義上的不安。若是所有的關係都是可能的,甚至連「開放性關係」也是一種束縛,我們將無法確認眼前的這個親密關係到底是什麼「關係」。
易洛斯用沙特對於「虛無」的比喻來描述這種感覺。人們在遲到的時候會四處張望,看看對方是不是在等待,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看到很多東西,會注意現場的誰是不是正在等待的人,如果一直沒發現對方,會開始猶豫是不是要繼續在這裡待下去。在周遭許多人事物的喧囂中,既感覺不到對方,也無法確定自己的意圖是不是要繼續等下去,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被拋下,也不能肯定自己還要不要繼續等下去。
虛無不是指對方的不在場,而是不確定對方是否已經不在場,知道某種程度上責任在於自己的自由選擇(即便是並非刻意的遲到),但心裡不免埋怨對方冷漠的矛盾情緒。易洛斯稱之為「消極關係」,關係中的各方都是自由的,但不若市場機制中的自由有甲方、乙方以及締結契約的我們,消極關係中只有張望著,不知是否繼續下去的我,我的比重無限大,卻同時是連自己的意圖都無法確定的無盡虛無。
如果說消極關係中的虛無是一種倒錯的愛欲經驗,那是因為愛欲經驗,如同羅蘭巴特在《戀人絮語》中所說,本質上是「異位的」(atopic),我們所愛欲的對象如此獨一無二,以至於我們無法用任何的具體特質來描述它,我所愛的不是你的眼、你的身甚至你的心,愛人是「無類」(atopos),是擁有這雙眼睛,這副肉身以及這般靈魂的你,那世上獨一無二的你。
「我願故汝在」(volo, ut sis),典出奧古斯丁。海德格在寫給(包含鄂蘭在內的)每個情人的情書中,都會提上這句話。說的是那無類的愛欲經驗,與世界獨一無二的你相遭遇,同時也造就了我,完善了我的生命。在消極關係中,有無限大卻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卻沒有在世界上找到獨一無二的你的我;虛無的體驗是只有不知道還在不在的他,卻沒有獨一無二的「他者」。
他者這個法式風格哲學迷因
不僅僅是親密關係自由化的產物,韓炳哲在現代社會一系列的精神苦楚中都發現了「消失了的他者」的病灶。新的市場理念不再是各得所需的交換,而是變形成無限內捲的競爭,也就創造了自我剝削的績效主體。韓炳哲用「抑鬱」(depression)來描述當前你我被迫無限自我內捲,因而過度緊張與焦慮的精神苦楚,因為時刻的病態性自我檢討,它也將同時必然是被迫自戀的。
現代社會的精神佈署是一種「我能」與「無力」之間的特殊辯證。無限的內捲導致人們必須被迫努力「加值」與「充實」,但這條自我優化之路卻看不到盡頭,韓炳哲借用班雅明的說法,把資本主義比喻成一種特殊的宗教,跟所有的宗教一樣,它都有一個「負債者」的主體結構,負債於更高的超驗存在等等,因而必須在此世刻苦修行還債,但資本主義沒有救贖,沒有所有宗教都有的債務終點,負債者沒有「還清債務」的一天,至死方休,即使死去也是虛無的消逝,不是邁向另一個輪迴的過渡,因為「精神上的無力償還」,所以「抑鬱與倦怠共同造成了我能(ability)無以救贖的挫敗」。如韓炳哲所說,倦怠社會特有的精神困境是「務成功引發的抑鬱」(success-induced depression; Erfolgsdeprssion)。
社畜、躺平、繭居,乃至於孤狼恐攻,都只是抵抗倦怠社會,無力的孤注一擲。我必須能,卻虛無地不知為何,於是最終只能以社會性死亡告終。
但在愛欲經驗中,有著全然不同的「無能」與「力量」辯證。在某種意義上,在愛情的世界裡,人人都是受害者,因為愛情不會因為我們的努力與積極而存在,愛情會沒來由地打擊我們。用韓炳哲引以為援的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話來說,「愛不是一種可能,並不出於我們積極,愛全無道理;我們抓不到它,而它卻能傷害我們」。
「他者」這個法式風格的哲學迷因,對勒維納斯來說其實就在人人都經歷的單戀、曖昧與戀愛經驗。愛情無法佔有與操控,不能去奮鬥,更無法傳授,人們會在愛欲經驗中親身感覺到一種與他者之間,近乎神秘的關係。韓炳哲這麼說:
愛欲是與他者的一種關係,座落在功績、表現與能力之外,無能為力代表了其否定性對應。他者(otherness)的否定性,我盡其一切所能卻不能及,他者的非域(atopia),構成了愛欲的體驗。
在人們穿透愛情表面的美好,越過承認挫敗的環節後,人們會抵達愛情的真理。它不一定是什麼高深的奧義,無論是柏拉圖筆下古典的蘇格拉底,還是韓炳哲時髦的法式做派文風,它可能就是一種把現代這個倦怠社會的「我能─無力」結構倒轉過來的想像:人們在戀愛中始終感受到無能為力,但這種無能為力,卻同時激發了人的力量,「愛欲會激發一種自願的忘我與自體犧牲,一種虛弱的感覺向墜入愛河的人的心頭襲來,但同時一種力量的感覺接踵而來」。
戀愛、愛情與愛欲的力量。
應該像極了愛情的政治
如果愛欲經驗(即便是倒錯的)始終涉及某種力量與無力之間的特殊關係,那麼愛欲與政治難免存在某種可類比性。福山筆下那在自由民主體制中因為空虛而只為爭一時血氣的「末人」,很難說不是處於某種消極的虛無關係中。不若兩戰期間法西斯猖獗,想捍衛民主不怕沒有對手的時代,當前的民主政治中,更多是心懷各種苛求,希望體制可以如保母般面面俱到,卻又每每失望因而心懷憤恨的人們。
如果韓炳哲說盡了倦怠社會的真相,那麼它的政治面向應該就是這種總是努力希望「我能」卻又不得不敗興「無力」的滿腹牢騷之人,而這幾乎必然是民主庸常運作下的抑鬱常態。
韓炳哲筆下的愛欲經驗,看起來像是一個美好的救贖,特別搭配了「他者」這樣的哲學奇異迷因。
我們不由得相信,如此難能可貴的愛情,會從某個瞬間的偶然開始,從此宣告了某種永恆,「永遠如此」的永遠愛你宣告了一種超乎世俗的政治忠誠,即便人們並不知道「永遠如此」意味著什麼,甚至也不知道它會持續多久。愛欲經驗是把自身當作賭注,押在時間洪流之上,甚至必須相信,愛會在時空之外也依然延續,甚至,延續到那可能的多元宇宙。
愛是一種近乎幻想的真理。
如果倦怠的社會確實需要某種延伸愛欲經驗的翻轉,那麼,擺脫民主政治庸常處境的構想可能也需要。政治是把自身當作賭注,押在那無以逆料的形勢變遷甚至終究徒勞中,即便如此,也依然相信理念的力量會在未來、下一個世代身上開花結果。
應該像極了愛情的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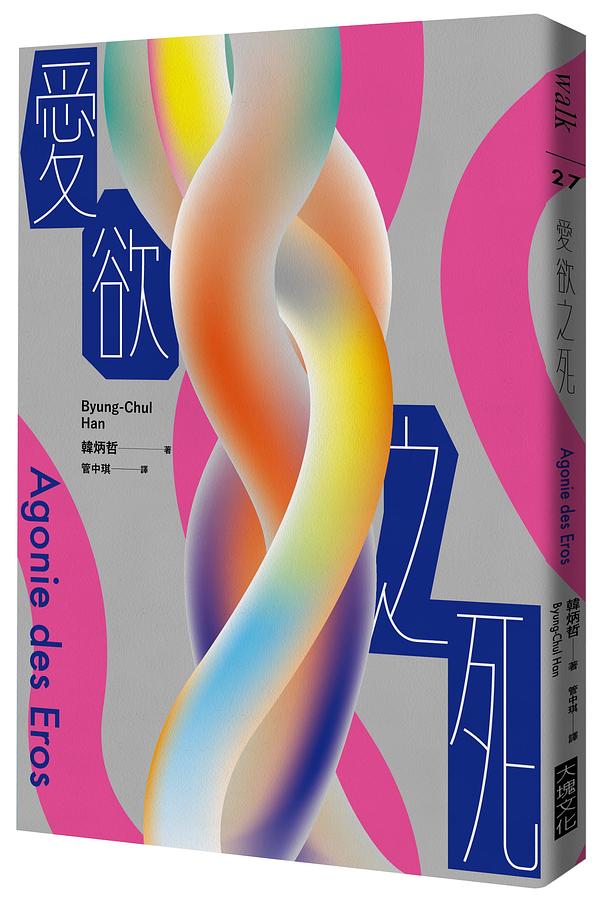
書名:《愛欲之死》
作者:韓炳哲
出版社:大塊
出版時間:2022/5/28
- 外星球與墓地:康德誕生三百年後的永久和平 - 2024 年 4 月 23 日
- 怎麼看《三體》才不會像小粉紅? - 2024 年 4 月 5 日
- 2014何以成為全球反中帝零年 - 2024 年 3 月 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