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於耶魯大學的挪威籍冷戰史名宿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2017年出版的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2023年由台灣聯經出版了繁體中文譯本《冷戰:從兩強爭霸到全球衝突,當代地緣政治的新世界史》。對一個早就以冷戰研究蜚聲國際的權威學者而言,這本著作的意義究竟為何?相較於自己過去那些獲獎無數的冷戰史等身著作《冷戰與革命》、《緩和的衰弱》、《決定性交會》、《全球冷戰》與《劍橋冷戰史》,這本文安立最新的冷戰史。究竟有甚麼特別或突破呢?
事實上,看中文書名的副標題「從兩強爭霸到全球衝突,當代地緣政治的新世界史」,正好可以凸顯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有時候,重點真的「不在」括弧裡。地緣政治的外在世界客觀地理條件,以及大國物質權力的競爭,或許是當代國際關係衝突的核心要素。但對文安立而言,冷戰確實是以物質權力的對峙、軍備競賽與核戰邊緣的形式表現;但究其源頭,冷戰實際上起源於兩種意識形態的衝突,是一種觀念上的對立造成了軍事上的對立;是價值的衝突而不是物質的結構衝突造就了冷戰。所以對他而言,這部冷戰史確實是一部政治史、世界史,乃至於國際關係史。但這卻是一部從「觀念史」發軔的國際政治分析,而不是單純有關冷戰的地緣政治解讀。
意識形態差異造成兩極體系的歷史特殊性
文安立在《冷戰》一書中,開宗明義的強調了他的研究動機。也就是,綜觀全球史上的多數國際體系,其實大多是多極體系(多個強權國)、單極體系次之(單一霸權國),但兩極體系是其中最少見的。對他來說,上一個在歐洲真正出現過的兩極體系,是西班牙跟英國兩者為了不同的宗教意識形態進行對立,並且在遠離本土之外極遠的殖民地展開戰爭。(但世界史上多數的「兩極體系」如:雅典斯巴達、羅馬迦太基、宋遼澶淵之盟、19世紀英俄大博弈,都是肇因於權力衝突與民族仇恨,而不是意識形態對立,這點我們還是需要注意)
對文安立來說,世界史上殊少形成兩極國際體系;但更少的是,一個兩極體系的成立關鍵,是以特殊的意識形態對立或觀念衝突為基礎。近代冷戰的成立重點,就來自一種觀念上的差異導致意識形態的衝突。文安立認為,究其根本,美蘇意識形態的衝突,來自雙方各自對19世紀末「現代性」興起所造成的新問題,也就是「上帝已死,人要如何自處或與它人相處」,所得出的兩種不相容答案。
美國在面對「上帝已死」這個現代性開端時,舊大陸上,舊社會文化與宗教傳統已然消失。除了自力保守「上帝未死」的宗教生活,遵循友愛與正義等傳統美德,以及政治上憲政主義強調的平等與權利觀外;美國人也需要一個與舊大陸新移民溝通,眾人得以共同在新大陸安身立命的新思想。文安立的觀察,美國人得出的結論,是用「市場」與「資本」來取代舊世界的神,使其成為新世界的神。
「資本主義」這個新世界的神,除了內涵與舊世界的神(基督教)不同以外,基本還是一種強調「普世性」與「線性進步」的新宗教。這種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構成的新宗教,在一戰後開始大量影響歐洲,使得手工業者組成的行會,被其衍伸出的福特主義與泰勒化的科學管理取代。這種管理風格,甚至也被1930年大崛起的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使用。如此更確定了生產模式的變遷,以及市場經濟的蓬勃。
而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這個「新興宗教」,歐洲大陸以俄羅斯為首的新興政權蘇聯,就反對「美式資本主義的普遍性」。蘇聯的立國精神「共產主義」源自19世紀面對工業革命發展已久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支持者認為,面對舊世界的衰亡,新世界要有的新興宗教,應該是以「計畫經濟」的「理性主義」來馴化多變的市場,消滅競爭、創造平等。而美國與蘇聯應對舊世界與舊宗教毀滅,與隨之而來的地方認同與社群歸屬崩壞下原子化個人的誕生時,一方面,美國透過自由放任、反對中央集權,來維持或保護這種個人主義下、原子化的社會現狀;另一方面,蘇聯則透過中央集權,將國家機器強化到控制所有人,來避免人與人過度競爭所造成的不平等或是市場失靈。
若是兩極體系的存在,需要特定意識形態的支持;那冷戰史作為近代史上兩極體系存在的一段歷史,其基礎就是上述兩種不同觀念的誕生,促成了相反的兩種意識形態,及雙方各自發展之後的對立與衝突的歷史。所以,在文安立的筆下,近代冷戰的開端並非二戰以後,美國決定全面圍堵蘇聯,或是韓戰的爆發,亦或柏林危機。這些外交決策與國際事件的發韌,在於兩種衝突意識形態的誕生,以及雙方認知彼此必然衝突的前提下,因此而產生的結果。因此,文安立將冷戰的開端,定錨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資本主義全球化,門羅主義跨出北美進入西太平洋,以及歐洲左翼工運激進化的時刻。這個原創性的詮釋,才是文安立對冷戰這個舊題新解的可貴之處。
意識形態對立之外的其他因素
文安立認為,冷戰的發韌來自資本與共產兩種意識形態在對人類應對現代性社會時,提出了兩種相反的觀念。而這兩種觀念的衝突,鞏固了國際關係中兩極體系的持續運作。在這個兩極對立的過程中,國際政治主要產生了兩種重要的變化:
第一、美國成為獨霸世界的力量:美國的國防預算,自1900年前後開始,為了應付美西戰爭因此擴編,一直到今日一百多年間,若是折合通膨與購買力,至少也是提升了一百倍;另一方面,1870年,南北戰爭前後,美國GDP約佔全球9%。
但到了冷戰的高峰期1955,美國GDP佔全球達28%。2020年後雖然佔比下滑,但仍有22%。第二、大量新興國家誕生:1900年以前,新興獨立國家大多來自拿破崙戰爭後,趁機獨立於西班牙與葡萄牙之外的拉丁美洲國家。二十世紀後,經歷兩次大戰,歐洲老牌殖民帝國相繼瓦解後,才有來自亞洲與非洲的大量新興國家出現,並且彼此以民族國家與主權國家的形式存在。
兩極體系之下,資本共產兩種觀念的對立,確保了冷戰的持續運作。但取代舊社會、舊群體與舊普世宗教而興起的現代性方案,除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外,不能忘記的,就是各個區域對應而生的民族國家與民族認同。扣連上述第二個「大量新興國家誕生」的現象,使得身分政治的出現,再再打擊那些超民族主義試圖重返帝國的努力(hypernatiopnalistic)。而兩極體系下,兩種價值的兩大陣營,也必須將自己所支持的「普世主義」價值,放置在各地民族主義「特殊性」挑戰的脈絡之下。
這也使得美蘇兩大陣營不同於過去德日以「民族帝國」將「特殊視為普遍,以特殊推廣普遍」的模式;而是一開始就宣稱各自意識形態的普遍性,將各自的民族國家置於這種普遍意識形態之下。但最終,兩大陣營的觀念雖然對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國際體系因此成為兩極體系;但各地民族主義的地方連結、身分政治與情感認同,還是讓地方特色持續保留,最終這股民族情感與地方勢力,也是導兩極體系瓦解、冷戰終結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兩大陣營中,主權國家還是存在。因為在地認同所構建的民族主義,借用了普世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力與外部援助,但卻無法改變一般個人與國家或民族的地方連帶所創造的特殊身分與情感歸屬。
除了民族主義的持續不滅,與冷戰大框架下的兩種意識形態持續相生相剋以外,冷戰的興起與其中意識形態的對立,對文安立而言,還有以下兩個有關政治與經濟上的時代因素。第一、政治上,其實20世紀初的美俄都以英國為敵。美俄崛起的時間,正好是大英帝國全球殖民的時代。英國早期自由主義的貨物與資本自由流通政策,在英國海軍的支持下,成為某種依靠實力形成的貿易壟斷,這讓美國作為新興挑戰者備感吃力。為了讓自己能「持續崛起」,美國也是透過作為「國際上的麻煩製造者」,反對英國霸權所建立的國際制度,經歷一百年的努力,甚至一直要到冷戰結束,一個貫徹美國全球霸權意志的新國際秩序及其制度才得到確定。
另一方面,對蘇聯來說,從帝俄時代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開始,英俄就是國際政治棋盤上的主要對手。雙方在克里米亞戰爭與日俄戰爭中都有交手的紀錄,而且俄羅斯也一直把英國作為帝國擴張啄取全球利益的重大障礙。但相較於英美之間是經濟與貿易利益的衝突;俄羅斯並不認為經濟發展可以讓自己取代英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但也正是領土持續爭奪與擴張,再加上相對經濟落後的狀況,大領土、低經濟兩者的結合,正是催生出共產主義蘇聯的特殊基礎,也讓俄羅斯成為聚攏反資本主義勢力的重要堡壘。
第二、經濟上,文安立雖然強調觀念的重要性,但他也認為,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的興起,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當時世界經濟的敗壞。除了極度不公平的經濟剝削與勞動壓榨外,20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運作的失靈,1930年代股市崩盤導致全世界國內生產毛額跌了15%,這也是共產主義真正可以崛起的重要原因。這種大蕭條,也讓那些無論在一戰或二戰後獨立的亞非拉國家,不得不思考一個更好的社會理念,以維持初步建構的共同體有更穩固的根基。同理,納粹與義大利法西斯也是在這波全球性經濟危機衝擊下,因為高失業率與通膨,而吸收了大量的支持基礎。
昭昭天命與美國例外
文安立認為,支持美蘇的兩種意識形態,也就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之所以讓美蘇不同於日德這種「民族帝國的超民族主義」,是因為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有某種普世性與進步性;並且更重要的是,基於我的意識型態的優越性,而不是基於我們民族的優越性,我們的民族受到這種意識型態的啟發,因此成為這個意識形態的推行者與守護者。作者稱之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感召。而且正是這種使命感,讓兩國以兩種意識形態為基礎,各自發展成為區域霸權與世界強權。
另一方面,有鑑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是人類史上唯一一次在價值觀念進步領先全世界,並且獨霸世界的時代。因此,美蘇的現代性方案也是脫胎自歐洲的觀念。對美蘇雙方各自都擁有「昭昭天命使命感」的領導來說,為了擴張自己觀念的影響力,除了擴大國家的影響力與領導力外,更重要也是傳承某種歐洲觀念與歐洲文明的香火。把這個所謂「文明的火炬」遞向歐洲以外的其它地方。對這些自承昭昭天命的美蘇領導者而言,他們本身扮演的就是啟蒙的先鋒,更是扛起某種信仰上「普世帝國」的重擔。這種普世帝國的新十字軍或至少是傳教士,不同於新帝國主義者對外尋求資源與商機,而是為了將自己的價值理念,無論是賺錢榮耀上帝也好,或是公平避免剝削也好,藉此拯救非歐洲地區國家人民的靈魂。
有趣的是,文安立還提到美蘇雙方的十字軍與傳教士精神,雖然源自於基督教,但卻都是不同於傳統基督教「原罪觀」的成功神學。他認為,正是因為美國福音教派與俄羅斯東正教都刻意忽略某種人的「原罪觀」,強調人、人類或人類社會整體,都可以臻於至善(perfectibility);所以他們積極作為上帝的使者,要向世界傳遞福音,向尚未被啟蒙者進行啟蒙,讓他們歐洲化、讓他們也受到普世價值的沐浴與普世帝國的看顧。
綜合以上,文安立對一向以「天命昭昭」自詡的「美國例外論」,做出了精要的拆解。他認為,美國例外論主要是由以下六種要素構成,而這是這六大元素,而不只是資本主義,奠基了美國自威爾遜以降的理想主義(以下稱之為威爾遜主義),以及緊接其後的冷戰意識形態。第一、昭昭天命:由「普世主義」加「線性進步史觀」為基礎,當我們認識到自己的價值與標準堪為世界的表率時,其他國家也應該跟我們共用一樣的價值;第二、歐洲文明的護衛者、復興者:舊世界的人們只要跟著我們由歐洲改革而來的價值,歐洲就會復興、舊世界也會整個昌盛。
第三、福音教會成功神學:缺乏原罪觀念,相信人類努力不懈可以甄於至善。(普世主義昭昭天命、文明復興者與成功神學上述三者共築了所謂美式使命感);第四、美國龐大的國土與豐富的物產,構築的國家實力;第五、更好的觀念加上更強的國力,等於美國天生比別國更理性、更先進;第六、綜上所述美國的好,讓美國內部出現兩派辯論,是要繼續做好自己該做的、建立典範,其他世界自然就會跟隨;或是,美國應該在各個殖民帝國擴張的世界裡,加入競爭,用美國的觀念與實力,將世界形塑成美國人理想的樣態,這個樣態也會是世界的「正軌」。而美國外交史上,孤立主義與世界主義的辯論,正是來自這種「我們應該如何處理自己的好」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基礎上。
威爾遜主義作為美國意識形態的基礎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透過美西戰爭取得西班牙在西太平洋與中美洲各地的殖民地,並且由後任總統的塔虎脫作為菲律賓第一任總督。塔虎脫上任菲律賓總督,旨在為這個美國20世紀最重要的新殖民地帶入美國價值。也就是一種揉雜憲政主義政治權利觀、基督教傳統道德、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的美式現代性。並且透過昭昭天命的示範作用,教育菲律賓人,將土著塑造成美國改造後的歐洲式文明人。另一方面,塔虎脫就任總統後,也透過戰爭對外擴張。在加勒比海中美洲與西太平洋地區建立以美元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區,被稱之為「美元外交」。美國從此走上了真正的強權之路,也測試了美國精神作為一種示範性的普世價值到底可不可行。
時間進入二十世紀,在1917年這個時間點上,文安立問了一個看起來老掉牙的問題,但卻給出了一個全新的答案。也就是,導致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決定投入一戰的原因是甚麼?傳統上,我們都知道是因為德國用U潛艇攻擊美國商船,打破了美國的中立,讓美國群情激憤的投入戰爭。但文安立在這裡把威爾遜所面臨的時代,以及時代對他的影響作了精緻的復盤。文安立強調,威爾遜是把自塔虎脫到老羅斯福以降的美國外交政策,也就是「建立和平穩定的自由貿易商業環境」,作為首要考量。所以在1917年宣戰以前,在威爾遜的領導下,美國其實已經兩次介入墨西哥內政,並且開始在中南美洲活動,意圖推廣(外送)民主憲政與資本主義到這些國家。
1917年的正式宣戰,原因就在德國攻擊商船,打壞了航道,這讓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出現中斷的風險。所謂「讓世界成為一個『對民主安全的地方』」只是手段;目的是在民主政體與法治框架下運作的國家,較容易信守承諾,維繫國際商業的穩定互動與自由貿易的繁榮昌盛。也就是說,並不是一種「貿易和平論」式的,因為彼此貿易相互依賴所以不會發生戰爭;而是我們要致力於壓制發動戰爭的暴力政權(且非關政權的制度為何),才能維繫自由貿易市場蓬勃商業環境的「民主和平論」。
文安立對威爾遜主義的再詮釋,強調了威爾遜是美國立國以來第一個南方人出生的總統。他所謂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或「威爾遜主義」(自由國際主義或理想主義),其實是當時美國男性的普遍價值觀。也就是,面對其他非歐洲國家的人作為一種「白種人的負擔」,我們文明比較優越的、較為理性的美國白種人,必須肩負起保護照顧教育他們的責任。唯有把他們教育成接受我們改良式歐洲文明的現代人,這些人才有能力運作一個民主憲政的政府,也才更有能力去遵守契約、維繫承諾,保護一個世界共有的自由貿易市場與商業環境守則。這其實是一種以「種族主義」為核心的啟蒙論述。美國作為「山巔之城」,其存在的價值就在引領世界做出理性正確的決定,讓各國通力合作在美國的價值下,維持政治環境的和平與經濟環境的永久繁榮。所以,其實對美國人而言,無論一戰或二戰,都是為了美國價值(憲政主義、傳統價值、自由市場)的被攻擊而戰。
威爾遜主義與第一次冷戰
值得一提的是,文安立把「冷戰的觀念史」上朔至十九世紀末,「市場自由」與「市場管制」兩種觀念的興起與對立時,等於把傳統上由二戰結束後開啟的美蘇對峙,往前提早了將近50年。其中,文安立如前文所述,也強調了威爾遜及其思想(威爾遜主義)在冷戰觀念史中承先啟後的重要性,但仍有略嫌不足之感。在這裡,我們根據Donald Davis & Eugene Trani 兩位歷史學者在《第一次冷戰:威爾遜對美蘇關係的遺產》(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 – Soviet Relations)一書中,有關威爾遜與美蘇關係的分析,正好可以對文安立有關威爾遜的說明進行補充。
根據《第一次冷戰》的敘述我們可以發現,威爾遜1913年當選美國總統,連任一次至1921年的威爾遜。其任內剛好經歷了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威爾遜一開始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是樂觀甚至和緩的。1917年蘇共推翻民主派臨時政府的當下,是在威爾遜獨排眾議下,才避免美國外交體系直接拒絕承認「威脅協約國與美國要直接退出一戰」的蘇聯。威爾遜甚至不是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而是積極對蘇宣傳,甚至動用私人外交管道,想說服列寧繼續投入戰爭。
上述計畫失敗後,威爾遜又寄希望於俄國的反共勢力,希望他們的反革命路線能夠勝出。但事與願違後,威爾遜還是沒放棄。就在14點和平宣言發布後,威爾遜又致函第四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並且透過托洛斯基找上列寧,要說服列寧認可14點和平宣言。但最終在英法兩國的干預下,此舉無疾而終。但威爾遜還是不放棄,在1919年邀請俄國內戰雙方至第三地進行談判,但只有俄共派人來,反對派沒有出席。正因為一系列嘗試跟努力都無效,威爾遜才會轉向,對蘇聯發動了一場沒有軍備競賽的意識形態鬥爭。
1919年威爾遜發表「西部演說」,確定對蘇冷戰基調;1920年由威爾遜時任國務卿柯爾比發表「柯爾比照會」,確定雙方的意識形態差異可能造成未來的衝突,在無法透過外交手段解決雙方分歧的情況下,一種以美國價值(憲政主義、傳統價值、自由市場)為中心向外推廣上述價值的「威爾遜主義」,成為美國發動「第一次冷戰」的思想基調。而這個第一次冷戰,一直要到1933年,小羅斯福當選,美國與蘇聯正式建交,相互承認。雙方關係才進入正常化,美蘇第一次冷戰因此結束。
《第一次冷戰》的兩位作者自承,之所以把焦點放在威爾遜對美蘇關係的影響,是因為他們相信,二十世紀以來,尤其是1946年邱吉爾「鐵幕演說」以後,從肯楠「遏制戰略」強調「美國人應該以不可動搖的反擊力量,在每一個點上與蘇聯對抗(confront)」或「馬歇爾計畫」大舉金援歐洲重建,這些以「保衛西方文明對抗邪惡帝國蘇聯」為核心關懷,希望所有人「學我然後跟我一樣好」的信念,都是威爾遜主義的延伸。
兩位作者認為,威爾遜一開始審慎接觸,接著又轉向對立不承認,這種對蘇態度的變化,其實是美國國內「治病救人」或「隔離病人」兩種對蘇態度在威爾遜主義上的具體展現。也就是「我要來拯救你、治療你」這種傳統「積極進取型威爾遜主義」,與「我好得很,你才有病、你全家都有病,我不要接觸你」這種強調不可共量、只好隔離的「保守冷戰型威爾遜主義」。「積極進取、宣揚美國精神」與「救不了、放棄治療、不跟你來往,甚至積極打趴你」,兩者都是威爾遜主義,都是美國普世價值擴張與受挫的反應。而這種思維,到現在都還宰制美國國內的「和平演變」學說。
如果說,在歐洲遊蕩的始終是共產主義的幽靈;那麼,在美洲真正陰魂不散的,除了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外,始終還是威爾遜主義的幽靈。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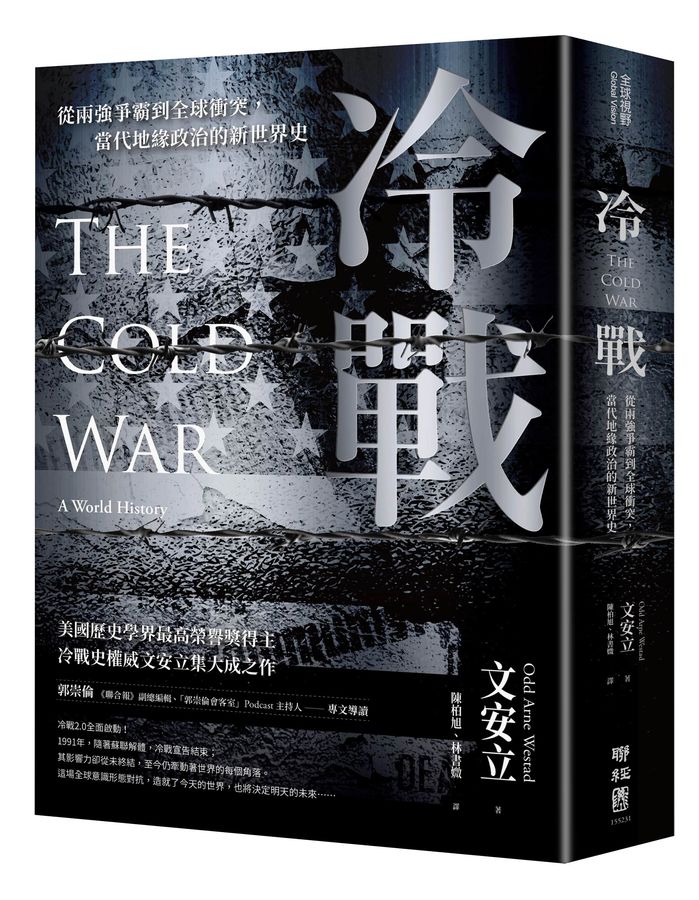
書名:《冷戰:從兩強爭霸到全球衝突,當代地緣政治的新世界史》
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3年11月
- 若然,川普歸來的混亂根源 - 2024 年 4 月 18 日
- 再論護國神山的懷璧其罪 - 2024 年 4 月 4 日
- 民主無國師?:一代風向大師威爾遜啟示錄 - 2024 年 3 月 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