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導諾蘭新片《奧本海默》(Oppenheimer)上映以來,已在全球掀起多方討論。尤其電影中,歐本海默本人(「奧本海默」是中譯;台譯過去一直以來皆為「歐本海默」)與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短暫對話,更被許多人認為雖然無涉主線劇情與人物,但卻是最劇力萬鈞的「驚鴻一撇」。這幕戲,除了飾演歐本海默的愛爾蘭演員Cillian Murphy與飾演杜魯門的英國演員Gary Oldman,兩人爐火純青的演技撐起了畫面與故事外;從後見之明的歷史角度看,這也是一次決定日後世界權力與安全格局的重要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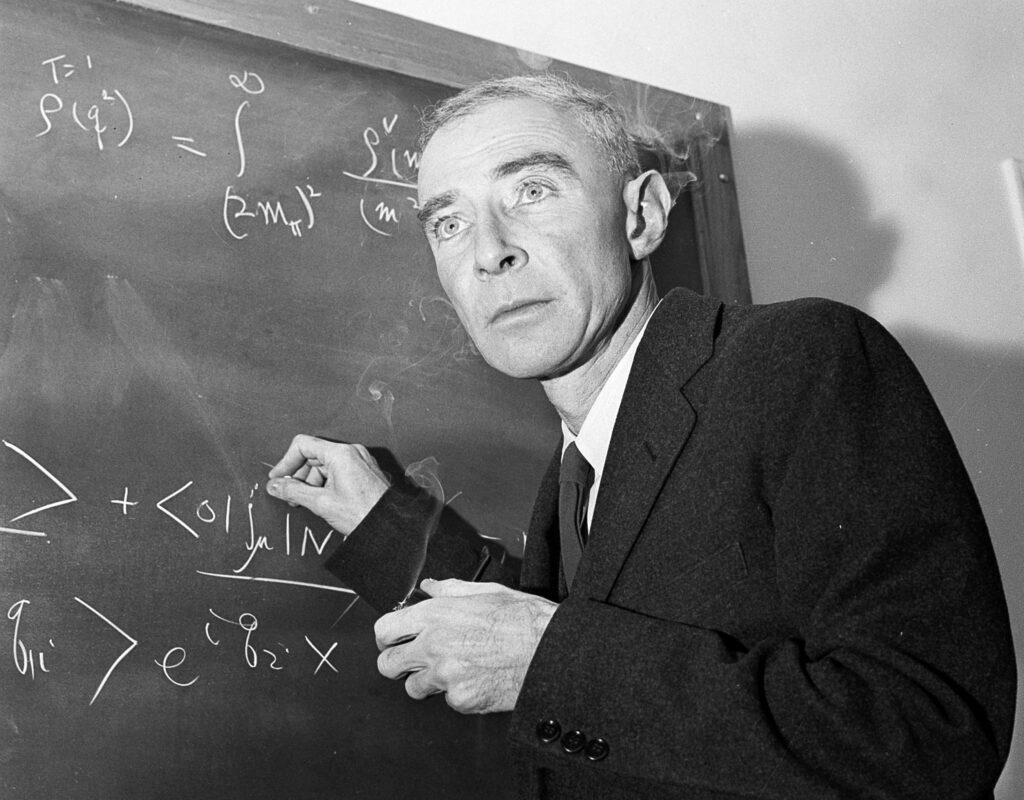
關於本次會面的細節,多數評論咸信,諾蘭身兼編導在撰寫台詞時,除了主線劇情根據廣受好評的歐本海默傳記《美國普羅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進行改編外,也參考了另一本歐本海默傳記。也就是出版於2014年的《中心生活》(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 Inside the Center)。根據《中心生活》作者Ray Monk的說法,在1945年10月會面中,歐本海默表示自己雙手沾滿鮮血;杜魯門接著拿出自己西裝口袋的袋巾,示意他擦擦手後;看似安慰卻又輕率地說:「你手上的鮮血沒有我多」。
更戲劇的是,在鏡頭帶向橢圓辦公室門口,準備掩門時,出現杜魯門遠遠的聲音表示:「我不想再看到這個愛哭鬼」(Monk表示,也有一說是「狗娘養的」(son of bitch)。因為杜魯門很喜歡罵人是狗娘養的,至少麥克阿瑟就被他公開罵過。美國的總統學研究非常出名,甚至已經是專業的次學門。所以對總統曾經的言行紀錄钜細靡遺,並不令人意外。但為何說這次短暫的會晤,影響了日後全球的安全與權力格局?或許我們要從會面的原因說起,再談談兩人對核武器管制截然不同的思維邏輯。
杜魯門與歐本海默代表兩種不同的管制思維
事實上,在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體」(trinity)核試成功前後,參與「曼哈頓計畫」的諸多科學家,就已提出各種未來如何管制核武的問題。如:要不要和戰時的盟友(意識形態的敵人)蘇聯分享核武的情資?監管的權力要掌握在美國手上,還是要交給國際單位?史實中,無論是7月底舉行的「波茨坦會議」,或是8月兩顆原子彈重創日本,並讓全世界迎來終戰時,美國核武的資訊都是相當隱蔽的,在如何監管上內部討論也是莫衷一是。但在杜魯門與歐本海默1945年10月的這次會面前,美國國內無論科學界或政界,大致上對核武管制的想法主要有二,杜魯門與歐本海默則分別代表想法光譜上的兩邊。
杜魯門想見歐本海默,除了知道他就是整個曼哈頓計畫的負責人,原子彈研發成功他是首功這個平淡的理由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杜魯門聽說歐本海默能言善辯、講話非常有說服力。更重要的是,在文人相輕的世界裡,他能夠調和鼎鼐,讓全美國最聰明的頭腦齊聚一堂、順利協作,這種人一定有很強的人格魅力與感召力。所以,杜魯門希望運用歐本海默的聲望,來達成他個人對核武的政治算盤。也就是讓歐本海默公開支持國務院力推的《梅─強森法案》(May─Johnson Bill),讓美國政府能得到法律授權,由美軍永久掌握未來核武或核能的開發與控制權力。
根據《中心生活》的描述,杜魯門派始終相信,無論是核能或核武,整套核子相關技術應該是屬於美國的。所以無論是發展或使用的管制權力,必然是國內問題。也惟有解決了國內問題,再來才有國際問題。杜魯門派這種思維,其實是建立在相信美國無論如何都可以保持核子技術絕對領先,以及核武絕對不會擴散的信心上。而這樣的信心,甚至讓杜魯門敢於在公開場合數度宣稱「蘇聯絕對不會擁有核武」(在電影中,雙方會面也有提到這件事情)。
杜魯門這種由無上政治權威而來的盲目自信與發言,讓歐本海默這種對核子技術知根知底的人聽來格外刺耳。《美國普羅米修斯》即描述,歐本海默聽完杜魯門的自信宣告後,第一時間就在自己與友人的書信裡大罵杜魯門的話是愚蠢且錯誤的。從歐本海默後續在1953年與1958年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言論,即可看出,早在原子彈還在開發階段,憑他的專業智識與政治素養,歐本海默就判斷核技術跨出美國國境是遲早的事情。所以,與其大家都偷偷摸摸亂搞,結果一個不小心導致世界毀滅;不如美國帶頭,一開始就光明正大讓大家瞭解核災的可怕,所有國家協力共同進行管制。
蘇聯1949年核子試爆的成功證實了歐本海默的看法。因為憑歐本海默對核子技術的瞭解,在原子彈開發階段,美國與納粹德國研發競賽的過程裡,美國會贏,其實就有材料選擇的運氣成分(這段電影裡有演出);更何況,對在二戰前有強烈左傾認同,又對蘇共運作也有相當瞭解的歐本海默來說,他始終相信,核子技術對蘇聯科學界而言並不困難。在當時普遍可知的發現基礎上,只要不停試錯,最後就一定會成功。重點是金錢和時間,而不是甚麼跨越不了的理論或技術門檻。
而且他們在科研上有相對於美國的低成本優勢,所以蘇聯發展核武是遲早的事情。就算不從美國這邊竊取情報,蘇聯也有成功的一天。歐本海默甚至在1953年《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中表示,若美蘇雙方投入相同資源,誰會在核子競爭中勝出除了運氣成分外,若是考量到蘇聯的舉國體制,要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來達成單一目標(核武研製),那蘇聯相較於美國的效率會更高、門檻會更低。
不同的管制思維來自不同的安全邏輯
而歐本海默與杜魯門,一個世界屬性、一個美國本位的管制思維差異,除了專業知識的落差、政治計算的不同,或甚至白話文說一點是「文理組之爭」外,更重要的是雙方有截然不同的安全邏輯。也就是「誰比較安全」與「誰比較危險」的差異。「誰比較安全」強調的是「誰比較有能力保護自己」;「誰比較危險」強調的則是「誰比較有能力傷害別人」。
對歐本海默來說,在核武面前,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有一種類似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所謂的「平等脆弱」(equality of vulnerability)。也就是,最弱的人也可以打倒熟睡中的最強人;最弱的國家擁有核武,也可以打爛最強的國家。但對杜魯門來說,既然在核武面前,所有人或所有國家都是不安全的,那我們只要比其他人更危險,就能藉由恫嚇他人來保護自己。
所以,雖然後世將核武所創造的「相互保證毀滅」或「恐怖平衡」,視為一種冷戰時代的常識或常態;但對歐本海默及其團隊裡的物理學家,以及二戰時期的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來說,這些後代視為常識的概念卻是不合邏輯的。因為無論是美蘇都沒有辦法控制所有核武,只要有這麼幾條漏網之魚,人類文明就隨時都危在旦夕。
《美國普羅米修斯》其中一個段落就提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史汀生在給杜魯門的一份報告中就強調,原子彈這種武器的出現,對美國與蘇聯都有不可知的危險。因為美國既無法勾勒出一個完整的計劃,來防禦這類新型武器的毀滅式攻擊,也無法在未來的時間裡,保證美國在這類武器上的領先地位。同樣的,美國更無法透過建立一套世界霸權,就能避免自身遭受核武的打擊或顛覆。因為核武的威攝力,其實來自於他的「不可使用性」。使用一次,核武對世人而言,會是神意式的天罰;但兩次、三次、幾次過後,人纇是很容易麻痺與習慣的。一旦習慣這種屠殺與污染,原是為了讓未來戰爭不可能發生的「例外狀態」武器,就會變成「例外狀態常態化」武器。
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熱愛哲學與宗教的科學家,歐本海默始終相信,外在世界和知識本身充滿了各種複雜、多樣和變化。面對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人類一直以來都有「尋找簡單答案回答複雜問題」的傾向。就像是世界上存在著一把鑰匙,只要找到這把鑰匙,所有的難題之鎖都可以迎刃而解。但事實遠非如此。
若我們沒辦法不斷過濾來自外在世界的新訊息,用新的證據來調整行動(無論是人的行動或國家的行動);那麼,決策就會不停失敗。用核武來解決冷戰,相信「核戰是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這種認識,也是一種「用簡單答案回答複雜問題」的典型狀況。注定了這樣的做法未來一定會失敗,而且創造的麻煩會遠比解決的問題還更多。
所以在1945年10月,杜魯門與歐本海默這次確認雙方想法南轅北轍的失敗會面後,歐本海默派的科學家們開始多方奔走,大力遊說阻擋《梅─強森法案》。最終,由康乃狄克州民主黨參議員Brien McMahon提出了新的《麥克馬洪法案》,立法設立一個全民間性質的專家委員會,也就是未來的美國原子能委員會(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並且該法規定,AEC會以推動國際原子能合作,以及在聯合國體制下,建立常設機構進行仲裁為目標。
但就像《美國普羅米修斯》描述的,當杜魯門於1946年8月簽署《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46)時,該法相較於《麥克馬洪法案》來說,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在這個1946年最後版本的《原子能法》中,多數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參與曼哈頓計畫的核子物理學家,都必須遵守比戰時還更嚴格的規定。相關的核子管制措施也一直以美軍為中心。一直要到1958年國際原子能總署設立,關於核能與核武的全球性協調管制,才有了國際主責機關;甚至到了古巴飛彈危機後,美蘇雙邊才有針對核技術的限武與管制共識,並於1960年代末期,才有《核不擴散條約》的出現。
所以真的可以「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嗎?
當我們在觀看電影《奧本海默》時,其實編劇諾蘭一直有意提醒大家,歐本海默雖然以科學為業,但足以讓他名留青史的,卻不是他的科學知識或學術研究(例如他在片中說自己「數學不好」),而是他的政治協調與組織能力。但這種科學家式「專家政治」群體中的頂尖政治力,面對政客式「權力政治」群體中的頂尖政治力時,就顯得力有未逮、甚至不堪一擊。
在一則《紐約時報》對諾蘭的專訪中,諾蘭就認為,縱使二戰結束前後當時國際局勢詭譎,美蘇意識形態對立,讓美國出現了各種麥卡錫主義式的「愛國主義危害」;但從歐本海默的書信集或是公開講話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在戰前一度有社會主義理想的歐本海默,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愛國者。基本上,他的愛國主義一直先於國際主義。
雖然史書上的「麥卡錫主義」說的風聲鶴唳、鋪天蓋地,但相較於威權國家的「白色恐怖」而言,美國始終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法治國家。一般人還是受到法律的保護。真正的極端份子在那個時代,始終還是少數。所以在核技術發展或安全戰略上強調美國中心的杜魯門派,與在同樣議題上強調世界關懷的歐本海默派,其實都是愛國者;杜魯門派也不會因為歐本海默派的「狀似不愛國、實則愛國」,而對之趕盡殺絕。也就是說,杜魯門派與歐本末派最大的差別,始終不在愛國與否,而是權力政治輾壓專家政治的當代日常,以及民主(或民粹)所賦予的權威,始終凌駕智商與專業之上的側面證明。
有趣的是,在《紐時》的專訪中諾蘭也自承,之所以把三小時電影中至少一半的時間,拿來處理歐本海默面臨聽證調查時的各方支持與批評,是因為他想翻轉過去總把歐本海默視為「誤闖政治叢林小白兔」的視角;而是把歐本海默重新詮釋為一個「看似過度天真的天才,實則野心超過智力的凡人」。因為,不帶同情的觀看歐本海默及其時代後,諾蘭認為,無論是原子彈或曼哈頓計畫,對歐本海默而言,其實都是一種「頭腦體操具像後的智商展示」。而天真的天才也不是真的天真無邪;而是某種程度上,科學家經常認為自己比凡人都聰明,理組就該嘲笑文組的典型日常。
甚至更白話一點,在諾蘭眼中,參與曼哈頓計畫製造原子彈的人們,就是現實世界中,名導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鏡頭下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也就是,天才科學家因為各種原因所以表示:「喔,我要製造一些酷東西」;接著東西做出來後,科學家又表示:「啊,完蛋了。這個東西太危險了,你們要想辦法束縛它或束縛我啊。如果沒有辦法管制,一定是這個世界太愚蠢了。」甚至,推到更極端一點,這些瘋狂科學家和連續殺人犯(或諾蘭自己鏡頭下《黑暗騎士》裡的小丑)也沒甚麼不同。因為他們都在發出殺人、破壞或發明宣告後,再來恥笑那些抓不住他的公權力。
所以,就在多數影評都認為,《奧本海默》是諾蘭寫給物理學的一封情書時,他自己又對歐本海默本人給了一個頗為世故、甚至略帶殘酷的評價(但這也滿符合諾蘭電影的套路,也就是「翻轉再翻轉」)。而這種對個人天才的反思,以及對專家政治必然遭到輾壓的無情,或許正符合杜魯門曾經說的:「不要把自己想的太重要。因為在時代的風口上,就算不是杜魯門或歐本海默,也會有人帶領美國贏得二戰、帶領曼哈頓計畫團隊發明原子彈」。
在當代的民主政治裡,個人服從於群體、科學服務於政治;或者說,科學始終脫離不了政治,科學就是政治的一環。英雄主義在這個時代,始終會被無面孔的大眾給吞沒。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 若然,川普歸來的混亂根源 - 2024 年 4 月 18 日
- 再論護國神山的懷璧其罪 - 2024 年 4 月 4 日
- 民主無國師?:一代風向大師威爾遜啟示錄 - 2024 年 3 月 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