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開始,延宕至今的烏俄戰爭,已對國際政治產生全面性的重大影響。在政治學界,不僅讓作古已久的地緣政治學門重返人們視野;另一方面,在「普丁國師」杜金(Alexander Dugin)的強力推薦下,德國公法學者與政治理論家施密特(Carl Schmitt)豐富的論著,也再度受到世人的注目(或側目)。本文試圖從施密特有關地緣政治的文本分析切入,以瞭解施氏於20世紀上半葉所描述,美國從門羅主義到威爾遜主義的霸權之路。並且,接著再從二戰前,施密特對德、日如何複製美國霸權之路的論述進行理解,藉此觀察當代中俄,如何行走這條美國曾走過的霸權之路,逕自成為了「權力階梯上的薛西佛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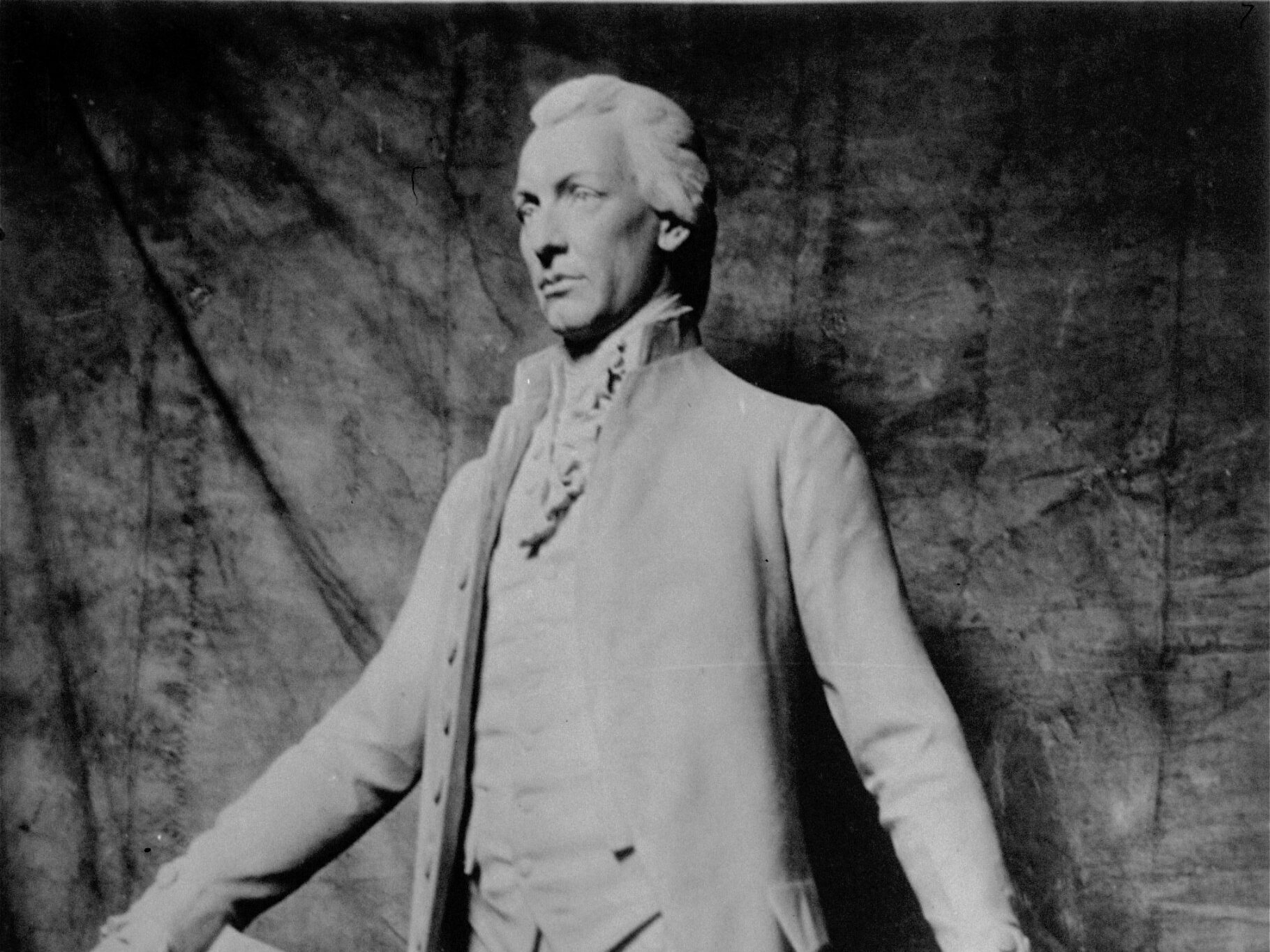
第三帝國的桂冠公法學者同時也是地緣政治分析的專家
除了是普丁與杜金的心頭好外,近年來,施密特之所以在中文知識界威名赫赫,是因為中國的新保守主義學者,為證成極權體制或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大量引用施密特批評當代自由主義的論述,使施密特成為中共系統性研究西方政治哲學的代表,甚至在中國帶起一波所謂「施米特學」或「施米特熱」的現象。但杜金極右翼「新歐亞主義」的源頭「大空間」政治秩序(Großraum,the great space)卻少有人提及。
因為傳統上,施密特學說論及國際關係的部分,經常被認為是一種「鬥爭哲學」或「戰鬥哲學」。其書寫的目的,被認定單純旨在政治宣傳,打擊他所屬時代的英美帝國主義,伸張德意志「第三帝國」在歐洲的天然權利;以維持足夠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在特定的「勢力範圍」內,重建屬於德意志的「大空間政治秩序」。這樣的說法,雖不能說是錯誤,但通常也容易流於表面,反而看不到施密特發展大空間理論對當代的意義與啟發。
源自大地法的大空間政治秩序
根據施密特《大地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一書譯者G. L. Ulmen的說法,要瞭解施密特的大空間概念,就必須從施密特對「大地法」的解釋切入。「大地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在施密特論述的脈絡裡,泛指一種「解釋政治實體互動秩序運作的普遍法則」;多數時候,是由空間、政治和法律構成的體系性秩序法則。這個秩序法則可以來自習俗與傳統,也有可能是自然法;但絕對不會是19世紀風行、由條約體系構成的實證法。一言以蔽之,大地法可說是「地球秩序」的統稱。不過,法律與政治體系或許容易理解,但「大地」作為一個承載或容納法的「空間」時,我們要如何瞭解空間與法的關係呢?
施密特在《陸地與海洋:世界史的考察》(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Meditation)一書中認為,空間概念緣於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是不同的職業。進入知識與價值多元的時代,空間概念即出現多元性。而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會產生某種力量,改變人類對空間概念的總體意識,施密特稱之為「歷史的力量」。在這股歷史的力量下,空間概念因此扭轉。
古代帝國疆域在地理空間上的擴張,讓原來位於不同區域的不同民族,感受了政治命運共同的統一性,空間觀念因此明確影響了政治意識。而連結空間概念的那些「如何劃定邊界、區隔或分割領域」的不同方式,則會創造新的政治經濟秩序。舉例而言,從歐洲共同市場到歐盟統合,就是透過經濟邊界的開放與重劃,改變了歐洲人對空間與疆域的想像,因此形成了新的政治認同。
所以對施密特來說,大地法是一種基本的空間秩序,也是一個國家或大陸的基本政治秩序。一個大陸或國家作為一個地理空間,其秩序的建立,以在空間中劃定界線、分配土地為始。所以每一次既有土地所有權的改變、彼此土地的掠奪或丟失,以及它國領土的兼併,這些都是空間秩序產生變化的重要事件。從此,因為政治秩序必須連結特定土地(空間),一個大國所對應的空間秩序,我們就稱之為「大空間」政治秩序。
施密特曾於《陸地與海洋》中表示,從地理大發現到英國海權的建構,這個歐洲人從陸地走向海洋的過程,是「整個行星的空間革命」(a planetary spatial revolution)。因為,對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歐洲國家與歐洲人來說,一旦在一個經常因為土地爭奪而產生衝突的空間秩序內,突然聞之有一整塊完整的無主地;這無疑是一次空間觀念全面顛覆的重大歷史事件。而接著從有限空間的政治秩序(大空間),到整個星球的、不切割空間的「普世主義」世界秩序,就要從這個「新大陸」開始說起。
「小空間」組成「大空間」:門羅主義的美國經濟緣起及其大空間政治秩序
後世經常直觀將大空間政治秩序,視為一種類似「勢力範圍」或是「生存空間」的軍事需求與安全宣稱。但大空間(Großraum)概念第一次出現,其實先是一個經濟概念,後來才轉變成一種地緣政治學說。施密特在1939年(納粹德國兼併捷克蘇台德後)發表了〈大空間與普世主義〉(Großraum gegen Universalismus)一文。該文將大空間的概念,連結到一種一戰後發展的,統合原料、技術與產業的「經濟圈」概念。這種概念稱之為「大空間經濟」(großrraumwirtschaft,large-scale economy)或「經濟大空間」。這個「大空間經濟」是由原來技術與交通不方便時,各自獨立的「小空間經濟圈」【the small-space(Kleinraum)isolation】所串連而成。
對施密特來說,世界史上,真正意義第一個能做到「將小空間串起成為大空間」的,是在北美,由各州(國)(states)所組成的美利堅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美洲這個全新的空間裡,經濟大空間透過各州間小空間經濟圈的自由貿易因此形成。而這個北美本土的大空間,在聯邦政府的領導下,形成了一種,承繼至英帝國海洋霸權所主持的市場機制(無特定地理空間);但在美國特殊的風土上,這種市場機制生長於特定地裡領域空間時,形成了一種美國帝國霸權支撐的「資本帝國主義」。施密特就將這個由小空間合成大空間的經濟學概念,用來解釋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作為一個「自由貿易的資本帝國」,如何在國際法與西半球的國際秩序發展中,奠定了「門羅主義」的經濟基礎。
作為一個國際關係上的政治宣告時,門羅主義對施密特而言,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一、美洲國家自歐洲殖民帝國手中獨立。二、所有國家在美洲這個空間內不得再進行殖民。三、美洲以外的國家,不得干涉美洲這一空間;同時,美洲亦不干涉美洲以外的空間。基於上述原則,所以一般對這三項原則的詮釋,都會直覺認為,美國以自身軍事力量,排除西半球區域外國家後,再殖民或介入區域內各國政治,並主導區域內國際政治。
相較於這些簡單的觀察,施密特獨到的見解是,美式門羅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成功,一開始,其實是時任門羅總統國務卿的昆西.亞當斯(後亦任總統),巧妙利用了大英帝國想要獨佔西半球經濟利益的心態,讓英國放下了與前殖民地美國,因為獨立戰爭的舊怨;從此,英國甘心以當時獨霸全球的大海軍實力與地主美國合作,希望藉此聯手來排除拿破崙法國的勢力。並且在拿破崙兵敗後,再繼續排除自維也納會議以降,反拿破崙稱帝與反各地民族獨立的「神聖同盟」與「歐洲協調」陸權勢力。
但當美國經濟規模,歷經整個十九世紀的持續擴張後,北美各州的小空間經濟,凝聚成了整個北美的經濟大空間。華盛頓開始以反殖與解殖之名,慢慢取代英國對西半球貿易的控制;藉帝國主義經濟殖民(非政治殖民)西半球後,又以軍事干預整個西半球。從此,美國逐步發展對西半球影響力,著手建立實質大空間經濟與政治秩序的方向得到確定。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老羅斯福的「巨棒外交」領導下,門羅主義才真正確立壟罩了整個西半球的經濟大空間與政治大空間。因此,門羅主義也被施密特視為世界史上,第一個有單一大陸或半球空間的大空間秩序。
門羅主義作為一種大空間秩序的美國政治思想基礎
門羅主義作為西半球大空間政治秩序在二十世紀初的成功,除了源於美國壓倒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以及受到帝國霸權所支持的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機制成功引導外;在政治制度上,施密特認為,門羅主義作為大空間政治秩序的成功,也與美國把北美土生土長的聯邦主義(federalism)帶入整個西半球有關。因為,在「權力分立」與「權力制衡」的傳統下,美國僅只追求成為一個「有限帝國」;而非真正發展成具全面價值同質性的普世主義「世界帝國」。
在這個美式聯邦主義的影響下,華盛頓主導西半球的大空間秩序時,可以允許各國在宗教、文化與政治上與美國的差異性。但在反殖、解殖與新興民族國家獨立的共有認同上,西半球各國仍有共同背景;而且,彼此透過華盛頓這個權力中心提供經濟與軍事資源,就可以維持大空間整體秩序的穩定。一個強勢核心霸權的存在,可以支持自由市場的穩定運作、調解貿易衝突與紛爭。也因此,在美國這個資本帝國的管理下,西半球大空間的各國從此缺乏全面戰爭(當然,在這之前的美西戰爭與美墨戰爭,美國已經兼併大量領土)。
只要這個大空間中的核心美國,對其他國家都只採取有限的干預,而不涉及領土變更與政權推翻。就像聯邦主義下,聯邦政府對各州只有特定權限,各州有各自國民兵、保持高度自治一樣。所以美國這種由聯邦主義與資本主義所推動的大空間秩序,與其它奉行殖民地擴張的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就出現很大的差異。對施密特來說,門羅主義這種20世紀初的西半球美式大空間,是具有高度美國原創性的新形態帝國。
在這個大空間中,美國作為政治秩序的權力核心,提供了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支援與保障。並以一個強調自由民主(反殖民族主義)與自由貿易(資本帝國主義)的廣義自由主義,安排大空間內各國法理上的權利義務關係。藉著這個安排,美國因此有了法律上,有限干預他國內政的權利;但卻不會有領土更迭、佔領與兼併的它國的問題(美國是經濟帝國主義而不是傳統帝國主義)。也就是說,在華盛頓的自我約束與安排下,美國只在貿易、財政與行政上對西半球國家進行干預與控制,而不干預政治選擇、直接選舉新政府,或對西半球其他國家的文化或宗教上問題發表意見(不過,雖然規矩已經定下來,但打破規矩的其實狀況還是不少。至少在當時,古巴和巴拿馬幾乎就等於美國的海外領地)。
另外,除了帶入聯邦主義對門羅主義進行剖析外,《大地法》的譯者Ulmen認為,施密特還看到了另外一個門羅主義建立大空間秩序的時代意義在於,以自由貿易的資本帝國作為經濟發展與制度運作的基礎,美國在西半球的大空間內,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不同於歐洲基督教文明共同體以「文明標準」,區隔共同體內外的模式。
過去,歐洲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以宗教、文化或強調主權國家身分的國際法,建構了一套「文明標準」,藉此甄別基督教文明共同體之內或之外的政治體;並且,以「文明與否」作為標準,進行差別對待。但在門羅主義的西半球大空間內,是以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債權人與債務人」模式,用「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取代了舊世界的「基督教與上帝」。也就是說,在舊歐洲,只有上帝之前,人人是平等的;上帝之外的人面對上帝之前的人,那就是不平等的。但在西半球,無關乎種族、宗教、文化等身分,在「錢」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 若然,川普歸來的混亂根源 - 2024 年 4 月 18 日
- 再論護國神山的懷璧其罪 - 2024 年 4 月 4 日
- 民主無國師?:一代風向大師威爾遜啟示錄 - 2024 年 3 月 21 日